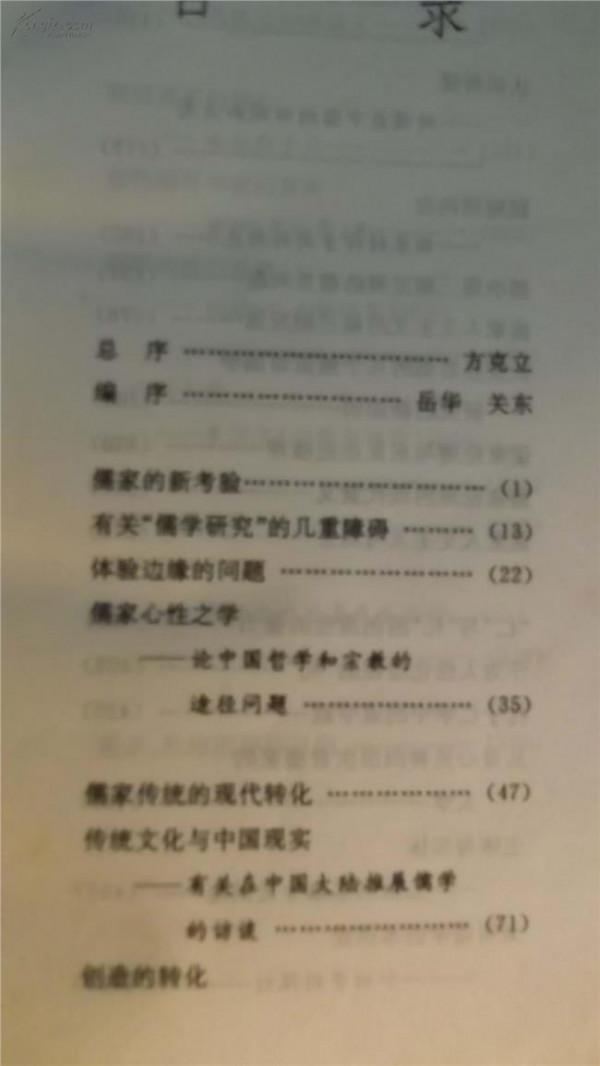杜维明评价 杜维明:中国现代化不能只走富强这条路
[导读]富强是手段,是为了人的平等,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但是,你现在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变为富强,那你只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所有文化的力量都消解掉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
名片

杜维明,1940年生于昆明,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现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先后求学于台湾东海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受教于牟宗三、徐复观、帕森斯等中外著名学者,1981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1996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长期以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诠释中国文化、反思现代精神、倡导文明对话,在海内外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杜维明很忙。
收录他早年随笔的著作《龙鹰之旅》、《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现龙在田》近日出版面世。已过古稀之年的他,忙着参加学术会议,举办讲座,与青年们交流。
6月1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博雅塔下一处幽静的办公地点,身为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的杜维明接受本报采访,从对青年的期望谈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从国人送子女出国留学谈到不同价值的互动,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谈到中国的富强之路。当然,也少不了他对大陆新儒家的认识和评价。

自我定义
“宣传”和“活动家”都是贬义词
新京报:为什么退休后会选择回到北京大学?
杜维明:2010年,我决定离开哈佛到北大建立高等人文研究院,但实际上并没有退休,仍是哈佛的研究教授及亚洲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我希望能开展文化中国的认同,文明对话的理论与实践,世界伦理以及儒学第三期发展等研究论域。我也很想为北大本科生提供“会读”《大学》和《中庸》和参加“文化中国人才班”的机会。

我虽然直接介入行政,但主要的工作是教学和研究。我们组织的学术活动很多,如演讲、工作会、国际学术会议等。
我经过了古稀之年,有强烈的意愿要进行“笔耕”的文化事业。北京大学出版社5月出版了三本反映我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思路书,三联书店准备在7月前陆续出版八本我在1989年出版的学术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有意出版一本用繁体排印的学术论集。
另外,我在一本讨论“克己复礼为仁”的书中收有我回应何炳棣批评我诠释方法的长文。我目前正在撰写的是《21世纪的儒家》。值得一提的是,过去20多年我不断地和英语世界的学术高人对话,包括了在社会理论、神学、宗教学、哲学、文化学和心理学造诣极高的思想家。我正在整理这些资料,准备以双语版的形式刊行。我希望高研院能在北大发展有国际视野而且有创意的人文学研究。
我并没有“宣传”儒学的意愿,更没有向北大学生弘法或传教的兴趣。这一点我的立场很坚定。记得1986年把我应聘为中国文化书院的导师,汤一介院长在介绍词里说我在世界各地宣传儒学,不仅是位学者而且是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
据说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我严正地表示,对我而言,“宣传”和“活动家”都是贬义词,我的自我定义是思想家,具体地说是扎根儒家心性之学的哲学家。我想在文化中国地区之外,在英语世界、欧洲、东亚、东南亚、印度及俄罗斯我活动的领域都是哲学界(或广义的思想界)。
冀望青年
没念过《大学》就没资格做北大人
新京报:学术之外,你对当下青年,包括北大的学生,会不会寄予期望?
杜维明:我希望通过对儒家心学的理解和诠释,能为北大学生提供一条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路,进而尚友千古,听到孔子、子思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陆象山、王阳明、李退溪、刘宗周、王夫之和戴震的声音。想起傅斯年在台湾大学校长任内规定《孟子》为全校各系必选的大一国文的教本,因此他有“没有读过《孟子》就没有资格做台大人”的名言。
我的野心没有那么大,我只是有一个心愿,十年后,我们能说“没有念过《大学》和《中庸》就没有资格做北大人。”
新京报:说到青年,去年最有影响的言论,恐怕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
杜维明:钱理群是我敬重的公共性极强的知识人。读他的文字,受益良多。据说他收有反映77级同学自我期许的杂志的创刊号《我们这一代》。我特别欣赏他对北大百年校庆所作的批判力度到位的反思。他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也心知其意。
当然,我希望北大的学子也能发展伦理智慧,崇尚神圣,不丢掉“赤子之心”,注重内容而不只苛求形式,培养“隔离的智慧”,保持批判的精神,走向“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为实现“真我”、“大我”而奋勉精进,走向完成自己事业和德业的康庄大道。
钱先生的忧虑,和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刚刚重新刊行的《龙鹰之旅》中所体现的“忧患意识”有很多类似之处。我记得清清楚楚,80年代中期一批老三届(当时多半是研究生)的“同道”忧心忡忡地狠批那时北大的年轻人:他们患了严重的政治冷感,群居终日,不接触任何敏感话题,满脑子是留美梦、跳舞、打麻将、吃喝玩乐而已。但没想到,那批看来毫无政治敏感的北大人居然引起轩然大波。这是不争的史实。
今天的年轻人所掌握的信息量大,视野宽,经验丰富。当然,市场经济对大学生的冲击甚大,即使投身文史哲的学生也常常通过双学位的方式来加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全球化的关系,目前中国有数百万家庭,他们的子女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澳洲读书。内地的大学生和香港、澳门及海外华人青年的互动非常频繁,价值多元的倾向明显,如何形成开放而且深具自我反思能力的认同是一大考验。
出国留学
送子女到国外是文明对话
新京报:我记得你在北大演讲时说,中国人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国外读书,从文明对话的角度来说,并不是坏事。在你看来,送子女到国外,也是文明对话之一种?
杜维明:现在中国有数百万家庭,能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以前是送去读大学,现在很多送去读中学了。我去伦敦政经学院,那里有一千个中国留学生,其中大概有50个,中学就在英国念书。现在官员、企业家的子女,出国读书的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中国文化的问题、儒学的问题,必须或者至少要在文化中国的范围内来讨论,不是只说中国大陆,还有散布世界各个地方的海外华人,还有关切中国、领养了中国孤儿的外国人。
新京报:不过,父母并不是出于文明对话的目的。
杜维明:是这样,应该从文化中国人才的培养,从文化中国各种不同价值之间的互动的角度来看。当然,送子女到国外,首先是一部分父母或子女自身的选择,不可避免;另外,子女到了国外,有一些小团体,比如富二代的团体,可能连“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都谈不上,是粗俗的利己主义者,这很不健康。但是,如果中国文化,包括我们谈的这些问题,孩子有感触,他希望学习、交流,这在发展文化中国的文化资源方面,就能发挥作用。
父母不是出于文明对话的目的,但他们可以分享其经验、经历。中国的父母送子女到国外,能够牺牲自己的利益,绝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不希望将来孩子能有所回报,只是想他们过得更好或者更愉快些。孩子是受惠者。在这个大的背景中,有很多善缘,能够产生它的力量。
现代转化
中国现代化不能只走富强这条路
新京报:你5月底在北大演讲的一个主题是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这一转化过程中,有哪些甚为关键却容易被人忽视的地方?
杜维明:我们要把儒家看成是一种整合的、全面的人文思潮,它接触面很广。但是,对于儒家,我们也需要分别,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种儒家相互冲突,那就是被现实政治利用的儒家和希望通过道德理想来转化现实政治的儒家。我们以前常常说中国有“儒法斗争”,我觉得并不是,主要是这两种不同的儒家在“斗争”。
说到两种儒家,有一个人们不太注意的情况,就是清朝政权的崩溃。有人认为,这是对纯粹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儒家一个致命的打击,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完全和儒家没有关系了。儒家仍然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而在这个基础上,怎样重新建构出一个现代的政治制度,是一个最严肃的大问题。
要建构现代政治制度,应该重视“民本”,我感觉这是属于民主的范畴。儒家一个基本的精神,就是要让人民能够安全,来维持生活,来追求富足,富足之后,可以培养他们的道德理性,所谓“富而好礼”。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创造条件,让人能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而不是用道德说教,麻醉人民,要他们做顺民。
新京报:那么,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与中国现代化的转变,有何内在关联?
杜维明:内在关联……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只走富强这条路,因为富强的价值,是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所以富强是手段,是为了人的平等,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但是,你现在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变为富强,那你只有两个条件: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所有文化的力量都消解掉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
新京报:这两个转变发生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杜维明: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应该发挥深刻的反思,要能够宁静致远,甚至要出有深厚的文化意蕴的大思想家。你看,八年抗战之时,中国没有出现了不起的文学作品或者哲学思想,这跟当时完全要求富强的狂潮有极大关系。如果不是钱穆写下《国史大纲》,梁漱溟讲《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熊十力谈《新唯识论》,如果没有这些经典作品、人生智慧,那么,现在文化转化的时候,在建构国学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资源可以传承下来,全被狂潮摧残了。
新京报:有一个现象蛮有意思,中国很多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之后,最终还是回归传统文化,回到儒家文化上来。为什么会这样?
杜维明:这个问题不谈中国。从人类的文明来看,在它发展到最关键的时期,常常回到它的根源。所以,西方哲学家,像怀特海说,整个西方哲学就是为柏拉图做注脚,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儒家文化的发展就是为孔子、孟子所代表的原初的智慧做注脚。儒家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根源性的东西,是源头活水。
这种回归,还体现了另一种要求。在当下这个社会,我们要把数据和信息分开,把信息和知识分开,把知识和智慧分开,我们现在有太多的数据、信息、知识,但是智慧不够。所以,我们要回归传统文化,回归原初的智慧。当然,这个智慧也有更新,有对话,是相当丰富的。
儒家研究
没有儒家传统,就没有西方启蒙
新京报:1994年,你接受访问时说:“从某种角度看,大陆的新儒家研究无论从资料整理到研究的深度都达到很高的程度。”近20年过去,特别是你长住中国之后,对大陆儒家,是否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
杜维明:如果从文化中国的角度来看,有一个时期,1987年前后,新加坡的儒学研究最先进。那个时候,国内很多教授被邀请到新加坡去,可以说是“大开眼界”。中国大陆儒学的大讨论,也是在1987年开始。那时不仅是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及其海外的儒学研究都比大陆强。
我在北京大学上儒家哲学的课,是1985年,到现在,快三十年了。这三十年的变化太大了,我觉得,现在儒学研究的真正动力在大陆,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比。除了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的深度,最大的变化是研究者具有问题意识。
现在,研究儒学的主要问题有中华民族的走向,如何自我了解,怎样文化认同,还有怎么认识我们的历史、政治等。具体来说,大陆有专门探讨政治儒学的,有专门探讨教育的,有专门探讨修身、修炼的。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变化,1985年,来北大听我讲课的人,一些研究生告诉我说,我可以研究儒学,但不可能认同儒学。现在,认同儒学的人非常多,认为我的生命哲学就是儒学的人也越来越多。
上面说的是学界的变化,在儒家与世界其他文化思潮的对话、交流、竞争方面也很多。比如,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与康德哲学,都有深入的交流、往来。
新京报:这种对话、交流,可能是基于某种共通的东西。
杜维明:说到这里,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说来可能会被认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其实并不是。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儒家传统,就没有西方的启蒙。有点耸人听闻?西方启蒙开始于十八世纪的法国,法国最重要的思想家是伏尔泰。北京大学教授孟华专门研究伏尔泰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他发现,伏尔泰在每一次收割稻谷时有一个仪式,那收割来的第一批谷子要用来礼敬先圣先贤,伏尔泰礼敬的是孔子。伏尔泰认同孔子的程度到这个地步!
为什么会这样?很容易理解。十八世纪的思想家,读由利玛窦翻译成拉丁文的四书五经。他们当时要寻找一个文明:没有上帝,但是有自然秩序,又合情合理,而且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至少跟欧洲相提并论,甚至更好。于是找到了儒家。这一点,我们要做深入研究。以前,总觉得在欧洲流行的是所谓的“中国风尚”,那些丝绸啊、茶叶啊、瓷器啊,现在发现,这都是表面的,真正深刻的是儒学对他们的影响。
■ 记者手记
在北大听杜维明讲座
两个出家人进来后不久,讲座开始了。
那是5月31日,杜维明在北京大学演讲,主题是“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容纳二百多人的教室爆满,过道处也站满了前来听讲的青年。
讲学时,杜维明的声调平稳如常,不用时下的新闻或者笑话,来取悦现场的观众,而是娓娓道来,把观众引向一个思考、求索的境地。这样着重精神对话与交流的讲座,竟有些求道、论道的古典气质。
杜维明谈到人们对过去患上了健忘症,对未来已失去直面的能力,只能活在当下,被生活绑架。他勉励现场观众:“风声雨声读书声不一定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一定关心。”尤其,他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受到的冲击和诱惑颇多,宜平心静气,宁静致远。
在杜维明的论说中,文化中国不只包括中国大陆,它有辽阔的思想疆域,散布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社会。正因如此,他认为儒学有三期发展,第一期从山东曲阜到中原地区,第二期从中原传到东亚。“儒学有没有第三期发展?有,那就是从东亚走向世界。”但同时,他又对唐君毅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写下的文章《花果飘零与灵根再植》颇多感慨,甚而认为,“到了韩国,你会感受到故国之风。”
这或许正是杜维明孜孜不倦地写作、演讲、论道的一个缘由。在新近整理出版的《迈进“自由之门”的儒家》一书中,他提出:“在文化生命上做个‘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中国人,才是由具体存在通向普遍价值的康庄大道:‘若问中国在哪里?就在诸位的生命里。我们每一个人,皆有资格代表中国,毫无惭愧。要说认同,即要先认同于自己个人心中之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