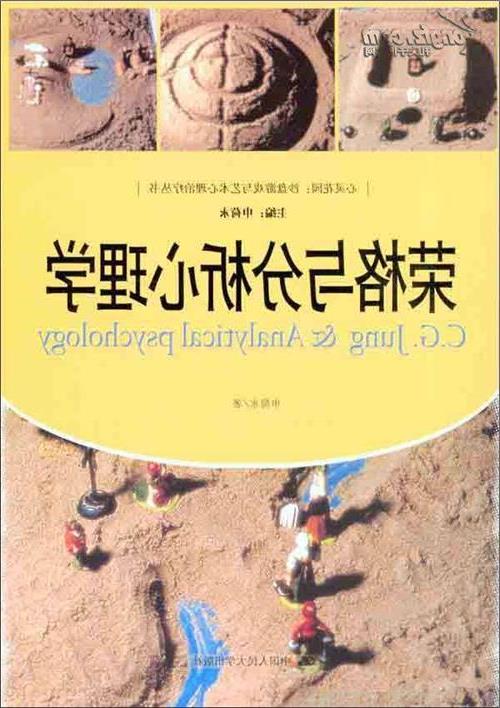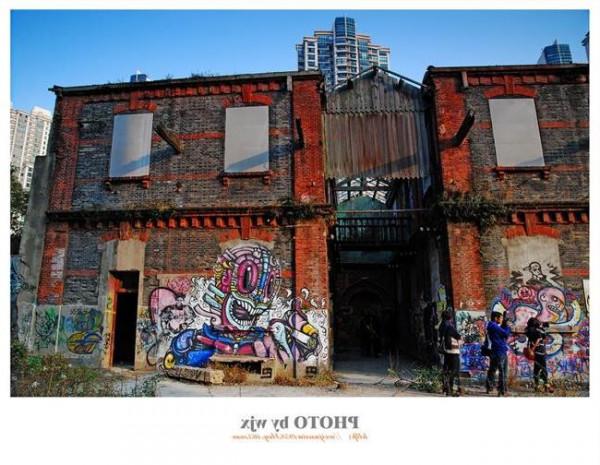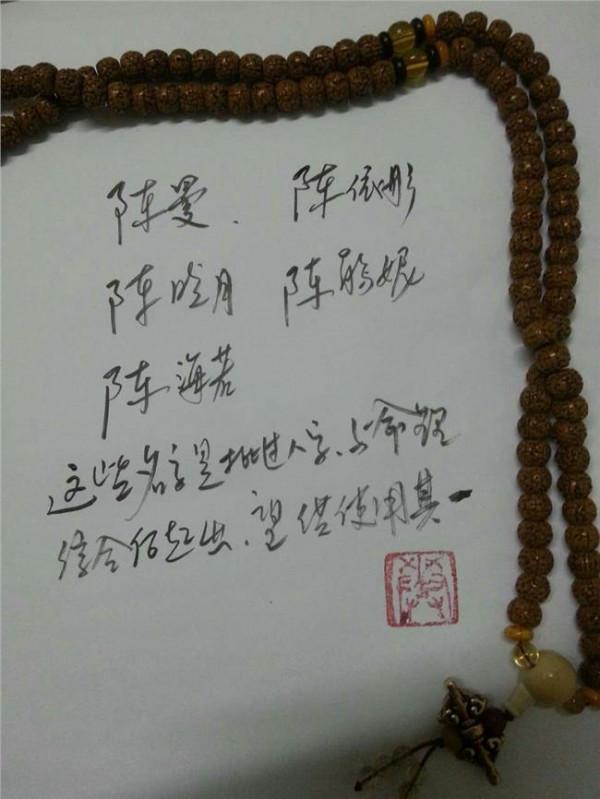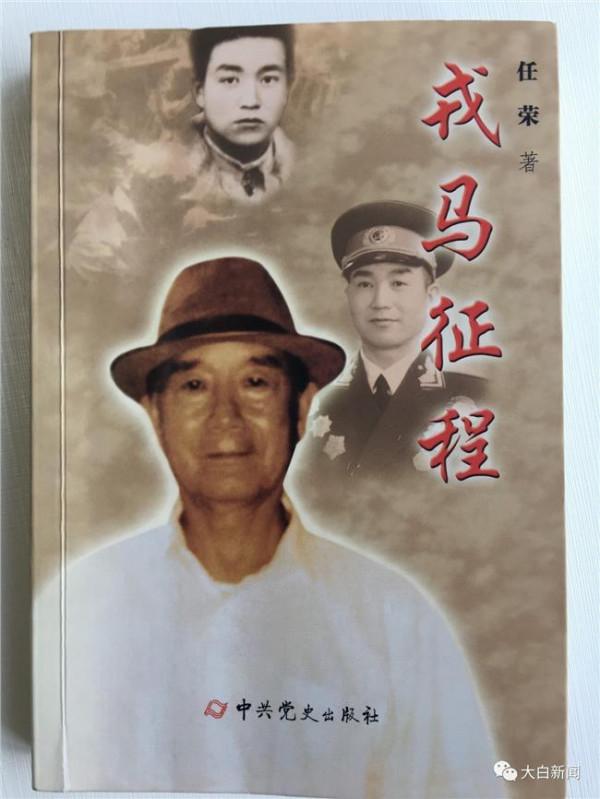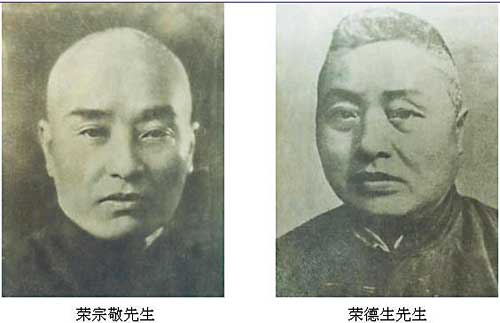荣格宗教 荣格分析心理学的宗教象征主义分析
精神分析和宗教的关系问题,一直是西方心理学界和宗教界热议的一个话题。作为两个看似不太相关的领域,它们的关系问题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瑞士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曾说,“精神分析与教士牧师对灵魂的治疗,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尽管如此,宗教观念仍然在荣格的许多著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荣格是如何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的?如果我们将这个问题细化进一步追问,荣格是如何将宗教引入心理学领域的?宗教在精神分析中到底起到了哪些作用?它又通过何种方式起作用?这些都是荣格在分析心理学的研究中必须做出回答的问题。
一、心理治疗可称为宗教的问题
在分析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中,荣格对原型心理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并以极高的热情将幻想、想象和梦魇等当作宗教观的根源。在他看来,“宗教无疑是人类心灵中一个最早和最具普遍性的表达方式”,是“对某些充满活力的要素的细致而小心的体察。这些要素被想象为各种‘力’(powers)———灵气、魔鬼、神祗、法则、观念、理想等。”属于触及个人心理结构的心理学。
荣格对宗教的定义强调的是宗教对某些神秘的情感、思想、事件进行仔细和认真的关注并对它们进行思考的一种态度。而作为宗教的内容———教义(宗教教条)则是一种集体认可的特定的信仰或特定的精神特质及行为模式的有组织的群体活动。
它反映出客观心理(无意识)的自发和自主活动。无意识的这种表达方式比任何科学理论都更能有效地抵御更进一步的直接体验。理论总是不得不无视经验的情感价值,教义却恰恰对经验的情感价值特别重视。一种科学理论总是很快便被另一种科学理论所取代,而宗教教义却可以绵延无数的时代。
进一步讲,理论能够做的只是以抽象的术语来表述活生生的东西;相反,教义却能通过悔悟、献身和赎罪的戏剧性形式来表达未曾意识到的心理过程。
因此,荣格认为,一个真正的宗教不应该是教条或信条,而应该是开放得足以包容所有个人有意义的意象,这种在个人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意象开放的特性使宗教充满活力。一旦一个宗教关闭了想象创新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宗教可能会变成信条。
在1937年的耶鲁大学特里讲座(Terry Lecture)中,荣格对宗教和宗教教条进行了区分:“当我使用‘宗教’这个词的时候,我指的并不是宗教的教条。不过,任何宗教教条,最初却的确一方面建立在对‘圣秘’的体验上,另一方面则建立在πLTLS的体验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对某种具有圣秘性质的体验及其在意识中引起的变化的忠诚、信赖和相信之上。
保罗的改信基督教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因此我们不妨说,‘宗教’这个词,指的是已被‘圣秘’体验改变了的意识的一种特有的态度。”
在《心理学和宗教》一书中,荣格曾多次提到他理论的出发点不是宗教教条,而是宗教体验:“如果心理学采取的是科学的立场,他就不得不置每一种宗教教条要求把自己当成唯一永恒的真理的做法于不顾,他不得不着眼于宗教问题的人性方面,因为他关注的乃是原初的宗教体验而不是宗教教条从这些原处体验中制造出来的东西。”
荣格所指的“宗教教条是原初宗教体验的法典化了的和教条化了的形式;宗教体验的内容在一个严格和往往十分精致的思想结构中被神圣化形成了宗教信条”。荣格认为,原初的宗教体验的实践已经成为一种仪式和一种不可改变的制度。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仪式和制度已经是僵化的、无生命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很可能仍然是宗教体验的一种有效形式。“尽管天主教会往往被攻击为特别刻板和僵化,她仍然承认:教义是活生生的东西,它的形式因此也是能够改变和发展的。甚至教义的数目也并没有限定,而是可以随时间的进展而增加。宗教仪式的情况也同样如此。然而,所有的变化和发展却只能按照最初被体验到的那些事实并在此框架之内来决定,这就建立起一种特殊的教义内容和情感价值。”
显然,宗教使人从传统的教义和法典化的仪式中获得了解放。作为心理学家,应该着眼于宗教问题的人性方面,关注原初的宗教体验,把宗教体验作为心理学的对象和目标,从而实现个体的自性化进程,获得精神的完整性。
二、无意识中存在着可靠的宗教功能
荣格认为,心理分析与宗教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们关注的基本上是不同的事情”,“教士或牧师对灵魂的治疗是建立在基督信仰告白的基础上的宗教影响,精神分析却是一种医疗上的干预,一种皆在揭示和显露无意识心理内容,并将它们整合到自觉意识中去的心理技巧。”尽管如此,荣格仍然看到了在无意识中宗教象征主义的作用。“我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有着积极的价值。从它们的象征主义当中,我认出了我的病人们在梦中和幻想中遇到的形象。……(他们)寻找对付生活内部力量的正确途径。”荣格认为,如果不恢复某种宗教的人生观,个人就不能恢复健康。因此,“人类随时随地都需要各方面之宗教所能提供给他的心灵之协助”。
尽管心理分析和宗教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在某些方面却具有相同的效果,“精神分析对无意识的敞露无疑具有极大的效果。与此同样,天主教告白的效果也是巨大的。”对荣格来说,最令人关注的问题是通过恢复宗教观来治疗神经官能症。“任何一个有理智的病人都不会期盼从医生那里获得比医学帮助更多的帮助,然而他们却期望着从神职人员那里得到更多的帮助,也就是说,期望获得宗教问题的解决。” 在《心理治疗者和牧师》一文中,荣格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我治疗过数百个病患,……病人当中,年愈中年者———即过了三十五岁者———没有一个不是想寻求一个人一生的宗教观的。他们每个人生病的原因都是因为,他已失去过去宗教所能赐给其信徒的东西,而倘若医生无法令他重新拾回其宗教观的话,那么医生亦一定无法真正治愈他的病。”
荣格强调的恢复病人的宗教观,并不一定意味着使病人恢复以前的宗教派别。在荣格的一生中,所有主要的宗教都因为失去使其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宗教的品质而受到荣格的批评。在荣格看来,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宗教应该能使该宗教满足现代个人精神需求的品质。在荣格对当代宗教的批评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态度:“我们今天的心理学兴趣是这样一种征象,它表明现在人正期望从心理中获得某种外部世界不曾给予的东西。无疑,这种东西本应包含在我们的宗教之中,但至少对现代人来说,它已经不再包含在宗教中了,在现代人看来,宗教的种种形式不再显得是来源于我们的内心,反倒更像是外部世界开列出来的清单。既然这个世界的精神不能给他以任何内在的启示,他便轮流去尝试各式各样的宗教信仰,就好像它们是星期日的礼服一样,穿上它们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又把它们像穿破的衣服一样地扔在一边。”
虽然荣格在1912年出版的《转变的象征》等论著中就已经开始讨论宗教象征主义在心理分析中所起的作用,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他才真正在心理分析中利用幻想和梦中的启示来恢复病人的宗教观。在荣格看来,幻想和启示都是宗教洞察力的真正源泉。在心理分析的实践中,荣格相信幻想能够激发病人身上的宗教观,当对幻想进行“目的性解释”时,它不仅对个人有极大的价值,而且还能产生“社会效力性”的象征:“当对幻想进行目的性解释时,幻想仿佛像一种象征,试图在现有材料的帮助下描绘出一个明确目标的特征,或者勾勒出未来心理发展的线索。因为积极主动的幻想是艺术心理的主要标志,艺术家不仅是外表的复制者,而且是外表的创造者和教育者,因为他的作品有着勾画出未来发展轮廓的象征价值。这些象征将具有有限的社会效力性还是普遍的社会效力性取决于这个有创造性个人的可行性能力。”
荣格将弥合有意识过程和无意识过程之间的鸿沟描述为在幻想意象中进行的,他把有意识和无意识在一个意象中的结合过程称为“超然作用”,他解释道:“之所以此过程被称为‘超然作用’,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种以真正的和‘想象’的或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资料为基础的作用,这是一个自然过程,一种从对立的紧张状态下涌出的精力的表现,它存在于自发地出现在梦想和幻想中的一系列现象之中。”
荣格把梦当作一种使病人与他自己的宗教相协调的手段。在他看来,梦是潜意识心灵活动的直接表现,是对无意识真实状况的一种自发和象征性自我描述。因此,“梦决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替代物,而是深层精神自发创造的表现形式,它有不可低估的价值。”由于从无意识中迸发出来的梦所使用的是象征性语言,往往具有古老的或神话的性质。
荣格主张分析梦时,梦就像一个复杂的文本,“人类心灵的进化过程在梦中比在意识状态下更容易显现出来。梦假借象征物而发言,把源自最原始的自然界之本性表现出来。意识常会很容易就脱离自然的法则,可是它仍然可利用和潜意识相调和的方法而与之相融合。借此,我们便可引导患者走向重新发现其真正自我的法则。”荣格对哲学、宗教、神话、考古学、民间传说、语言学等方面的渊博知识,使他在梦的分析中能熟练地运用这些知识来解释梦的内涵,正是通过梦的分析,他才看到了人类心灵中最原始的自然本性。
三、无意识心理过程中的宗教象征
在荣格看来,象征是有意义的意象,是促使人的心理发生转换和变化的一种工具。就其来源而言,象征是自发地从潜意识中产生的,是“建立在潜意识原型的基础之上的”。它们经历过很多转变,是有意识的长期发展过程。因而它们成为文明社会的集体意象,并被文明社会所接受。
象征不仅仅是一些符号、比喻之类的东西,它更重要的是一种推动心理发展的力量。荣格把这种力量称之为“超验功能”(transcendent function),即象征能超越和协调相互对立的双方,使之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些就是自性(self)的象征。
在心理治疗的实践中,荣格发现最经常出现的一个整体象征是“曼荼罗”(mandala)。所谓曼荼罗,在梵语中的意思是“神奇的圆圈”,“从柏拉图的《提麦奥斯》(Timacus)以来,圆的形象就被视为最完美的形式,并且总是被指派给最完美的实体。
”在基督教艺术中流行最广泛的曼荼罗,就是四福音书使者围着基督的形象。宗教绘画中的曼荼罗可视作基督和基督徒的光辉,它代表着人的整体精神。
“曼荼罗中的每个细节都很重要,并不是艺术家一时的心血来潮,或随心所欲的奇想性产物,而是多少世纪以来禅思体验的结果,是像数学公式中的符号语言般精确、约定俗成的象征语言。每个符号,包括其在公式中的位置,都能决定整体的价值。
”在心理学意义上,曼荼罗实际是统一和联结的象征,是整个人格的中心,可以把各种矛盾冲突的力量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荣格通过他个人的经验和治疗工作,已经观察到曼荼罗的共同特征:“曼荼罗通常是在精神处于混乱状态时,作为补充作用的调节因素而显现的。
这主要表现在它们的数理结构中。”正是在那些处于个性化过程内患者的梦和积极想象法中,荣格发现了关于曼荼罗形成最惊人的例子。这些想象的内容以符号形式表现出对立面的激烈冲突,也表现出自性在精神核心显现时,这些对立面的融合。
和基督教神学家们一样,荣格把救世主当作从耶稣那里获得的另外一个任命。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它就是自性原型的一个范例。然而,由于基督教把救世主描绘得尽善尽美,因此,在荣格看来,这个概念表现出许多问题:“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救世主)仅符合这个原型的一半。而另一半则表现在反基督之中。后者仅仅是自性的一种表现,除非他是由黑暗而构成的。这两半都是基督教的象征,并且都具有相同的意义,即作为救世主受难于两个窃贼之间的意象。”
在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其传统象征(如三位一体,圣餐)丧失了应有的生命活力,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意象和活动已经不再发挥其真正应有的象征功能。于是,荣格对基督教的意象象征———“三位一体”进行了修正。
众所周知,在基督教信仰中,有“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圣父”,是第一因,圣子和圣灵皆是由其分离而来,由于圣父在天,称其为“天父”。“圣子”是第二因,是天父派遣到人间解救世人、替人们受苦受难的耶稣基督。“圣灵”是第三因,它是上帝和人的中介,紧密地连接了圣父和圣子二者。这三者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三个神,而是同一本体,它们共同组成上帝的统一整体。根据台湾学者虚德的观点,基督教信仰中的圣父、圣子和圣灵乃是集体性心理的象征:圣父的象征相当于集体无意识,亦即我们内在的上帝,具有集体的普遍性与共通性;圣子基督,即“自性”的具体化,是最真实而圆满的象征,是我们每个人自我实现的个性化进程;作为基督教第三因圣灵的象征与作用有如anima(阿尼玛)及animus(阿尼姆斯),是意识与潜意识的中介,也是潜意识心灵的具体化象征。
荣格在考察了古代神话、宗教发展的起源与类型,尤其是世界各地的曼荼罗之后,认为象征“圆满”的原型不是“三位一体”,而应是“四位一体”。他的根据是,“当基督教的核心象征是三位一体的时候,无意识呈现给我们的信条却是四位一体。” “四位一体”最有意义地代表着无意识创作出来的宗教仪式。更有甚者,荣格指出宗教信仰中的“三位一体”,其实存在许多缺憾,具有许多尚未处理的问题。
为了弥补“三位一体”的这一缺憾,荣格从宗教现象学、宗教历史及神话学的探讨中寻找答案。基于从“一种宗教的主要象征性形象总是表现着特别的道德和精神态度”出发,荣格将基督教之缺憾的“第四位”指称为魔鬼(代表恶):“从现代人心理中产生出来的四位一体却不仅直接指向内在的上帝,而且直接指向上帝和人的同一。与教义相反,这里存在的不是三个面而是四个面;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推论:第四面代表的是魔鬼。……既然在三位一体的教义中,女性和邪恶被排除在了上帝之外,那么在4个位格的宗教象征中,恶的要素就会形成其中的一部分。”
荣格认为,传统的基督教中“圣父—圣灵—圣子”的三位一体,其实是表明了某种“上行”的运动。在人类的心理发展史上,这一象征尽管曾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此象征亦是“单向”和“片面”的,以至于在近现代沦为了一种“僵化”的符号,从而失去了鲜活的生命力。为了弥补“三位一体”的这种先天缺陷,荣格从十五世纪德国方济各会僧侣Ulmannus的炼金术文献《论神圣三位一体》中找到了灵感。荣格认为,应当找出其本身的阴影,也就是另一种与之相反的“三位一体”。因此,荣格提出了三位之外的“第四位”,也就是所谓的“魔鬼”(以蛇为象征),从而得出了一种“下行”的“三位一体”———“圣子—魔鬼—圣父”。荣格认为,只有结合了双重的三位一体,方能构成完整的个体化过程,也就是他所谓的“四位一体”。
荣格在心理治疗的实践中认识到,“现代梦境中的四位一体是无意识的创造;……无意识往往通过阿尼玛即一个女性形象而人格化。四位一体的象征显然来自她。她可能是孕育四位一体的母胎,即一个MaterDei(上帝之母),就像大地被理解成上帝之母那样。”[2]368为此,荣格又将基督教的“第四位”赋予了圣母玛丽亚:“‘出于自然之想象’而言,古代的自然哲学家们把三位一体想象为三种精神或三种‘活力’(volatilia),即水、空气和火。另一方面,第四种构成要素则是大地或人体。古代的自然哲学家们用圣母来象征后者。以这种方式,他们把女性的要素增加到三位一体之中,这样便产生出了四位一体或四等份的圆(circulusquadratus),它的象征是两性同体的rebis。中世纪的自然哲学家毫无疑问是用第四种要素来意指土和女人。”
荣格之所以将基督教的“第四位”赋予圣母玛丽亚是有其根据的。其一,从基督教神学的核心思想看,它的教理是不完美的,主要表现在它企图将女性因素以及人类心理的阴暗面排除在外,而清一色地专注于男性。基督教主要的象征则是三位一体,它具有绝对的男性性质。据此,荣格认为三位一体就其本身而言,全然男性化,或者基于某种未知的原因,是有缺陷的。其二,从当代的宗教学研究中,我们已知在历史上男神当道之前,象征生育力、包容力、大地母亲的女神,更是人类奉为最高的崇拜对象;尤有甚者,古代的大母神同样呈现了三个面向。根据宗教历史学家的考察,女性的三位一体其实是一种补偿、对称、平衡男性化三位一体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