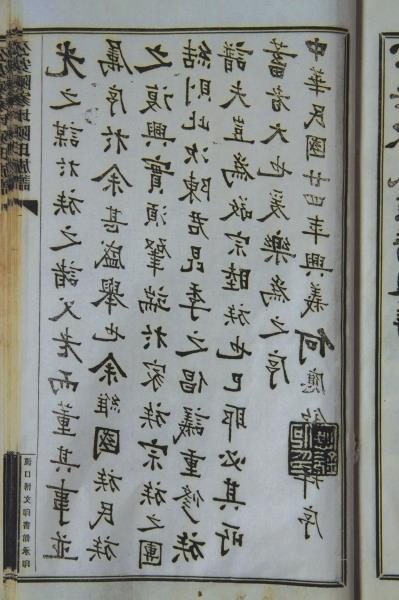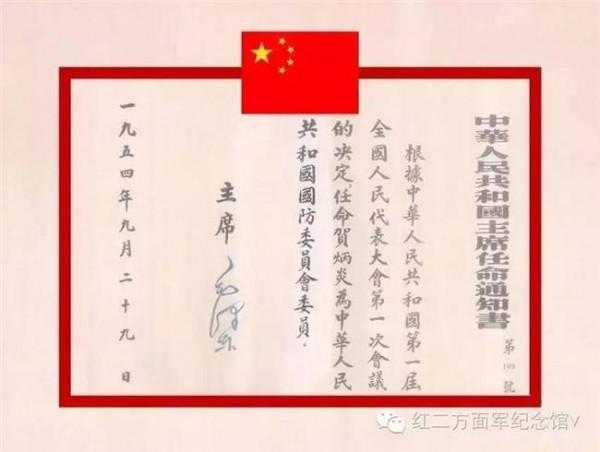贺友直女儿 贺友直:纸上做戏的可爱老头儿
如果没有特别安排,92岁的贺友直的一天基本是这样度过的:早上起床,下碗面吃,然后开始画他的老上海风俗画,那些他记忆中的老上海风情。中午,咪半斤黄酒,一个舒服的午觉后,三点醒来,回个信,写点文章,如果有稿费单要取或有信要寄,必要亲自去邮局,亦是例行散步。
晚上,照旧是半斤黄酒,就着夫人做的小菜慢悠悠地喝,一顿酒,常常要喝上两个钟头,要是正好在想哪个画里的情节,用筷子蘸上酒,在桌子上笔划。
上海话叫“老适意”。
贺友直至今还住在那间不过三十平方米的石库门房子里。推开老旧的赭红色木门,上十六级木扶梯,是传说中“一室四厅”的贺府——所谓四厅,画画、见客、饮食、起居都在这里。
地段按照贺友直自己的形容,是“钻石地段”。上海巨鹿路,曾经是法租界的所在,弄堂里的安静与淮海路的繁华似乎有一道天然的墙,两不打扰,又不妨碍往来穿梭。
女儿贺小珠说,她出生就在这里,算下来,得有58年了。很多人为贺友直张罗过新房子,但他不想搬。后来屋里又辟了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单间,作为工作间。
住进这个石库门房子之前,“贺友直”这个名字已经跟着连环画《福贵》出来了,这是他的第一部连环画。再过几年,就在这个小屋里,他画出了《山乡巨变》——维基百科上的词条,记录着“被认为是中国连环画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
但贺友直最满意的并不是《山乡巨变》,因为它“比较程式”,而是《朝阳沟》。这个讲述城里姑娘跟着农村未婚夫下乡的故事,按照他的说法,“画出情调来了。一个场景,一组人物,举手投足都是情调——这才是连环画的境界。”
他的“谈情·说爱——贺友直艺术展”正在浙江美术馆开幕,三个展厅,展出他1949年以来的代表作手稿,几十年来与连环画的谈情说爱。开幕那天早上,美术界众大佬回顾完他的艺术生涯,他低了低头,用眼镜后面的眼睛扫了扫台下一脸虔诚的人们,慢悠悠地收尾:“这样的展览,按道理应该请大家多多批评,但我估计明年大概画不动了,所以批评不批评对我已经没有多大作用了。
等着瞧吧。看得好说句好,看得不好照顾面子,在背后骂两句就算了。”
底下大笑。
果然是传说中的逗老头儿。
“明年画不动”的估计,也就是这么一说。真要到“stop”的那天,除非他提不起笔了。贺友直的案头有一方印:“永未毕业”,是一次在新加坡做展览,新加坡学者潘受形容他的一句话,说老先生小学毕业能有这样的功力,追求的就是“永未毕业”。他一听,有意思,回来就刻了一方印。
而另一个逗老头儿,比他小两岁的黄永玉,说贺友直对待连环画的态度,“有一种类似宗教的虔诚”。
美术馆一侧的大屏幕上,滚动播出着纪录片,贺友直聊他和连环画六十多年的故事。镜头一转,老爷子拿着锅铲,把光亮亮的酱爆鳝丝盛进一个青瓷大碗。他洋洋得意:“浓油赤酱,怎么样?”镜头再一切,是笑盈盈的夫人。据说贺夫人的秘制贺家菜是一绝,还有手制的红焖肉,以宣纸覆钵,蒸之。贺家菜当年让华君武和丁聪很是垂涎。
我是个匠人。
我说我是个匠人,不是贬低自己。
2000年,79岁的贺友直受邀去法国昂古莱姆高等图像学院讲两周课。
上课前,院长提醒:不要讲理论,讲理论他们不爱听。
老爷子上手,唰唰唰,几笔画了个自画像,底下一群自由散漫的法国小青年瞬间就被镇住。他的模样,后来被制成地砖,铺在昂古莱姆市法国国家连环画和图像中心的广场上。
那是张半脸的自画像。标准版。如果这两天去浙江美术馆,正门口,隔老远就能看见:脑门儿头发几根,大黑框眼镜低低地架在鼻子上,探出一双眼睛。
92岁的老头儿,眼神凌厉,却清澈地让人吃一惊。
我是1937届毕业的——浙江镇海的小学六年级毕业,从此就没有进过正规学校,除了学徒的时候去夜校学英语。
很多来采访我的人说我是连环画的“泰斗”,我知道采访我的人一定要说得比较高。我去查辞海,什么是泰斗。查出来说,泰是泰山,斗是北斗——我有那么高吗?我就是个画家。而且不敢说是“专家”,只是画连环画的“内行”。
什么是内行?
连环画在美术行当里一直是小画种,一般说“油国版雕”,连环画是不上品的。过去其他画没有市场,只有连环画有稿费,所以很多画家,陈逸飞、陈丹青,都到连环画里混稿费。包括陆俨少先生也画过连环画。
他们画连环画,我说是画得好,但不是内行。齐白石老人讲画,似与不似之间。太像叫媚俗,太像叫欺世,妙就妙在之间。但连环画是画故事,画故事就要像,连环画就是表演,在纸上做一出戏。
我是个干活的匠人,凭手艺功夫吃饭。我把自己比作匠人,并没有贬低自己,回过头去看历史,现在有多少大画家比得上明代的工匠?你要是收藏古代家具,就会知道明代木匠是多了不起的艺术家。你去看永乐宫的笔画,去看敦煌壁画,那些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画画的是什么人?都不是全国美协会员,也不是什么PROFESSOR(教授),都是画工。
画画为了什么?名利?没错。
但那是画出来以后的事,不是落笔之前。
贺友直的画不进市场,“没卖过。要有,就是别人从出版社偷出去的,或者是赝品。”就连“平尺”这样的常见词语,都被老爷子说成“平米?市尺?”
手头自己的手稿一股脑儿捐给了上海美术馆,捐也很简单:夫妻俩签个字,把东西一交,就完了。按照他想,“国家的美术馆能收藏你的作品,是对一个画家的最高肯定,还要求个什么?”
银行存款据说保持在六位数,“我又不卡拉又不OK,可以啦。”——拍卖市场,名家的一套连环画手稿,成交价已经上百万。
有朋友对贺友直说,你有个最大的特点,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老头儿说,做人简单点好。
画画为了什么?
名利?没错。钱当然是要的,过生活,是很现实的事情。
但为名为利,是画出来以后的事,不是落笔之前。
把这个顺序搞乱了,就麻烦了。什么人的画卖钱了,什么人的画时新了,你就去跟,好,到最后,北京人叫加塞,我们叫插队,大家都挤进去,出来的画都是一个样。现在我们的市场里,张三李四王五,画的画掺在一起,都很像——没有自己了。
画画的人毕生要追求的,不是名利。要追求的,第一是发现,第二是区别——找到你自己,你的路。
我能夸口,我现在的画,是跟别人拉开距离的。我绝不跟着别人的路走。我也能夸口,我现在画出来马上就能变钱。
我也有过画大画的机会。
文革刚结束,北京荣宝斋找到我,让我画一批人物画。上海朵云轩也来找我,送来一批扇面。不是这个领域的可能不知道,这是个发财的机会。文化大革命让人穷了十年,穷到什么程度?我那么喜欢喝酒的人,就只有星期六星期天,喝那么一小盅酒。
但我拒绝了,他们要我画人物画,画李白、杜甫、李清照。李白的诗我都背不出一首,让我画李白不是开玩笑嘛。画中国画,那是要有底子的。有人说自己的画是“新文人画”,那不是开玩笑嘛。你去看宋代到元代的画史,那些文人画家,从苏东坡到赵孟頫、黄公望,他们的画背后的文化积累。不画,我觉得我拒绝得很聪明。
人要有大聪明,不是小聪明。
人最大的聪明是什么?就是要明白自己。你要不明白自己就处理不好很多事情。很多人心态不好,根子在哪里?就在不明白自己。所以现在我们上海美术界,哪怕全国美术界,知道我贺友直的,都会说,这个人心态不错的。我自己也觉得。
电影故事好,有内容,这个电影就有看头。
小小连环画,也是一样道理。
1980年贺友直被中央美术学院聘为教授,给新成立的连年系(连环画年画系)教课。第一堂课,“大概是要试试我”,先让他上一堂公开课。
结果那一堂课,阶梯教室,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地上,窗台上。除了央美的学生,还有很多出版社的同行。第一排地上,齐刷刷一排,那年代最高级的双卡录音机,后面,是日后画界的中坚,陈丹青、汤沐黎。
他在央美一教七年。
33年后,贺友直在浙江美术馆同观众聊连环画,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同年轻的学生们聊连环画。
他说连环画在今天已经是“past time(过时)”的、“被摆在潘家园专卖旧书摊上卖”的东西。但他还是很想同人们聊聊。
过时了吗?
我最近看喜羊羊灰太狼,我们中国很著名的动画片。看不下去。那里头的角色,除了眼睛会动,其他都不会动,这叫什么动画?你看迪士尼的动画,《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全身都是会做戏的。那七个小矮人里的第一个,用屁股弹钢琴,你看他屁股的动作,和钢琴的琴键出来的声音是一致的,不会弹错,高音部不会弹到低音部去——这就是讲究。
我有时候看很多东西,会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很没有趣味。比如看杂技。我们的杂技只有难度,那镜头一扫到观众身上,大家的表情都紧张到这个样子:这个杂技演员就要摔下来了……
国外的杂技呢?那个小丑,就非常有趣,你看他好像马上就要脱手了,哎,他马上又抓紧了,底下大家都笑,真好玩啊——这就是讲究。
我再举个我自己的例子。《十五贯》出场的第一个人物,尤葫芦,肉铺老板。肉铺开不下去了,但是跟我一样,酒还是要喝的。这个人物怎么出场?连环画人物的出场,是要好好设计的,跟京剧的人物出场一样,一个亮相。开肉铺一般块头都很大,我就让他袒胸,露出肚皮,肚子搁在案上;肉铺开不下去怎么表现?一天来肉卖不出去,有点臭了,苍蝇叮在上面——这样来形容他的处境。
一个人物出场,你总要给他一个说明,总不能在白纸上平白无故画一个人物杵在那里。读者会想,这个人是干吗的,为什么是这样的。
小小的连环画,你真要把他画好,是要费点心思的,并不是随心所欲。这不是个技术问题,是表演。在纸上做戏,这场戏怎么做?首先要积累大量的生活资料以及社会常识,通俗点就是脑壳里面有个仓库。你要有大量的生活资料,到时候根据需要拿出来一组合,就画龙点睛了。
我们看电影,都有感觉:故事好,有内容,这个电影就有看头。有的导演再有名,但内容是空的,只有大场面,只有万箭齐发,大家就不买账。一样道理。
我再说一个事,现在大家都用傻瓜相机。
傻瓜相机,你别以为相机是傻瓜,其实相机后面的人才是傻瓜。乔布斯很聪明,但聪明的乔布斯后面,几亿傻瓜。你只会用他设计的程序,什么时候程序一罢工,电脑一罢工,全部完蛋。
美术学院的学生出去体验生活,拿笔才是正道。你在美术学院待了四年,最后落得个不会用笔画画,何必到这里来?没有这点手头功夫何必叫画家?
贺友直
中国著名的连环画家、线描大师,首届“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他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福贵》创作于1949年。作品《山乡巨变》,被称为是中国连环画史上的里程碑式的杰作。从事连环画创作50多年,代表作还包括《朝阳沟》、《李双双》、《十五贯》、《白光》等。
【贺友直的自说自画】
贺友直用画给自己写自传。
在《贺友直自说自话》,第一部分的“贺友直画自己”和后一册的“我自民间来”都是他而立之前的人生记录:画五岁时母亲的去世,跟着姑妈度过的乡下的童年;画父亲失业之后,为了一顿温饱,也会去抢有钱人家盖新屋上梁散发的馒头;画十几岁在上海当学徒,冬天睡在钳桌下水泥地上冻得两腿抽筋;画在霞飞路外国人开的店前看油画看得出神,回去用幽默在马粪纸上模仿;画父亲临终前说的一句话“我没有给你读书”;画娶妻后交不出电费,用蜡烛给孩子煮奶,一直画到解放后生活的转机——接触到连环画,1952年,又考上了“连环画工作者学习班”——这部分故事的结局,如同他的大多数连环画里的主基调:“从此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
而在中间部分,贺友直终于画到了娜拉出走之后。
那部分的开场白,贺友直是这么说的——
1996年我曾在“图画大舞台”写画过一个专栏“贺友直画自己”,用意是通过自己的经历带出一些民风民俗。发表后朋友们希望我继续画下去,我回答说:“不敢,因为工作之后,运动不断,这么说画?万一出格要犯大错误,老汉八十多了,安稳点度过晚年吧!
”先进编辑又看中我要我再弄一个专栏,自视尚有余力,斗胆应承,就开一个栏目叫“生活记趣”,意欲通过生活中碰到的趣事以反映当时的实际状况,也算是历史记录。
画下放,画大跃进,画被批斗抄家关牛棚,也画他在“文革”中给别人写大字报——无数人恨不能埋到地底的经历,他却将往事一把撕开,并且把它交去发行量上百万的报纸上登载。
贺小珠说起父亲曾经给老友刘旦宅写大字报的经历,“那是他的一个伤口。”“文革”结束后,他总是不敢见刘旦宅。一次画展上,碰到刘旦宅的儿子,过来叫一声“贺伯伯”,贺友直顿时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