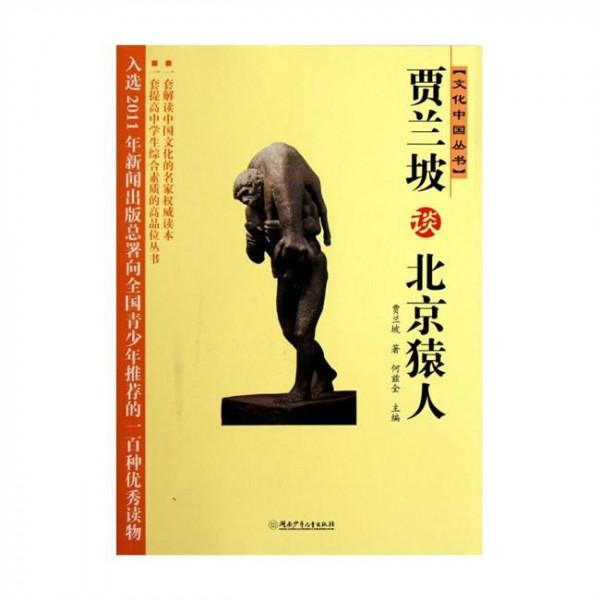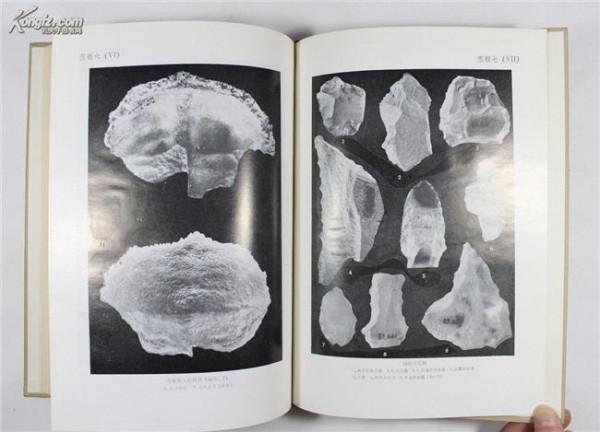贾兰坡图片 图书贾兰坡谈北京猿人/文化中国丛书
第一章 学生时代1908年11月25日,我出生在河北玉田县城北约七公里的小村庄——邢家坞。这个人口不足两百户的村子,北临山丘,南望一片平原,土地贫瘠,村民的生活比较贫困。 据坟地碑文记载,我们贾家原籍河南省孟县朱家庄,在明代初期才迁移到邢家坞。
听老一辈人说,我的曾祖有兄弟两人,大曾祖父没有儿子,按我们家乡当时的规矩,需要把我二曾祖父的长子,即我的大祖父过继给大曾祖父。
我的二祖父也没儿子,又从我三祖父一门中把我的父亲过继给二祖父。 由于生活困难,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只身到北京谋生。
我们村里有个叫宋竹君的,据说他是从燕京大学的前身——汇文大学(后改为汇文中学)毕业的,在北京英美烟公司任高级职员。
经他介绍,我父亲也进了英美烟公司。父亲本名贾连弟,号荣斋。他工作的部门叫“调换处”,实际上是做一种广告性质的工作。人们只要能集到一定数量英美烟公司出品的香烟空纸盒或烟盒内的画片,就可以到调换处换取挂历、成套茶具及小玩意儿等物品。
由于工作日渐有起色,人来人往日渐增多,人们都习惯称父亲为荣斋,而他的本名反而没人叫了。当时父亲每月薪水18元,他自己省吃俭用,每月需花8元,其余10元就托人捎回老家,家中的日子自然好多了。
我家村后的东山上有两个山洞,一大一小,我常常跟着其他小孩到小洞里探洞玩。大洞深不可测,我们从来不敢进去。
我们有时把石头打成圆球,从山上往下滚着玩,想不到这在以后的工作中,对发现石器的打制过程和用途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在村北的小山下,还有一条南北向的细长的水坑,这也是我们孩子们常常光顾的地方,我们常在坑里洗澡、打水仗。
我还常常到地里逮蝈蝈、捉蜻蜓和小鸟。在鸟中,我们最喜爱“红靛颏儿”或‘‘蓝靛颏儿”,凡是我们网着的鸟,除了这两种,其余统统放生。
当然我们小孩之间,也常常为逮乌打架,母亲只是拉开了就完事了,最多打几下屁股。她不许我骂人。骂人准挨一顿掸把子。 我外祖母家在门庄子,位于邢家坞村和玉田县城之间,地处平原。
风光秀丽,也是个两百多户的村子。外祖母住在村前街的西头路北,家中有五间北房。东侧一条路通往后街小路,东边有个数十米长、直通南北街的大水坑,水坑东西有三四十米长。
前街路南有一块菜园,冬季多种大白菜,夏天除种各种蔬菜外,还种甜瓜、西瓜等。外祖母家我也非常爱去,除了有水坑可以游泳外,更因为那块很大的菜园子里有很多好吃的瓜果和蔬菜,比邢家坞的菜多了很多,何况还有一个比我大13岁的表兄,他常带我去水坑里摸鱼和捉螃蟹,又好玩又能解馋。
大约到7岁,我在外祖母家开始上学了。当地没有学校,读的是私塾。 所谓私塾,就是在老师家上课。
老师教几个学生,屋里没有课桌,只有个方桌,炕上放个炕桌而已。教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我还记得,老师叫谷显荣。每天进老师家中第一件事,就是向孔子牌位行作揖礼,然后各就各位,背书或描红模子。
学完了三本小书,又学了半本《论语》,谷老师因病去世了。我就到邻村跟一位叫“李小辫子”的老师学。当时已是民国,但他还是清朝打扮,留着辫子,所以当地人都叫他“李小辫子”,而不知他的大名。
他对学生管得很严,背书背不下来或背错了,都要挨掸把子。他给我们讲的课文,我们听了有时虽然似懂非懂,但因怕挨打,背得都很熟。所以到现在什么“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都还记得清清楚楚。 大约到8岁,《四书》读完,又读了点《诗经》,我的外祖母去世了。
此时邢家坞也有了私塾,我又返回自己的家继续读书。 应该说,我识字的启蒙老师是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戴明虽未上过学,但聪明而知晓大义。村里有个叫王雍的老头识字最多,他看的小说也多。 每到夏天,大家在一起乘凉都会叫王雍讲故事。
母亲常把听来的故事再讲给我听,都是一些“岳母刺字”、“精忠报国”之类的。母亲一边讲一边教导我要学好人,不要做坏事。后来母亲对小说也着了迷,就借来看,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地方就请教王雍,天长日久,也认识了很多字,可就是不会写。
到后来,她连不带标点的木版印刷的小说也能看得懂。 父亲在北京做事,家里有了活钱,生活自然好多了。母亲要求我穿戴不能与其他孩子有区别,我只比别的孩子多件内褂和内裤,外面仍是粗布衣裤。
别人家的孩子在玩的时候都背着背篓,边玩边拾柴,母亲也叫我背一个,不要求拾多少柴。就是不能比别人家的小孩有特殊感。这对我作用很大,以至后来,我对待他人,不管职位高低,都能一视同仁,这不能不说是母亲当年教育的结果。
虽然父亲每月捎钱来,但家里平时仍是早饭玉米渣粥加成菜,午饭和晚饭是玉米面贴饼子加上一锅菜,有时是小米饭。
当然,过节和有客人来时就不一样了。有时为了给祖父下酒,母亲会炒个菜,祖父总想叫我一起吃,母亲反对说:“小孩子家,吃喝时间长着呢!不在这一口两口。”过年时,客人给的压岁钱,都得如数上交,母亲又说:“孩子花惯了钱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
”但过年的新衣、新鞋母亲总是早早就做好,当然还有灯笼、鞭炮之类的玩意儿。所以过年是小孩子最盼望的了。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
虽然家境不是很宽裕,但童年的生活非常愉快,无忧无虑。至今我还常常回忆起那时的情景。 我13岁那年,正赶上直奉战争,奉军溃败,逃兵很多。
他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到处抢劫,用他们的话说:“打是米,骂是面,不打不骂小米干饭。”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我父亲对家里很不放心,他便决定抽时间回到家里探亲。一路上看到的和听到的都使他胆战心惊。
他决定不在乡间久留,便雇了两辆骡子拉的轿车(即车上装个布围子),带着我的祖母、母亲、姑母和我及妹妹一起到北京暂避。轿车每辆可乘四人,乘一人或乘四人都需花4块银元。平常从老家到北京需两天的时间,这次走了三天,因为怕碰上逃兵,我们有时只好绕着道走。
途中的栈房(能停车辆的小旅店)都被兵占据了,我们只好借宿到百姓家里。当时的百姓家对往来借宿的客人都很热情,供吃供住,还不当面收钱,客人要给钱就给小孩,借给小孩买吃的为名,还了这份人情,否则人家会说“我家不开店”,叫你下不了台。
进了朝阳门,到了崇文门外翟家口恒豫隆丝线店已是掌灯时分。
当时北京大多数人家还没装电灯,用的都是煤油灯。 我们的落脚处是父亲在我们来京之前预先托朋友找好的。这原是一家闲置的店铺,托恒豫隆代为照料。我们只占用了五间朝东的正房,其他房间还闲在那里。
当时的人很迷信,住房子要看了风水才能决定,特别是作为买卖用的铺面房。我们临时租住的这幢房子,因有人说里面不干净,闹过鬼,所以很难租出去。租不出去,还要花钱雇人看管,房东当然愿意有人租这房子住,这样证明里面没有鬼;我父母又是不信神不信鬼的人,即使旧历年节也没烧过香或祭过灶王爷,这事对双方当然都是再合适不过了。
这时,我父亲辞去了英美烟公司的工作,在前门外打磨厂集资开了一片商店——义兴合纸烟店。
店子的主要股东是义兴合钱庄,经理是个叫史冠德的山西人。纸烟店就在钱庄的东隔壁。 虽说父亲辞去了英美烟公司的工作,与别人合伙开了纸烟店,但并没有完全脱离英美烟公司,他专门负责批发英美烟公司出产的纸烟。
当时这类烟店,京城共有四家,分布在北京四个区,每区一家专卖店,出售不许越界。
当然父亲的薪金也比过去多了,年终还能分到红利。 在京呆了半年之久,地方上已经平静,老家的叔叔来京接我祖母等人回家。我母亲陪着祖母、姑母及妹妹一行人又返回了邢家坞。
妹妹贾英伯在家时也读了很多书,且非常聪明,《诗经》背得很熟。 她本想留下来和我一起在北京读书,但因家人一走,我父亲便把原租住的房子退掉了,在纸烟店我们爷俩合着住,妹妹留下来挤在一起不方便,所以她不得不和母亲一起返回了老家。
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