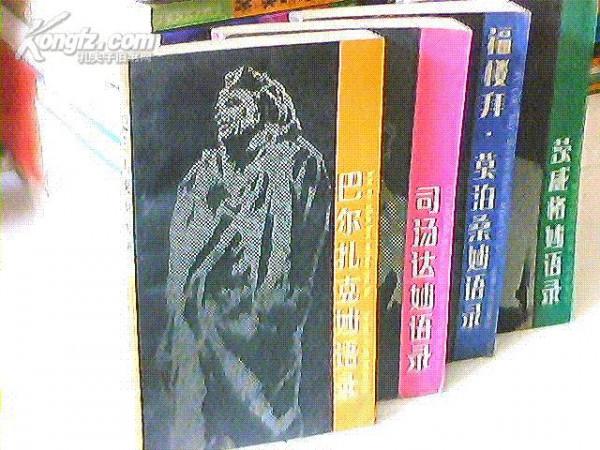【巴尔扎克名言挫折】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中国元素
巴尔扎克,尚侠,世代簪缨,略者,中国方言
人文
作者:曹洪洋
被誉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的巴尔扎克,一生中仅写过两篇较长的专论,其中一篇就是他为好友奥古斯特·博尔热的画集《中国与中国人》所写的专论,并称“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和中国人的摇篮里度过的”。

从未到过中国的巴尔扎克一生对中国有着“永无止境的兴趣”,他笔下的中国是“仙境”,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向往,它地处东方“金色梦幻的乐土”,是一个“诗意浓厚”“美丽富饶”的国度;那里的人“在德行方面比在钱财方面更加乐善好施”;“对这个民族的钦佩简直不能自已……它的历史比神话的年代或圣经的年代还要悠久……”

就我们熟悉的外国作家而言,要论其书中的中国元素,似乎没有谁能多过巴尔扎克。通过那些信手拈来的书写,他对于中国器物之熟悉及喜爱,可见一斑。
他形容某个客厅硬木地板的光滑、细腻,“宛如上了仿中国漆器的油漆,煞是好看”(《莫黛斯特·米尼翁》)。

他称赞一件中国牙雕作品的精美,说“为此大约需要两户中国艺人之家雕刻一辈子”(《假情妇》)。
他描述从阳台往下俯瞰的街景,“那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的情景大有中国走马灯的意味”(《双重家庭》)。
他将美好的女性形象比作“中国画家笔下的仙女像”(《贝阿特丽克丝》),更在《烟花女荣辱记》中直述:“她的皮肤细腻,有如中国的宣纸。”他描写女性的眉毛:“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于中国画家的手笔”(《幻灭》),“像中国画家描出来的”(《贝阿特丽克丝》),或者“好似中国脸谱用彩笔一一勾出的那样”(《莫黛斯特·米尼翁》)。

他不厌其详地描摹一幅窗帘,“走进餐厅时,男爵情不自禁地要爱丝苔摸摸窗帘的料子。这窗帘简直跟王家的一样阔气,那里子是白色波纹绸,边饰足以与一位葡萄牙公主的胸衣媲美。这窗帘料子是从广州买来的一种丝绸,中国的能工巧匠在上面画上了亚洲的各种飞鸟,其精美只有中世纪绘在犊皮纸上的画或者绘在查理五世的弥撒经本上的画可与之媲美”(《烟花女荣辱记》)。
他描写一个人,“他蔑视社会的习俗,摆出一副对上流社会所尊崇的一切都要予以批判的架势,这就使他与那些思想狭隘和力图维护传统礼节的人格格不入。但这种作风是一种像中国货一样新奇的东西,一点儿也不令妇女们讨厌”(《夏娃的女儿》)。
据不完全统计,出现在其作品中的中国物件有:窗帘,帷幔,挂毯,屏风,红绸披肩,南京缎裤子,南京土布裤子,北京绘花宽条绸,各种漆器、瓷器和木器,花盆,宣纸及其他中国纸,阳伞,中国画,中国锣,各种用作装饰的小物件,装烟草的中国陶罐,或长颈或鼓肚的形状古怪的各类中国花瓶,中国佛像,中国古玩,中国女红台之类的中国家具,皮影戏,中国式的水阁、亭子和书房,以及从中国运来的果品。
恐怕连专营店的常客也开不出如此之长的货单吧。
生于1799年的巴尔扎克没有赶上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chinoiserie),但在19世纪上半叶应该还能感受到不少余温。历史告诉我们,早在公元前1世纪,中国丝绸便通过陆路传到了罗马,然而东西方之间大宗货物贸易的真正开展,还是要以1513年葡萄牙商船出现在中国海面为标志。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为欧洲与中国的交往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660年前后,每年行驶在达伽马所开辟的东西方航道上的商船,即达20000艘之多(《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海上强国相比,作为陆上强权的法国进入远东海域的时间较晚,对华贸易规模较小,然而它一样迎来大量品种繁多的中国商品的涌入。
商品的输入即意味着文化的输入——因为任何商品“本身就带着一种实用哲学和生活学说”,更不用说价值观和审美观了。法国汉学家艾田蒲曾经举过葡萄酒瓶塞的例子:如果我们抛弃旧传统,手懒而不用蜡封瓶口,葡萄酒的质量就会受到损害——于是,纵然把世界的所有专利证都给了加利福尼亚的葡萄种植者,他们也绝对酿造不出优质波尔多葡萄酒,甚至普通的安儒葡萄酒,因为这些葡萄酒都离不开瓶塞。
所以,当一个中国人喝法国的葡萄酒时,他就分享了法国的价值观;而当罗马妇女身着中国丝绸时,她们也就打上了中国的价值标记(参见《中国之欧洲》)。
在这个意义上,自述童年“在中国和中国人的摇篮里度过”的巴尔扎克,对于中国文化自然会有深刻的理解和高度的认同。
在《幻灭》中,他比较详细地谈到了中国的造纸工艺和技术。小说主人公吕西安的父亲曾经有个想法:采用美洲的一种植物来造纸,因为这近乎中国人用的原料,成本非常便宜,可以把纸价降低一半。吕西安将此推荐给恰巧接手老家印刷所的同学大卫,大卫于是开始进行尝试。借大卫之口,巴尔扎克展示了自己关于中国造纸术的渊博知识:
有一次在我巴黎的办公室内,几个人为了中国造纸用的原料,展开一场热烈的争论。由于原料关系,中国纸一开始就胜过我们的纸。中国纸又薄又细腻,比我们的好多了,而且这些可贵的特点并不减少纸的韧性,不管怎么薄,还是不透明的。
多年来大家对中国纸极感兴趣。有位非常博学的校对,……德·圣西门伯爵来看我们。他说,肯普夫和杜·阿尔德认为中国纸和我们的纸同样是用植物做的,原料是楮。另外一个校对认为中国纸主要用动物性的原料,就是中国大量生产的丝。
他们在我面前打赌。……就把问题送交研究院,由前任帝国印刷所所长马塞尔先生做评判。马塞尔先生打发他们两人去见兵工厂图书馆馆长葛罗齐埃神甫。据葛罗齐埃神甫的意见,两个打赌的人都输了。中国纸的原料既不是楮,也不是丝,而是用捣碎的竹子纤维做的纸浆。葛罗齐埃神甫藏着一部讲述造纸技术的中国书,附有不少图解,说明全部制造过程……
葛罗齐埃神甫所藏的这本书,按照推测应该就是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的《天工开物》。《天工开物》卷十三《杀青》介绍了中国古代制造竹纸(煮竹取浆)和皮纸(煮楮树皮取浆)的方法,对于造纸过程、工艺以及工具等,都有详细的描绘并附图。巴尔扎克的转述的确存在一些疏失,然而他洋溢于字里行间的对于中国造纸技术的由衷赞叹,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篇小说《禁治产》,在观念上拥有着更多的中国元素,但一直未引起中国读者的足够关注。小说主人公是一位善良正直、充满正义感的侯爵——德·埃斯巴。他因其祖上采取不道德的方法巧取豪夺了一家姓冉乐诺的新教徒的田产而倍感愧疚——“我不愿意我的孩子们将来对我像我对祖先一样想法。
我要传给他们一份没有污点的遗产,一个没有污点的爵徽;我不愿意贵族的品格在我身上变成自欺欺人的谎言。”于是,侯爵设法找到了还在世的冉乐诺母子,要返还其财产。
这家母子也是老实人,她们只愿意按照当初的地价——而不是有了巨额升值后的现价(他们将此看作一种剥削)——来收回。侯爵和这母子俩共同议定偿还110万法郎;鉴于数额庞大,侯爵只能分期支付,冉乐诺母子当然也拒收任何利息。为了支付这笔款项,侯爵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动用其收入。于是这引起了他和侯爵夫人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出身于名门望族的侯爵夫人,极其热衷于混迹上流社会并在其间呼风唤雨,她不仅无法理解丈夫的行为,而且将此视为疯狂之举,遂向法院提出下达禁治产令的请求。她在诉状中说:
侯爵行事均带有疯狂意味。近十年来,渠所关切之事仅限于中国事物,中国服装,中国风俗,中国历史,乃至一切均以中国习惯衡量;谈话之间往往以当代之事,隔日之事,与有关中国之事混为一谈;侯爵平日虽拥戴王上,但动辄征引中国政治故实,与我国政府之措施即王上之行为相比,加以评骘。
……侯爵之自溺狂使子女亦蒙受影响,彼等所受教育竟一反常规,学习内容与天主教义抵触之中国史实,学习中国方言……
事无大小,侯爵均谓在中国即非如此这般!谈话之间倘或提及冉乐诺夫人或路易十四时代之时事,侯爵即愁容满面,且常以为身在中国。渠之邻居,例如同住一处之医学生爱德蒙·伯凯,冉-巴蒂斯特·佛雷米奥教授,与侯爵往还之下,认为其有关中国之偏执狂,实出于冉乐诺母子之阴谋,意欲借此使侯爵完全丧失理性……
具有高贵品质的侯爵竟被医学生和教授戴上了一顶“中国偏执狂”的帽子,巴尔扎克这么写显然有其特殊用意:如果有谁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并希望从那里为法国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贫富对立、阶级压迫、权力滥用、法制腐败、宗教冲突、道德败坏、教育僵化、社会束缚等等——找到答案,不要说一般老百姓,就是智识阶层也不能接受。
然而侯爵的“中国癖”(Sinophilie)并非出于完全的想象,而是来自广泛的阅读和丰富的知识:“我从小有个受业的老师,叫做葛罗齐埃神甫,由于我的保举,查理十世派他做兵工厂图书馆的馆员,那图书馆是今上当太子的时候就主管的。
葛罗齐埃神甫对于中国极有研究,深知它的风俗习惯。我在一个人极容易对所学的东西入迷的年龄上承继了他的遗产,25岁就学会了中文。我承认我对这个民族的钦佩简直不能自已,因为它能把征略者同化,它的历史比神话的年代或圣经的年代还要悠久,稳定的制度使它能保持领土的完整,纪念建筑伟大无比,行政机关完满无比,革命是不可能的;它认为理想的美是贫弱的艺术原则,它的工艺和珍贵的出品发展到登峰造极;我们无论在哪一点上都不能超过它,而我们自命为高人一等的成绩,他们却和我们并驾齐驱。
”
如果我们读过巴尔扎克在1842年10月发表的一篇专论——《中国与中国人》,就会知道侯爵的自述羼杂了巴尔扎克本人的经历。“从十五岁起,”巴尔扎克写道,“我就读过杜赫德神父、葛罗齐埃修道院院长……关于中国的多少有些不可靠的绝大部分的报道;总之,理论上有关中国的一切知识,我都知道。
”杜赫德神父编辑出版了《中华帝国全志》——这部西方汉学巨著荟萃了超过27位来华耶稣会士在长达80余年里的书信稿件,首刊于1735年,随即被翻译印行于欧洲各地。
他在《序言》中写道:“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判定:因为这些治国理家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始终得到贯彻执行因而持久不衰,所以当人们看到如此广阔的帝国历经漫漫世纪长河却依然屹立于世,而且至今依然焕发活力,也就不会大惊小怪了。”对照上一段,可以看出巴尔扎克中国观念的来源。
然而与其说巴尔扎克意在提供一个中国样板,倒不如说他希望将中国看作一面奇妙的镜子,借以让法国人看到自己昔日充满荣光的倒影,认清什么才是真正的法国身份。他在小说里写道:“固然他(侯爵)自信血统高人一等,但也相信贵族有贵族的责任;而贵族所应有的德性与魄力,他也无不具备。
他用他的道德观教育两个孩子,从摇篮起就把他阶级的信仰灌输给他们。对于自己的尊严所抱的深刻的观念,对于姓氏的骄傲,对于身为优秀种族的信心,在他们身上养成了一种天潢贵胄的傲气,尚侠的精神,和古代诸侯们乐善好施的仁爱。”
在巴尔扎克笔下,侯爵所做的一切终究还是为了法国的利益。侯爵承认,“即使我常常在谈笑中把欧洲各国的情形与中国的相比,我到底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法国绅士……我的政治生涯,我的世代簪缨的身份,自己可能挣到而传给孩子们的新的光荣,全都放弃了;但是我们姓埃斯巴的并没损失,孩子们将来一定是出众的人物。
我固然没有进贵族院,但日后他们可以凭着为国效劳的功绩,光明正大的去争取,他们也必定能为祖国作出一番传世的事业。我把家声洗刷干净之后,等于替后人奠定了一个光荣的前途:虽然这番苦功是没人知道的,没有光华的,也不能不说是一件高尚的行为罢?”然而在一个卑鄙和堕落大行其道的年代,个人的高尚之举只能是一把酿造自饮苦酒的酵母。
1841年12月24至28日,巴尔扎克在《世纪报》上以连载形式刊发了小说《假情妇》,这时维多利亚女王组织发动的鸦片战争还在进行期间。巴尔扎克对于那种试图通过暴力获取一种“优越地位”的观念和做法——这在欧洲大陆屡见不鲜——大不以为然,他在书中谈到俄国与波兰的冲突时写道:“顺便说一句,波兰满可以学中国人的做法,不是用武器打败俄国,而是通过其道德风尚的影响。
”在评论英国发动掠夺中国的鸦片战争时,巴尔扎克使用了英国的绰号“约翰牛”,表达心中对欧洲老牌殖民主义的蔑视。
他谴责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邪恶动机,揭露其“不道德”的本性。在《中国与中国人》文中,巴尔扎克借画家之口,称赞中国民情,颂扬“中国人民重德轻利”的传统优秀品格,并说:“向本欲完善资质的消费者提供毒品,老天不容。或曰,不义之财,终不得好报。”
作为挚友,雨果曾在巴尔扎克的葬礼上致辞说:“(巴尔扎克的作品)生动、深邃且熠熠生辉;从中能看到我们的现代文明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既真实又惶恐而骇人的东西,走来走去……”为作品添色不少的中国器物描写颇适合于前半句;而通过后半句,我们或可明白那些以中国思想做比拟的观念为什么常常会使读者感到纠结。
十八世纪的东西方贸易并未出现多大的波动和逆转,而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却经历了由赞美到怀疑再到否定的根本转变。与莱布尼茨、沃尔夫和伏尔泰等“中国粉”相比,孟德斯鸠、卢梭和黑格尔等“中国黑”并不会拒绝在其早餐盘上安放一杯热腾腾的香茶,他们的身体也不会拒绝东方棉布做成的吸汗透气的贴身内衣。
有学者研究发现,法国《新书评论杂志》1840年之前所涉书籍“均为介绍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文化的”,1840年起则开始出现了负面意见。
1842年在对一本英国中尉关于鸦片战争的书进行介绍时,认为“阅读此书可知中国军队贪生怕死、不堪一击……”在法国正式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的报纸杂志涉及中国的负面报道就更多了,有一幅漫画甚至对中国人不懂大炮膛线而发出了尖刻的嘲笑(《中法文学关系研究》)。
群情汹汹之中,难得有雨果这样的人士站出来仗义执言。1861年当拿破仑三世在巴黎恬不知耻地展出劫掠来的圆明园珍物时,雨果发出了著名的《就英法联军远征中国给巴特勒上尉的信》。他讽刺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
这就是文明对野蛮干下的事!”在信的结尾,雨果真诚地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洗刷得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这当然会让我们想起前述《禁治产》中侯爵的话。早在1848年拿破仑三世还是路易·波拿巴时,雨果曾为其当选法国总统提出过一个政治计划,其中就有“学习中国文化”一项内容——这依然能让我们联想到那位侯爵。(曹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