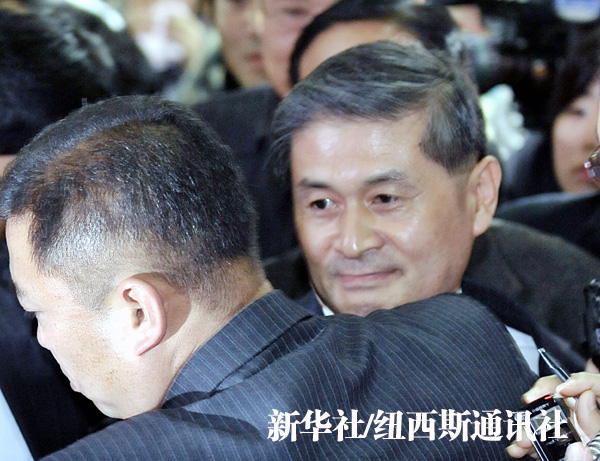伯格曼安东尼奥尼 中国新闻周刊:安东尼奥尼说“不要试着找我”
伯格曼与安东尼奥尼,两位现代电影开创者的离世近乎同时,注定了要被当作一个象征意味颇浓的符号。虽然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资格被称作电影大师的创作者已经相继沉寂,但他们离世的巧合,又让我们记起美好而深邃的影像岁月一去不回的悲伤
文/卫西谛
罗马市长在悼念安东尼奥尼时,用通俗的口吻感谢这位大师的影片,“我们拥有了观看现实的另一个视角,观看女性面孔和汽车设计的另一种方式。即便是一朵云,在看过他的影片之后,也不再是原来的模样了。”当然,安东尼奥尼的另一视角并非像法国人热内在《天使艾米莉》里,用CG技术将云朵变成玩具兔的模样,他寻找到的是用镜头表现内心的准确方式。
国内许多影迷曾经将安东尼奥尼晚期作品《云上的日子》视作是最爱的艺术电影之一,那部充满欲望与哲思的电影以短片集的方式,延续了他一贯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可沟通性的疏离主题。
“现实为电影服务”
上世纪50~60年代的欧洲,世界电影史出现了一次“剧烈的造山运动”,涌现了一批后人无法超越的经典作品与大师人物,从伯格曼、塔尔科夫斯基、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到戈达尔。电影学院的年轻学者杜庆春曾总结说,“那个时代的电影大师和思想大师的思想敏锐程度和深度达到惊人的契合,如同萨特对塔尔柯夫斯基的激赏,或者罗兰·巴特对安东尼奥尼的书信倾诉,以及弗朗索瓦·多斯说(戈达尔的)《万事快调》的一个镜头呈现了‘历史地自我思考的拂晓’。
”
作者甚至指出,1983年安东尼奥尼的中风造成语言能力丧失,也是欧洲思想界巨变的一个侧影:1980年罗兰·巴特被干洗店的卡车撞到,受了一点轻微脑颅外伤后,不可思议地选择了死亡;1980年,路易·阿尔都塞掐死妻子,进了精神病院;1981年,雅克·拉康在经受严重的失语症后撒手人寰;1984年米歇尔·福柯死于这个世纪的新瘟疫艾滋病。而安东尼奥尼似乎为了电影活了下来,他曾说,“拍电影就是我的生存”。
安东尼奥尼最初是通过成为影评人而进入电影圈的,他曾在1941年的《电影》杂志上写下一句话:“如果不严肃地介入社会,就创造不出艺术。”1943年,安东尼奥尼开始拍摄纪录短片,他在拍摄《波河的人们》(Gente del Po)的同时,在波河的另一边,维斯康蒂正在拍摄《沉沦》(Ossessione)。在此之前,意大利电影几乎不把镜头对准底层人民。安东尼奥尼于是成为新现实主义最早的一分子。
50年代中期,他和另一位新现实主义成员费里尼背离了这条道路。这两位导演都生长在外省,他们的故乡费拉拉和里米尼都在他们各自的电影世界里成为重要的场景。他们几乎同时开始拍电影,也同时走出了新现实主义之路。安东尼奥尼说他与新现实主义导演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认为“电影为现实服务”,在他看来,“现实为电影服务”。
评论家一般将后来的费里尼的电影称为“魔幻现实主义”,而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被称为“内心现实主义”。这也是两位意大利电影大师最大的区别,在安东尼奥尼的电影里没有一个费里尼式的有着“伦理落点”的结局,因为他是一个不信上帝,却又是一个守着道德疆界的人。
如果我们抛开剧情层面上的沉闷(有一个词汇是Antoniennui ,指“安东尼式无聊”),许多热爱艺术电影的影迷对他的作品的直觉往往会是:冰冷、坚硬、抽象、缓慢、深刻,但是它所呈现的视觉画面又是如此完美、迷人、敏感、准确。
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人类情感三部曲”:《奇遇》《夜》《蚀》这三部作品时,他发现,私生活也具有政治性。他不可避免地和同时代的艺术家一样,受到当时的精神分析与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创造出来的影像却独一无二。
《奇遇》被称为是第一部真正的现代电影。他要探索的是“道德的未知数”。可以说,对于无神论者、理性创作者安东尼奥尼而言——“不可知论”是他永恒的主题。
一名电影导演想展示的新世界
作为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的独特性在于,他几乎不触及现代西方哲学的经典命题——拯救,而成为现代西方文明无情的批判者。安东尼奥尼用极其冷漠的诗意,表现出人类在新造城市与先进科技的包围下,失去沟通能力之后的孤独境况。
而那些“既无闪回,也无预言”,只关注当下现实的电影,他所探讨的问题,与今天飞速发展的中国是多么接近。
早在1964年的《红色沙漠》里,他已经开始审视适应新世界的问题。为了能够真正讨论人类面对外部环境的突变、而产生的内心困境问题,安东尼奥尼往往选择模棱两可的开放性结尾,甚至没有结尾。安东尼奥尼式的结尾也成为电影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片段。最著名的比如《蚀》,最后若干断续的空镜头组成结尾;《放大》的最后人们用空气代替网球进行的哑剧式运动;《扎布里斯角》最后资产阶级象征物的别墅无声地爆炸。
安东尼奥尼电影中,时间往往是扁平的,但他电影里的墙壁、窗户、街道、房屋、岩石,总是占据他的电影的银幕的大半,成为研究者们再三探讨的关键词。他的空间观念也影响了之后许多导演。
为了表现内心世界,安东尼奥尼甚至不惜改变外观世界,在沼泽上喷上红色涂料(《红色沙漠》),改变伦敦一部分的街景(《放大》)等等。这是一种表现主义的趋势,他想要追求的是内心的真实,譬如《红色沙漠》要表现一个精神病人的视角,那么在这个病人眼里五颜六色的世界才是真实的。
什么是真实?安东尼奥尼曾说,“我们知道在表露的意象背后,还有另一个对真实更忠实的意象,在那个之后还有一个,层层包裹……那真正的意象是没有人可以看到的……抽象电影因此自有存在的原因。”
克莉丝汀·汤普森和大卫·波德维尔在他们的《世界电影史》中说“整整一代人都以安东尼奥尼电影中的寂静、空虚的世界来鉴定电影的艺术性,而许多观众也看着他们自己的生活展现其中”。而安东尼奥尼似乎并不愿意成为他电影之外的瞩目焦点,比起同胞费里尼那样留下各种各样的自传、他传、访谈和逸闻趣事,安东尼奥尼则很少对自己的生活和作品作出具体的诠释,他说过“任何解释都不如神秘本身有趣”。
在中国,和他有关的著作是文德斯所写的《和安东尼奥尼一起的时光》,记录他帮助大师拍摄《云上的日子》时的点滴;还有一本是安东尼奥尼自己的笔记《一个导演的故事》,他视其为“导演的涂鸦”。在这部短篇集的最后,有一篇名为《不要试着找我》的小说,而他自己现在真的消逝不见了。当然,他留下了自己的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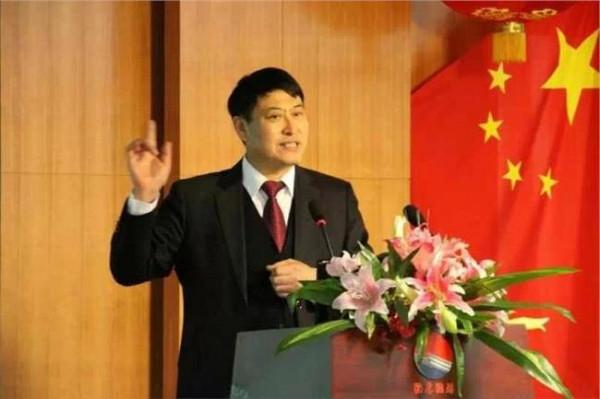

![>肖锋新周刊 [40P]中国新闻周刊肖锋/中国新闻周刊](https://pic.bilezu.com/upload/d/55/d55c90dc90fca295bdc6d4151b32db1d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