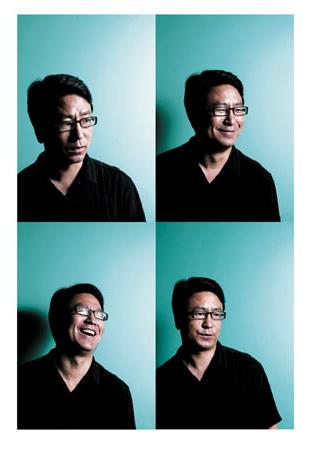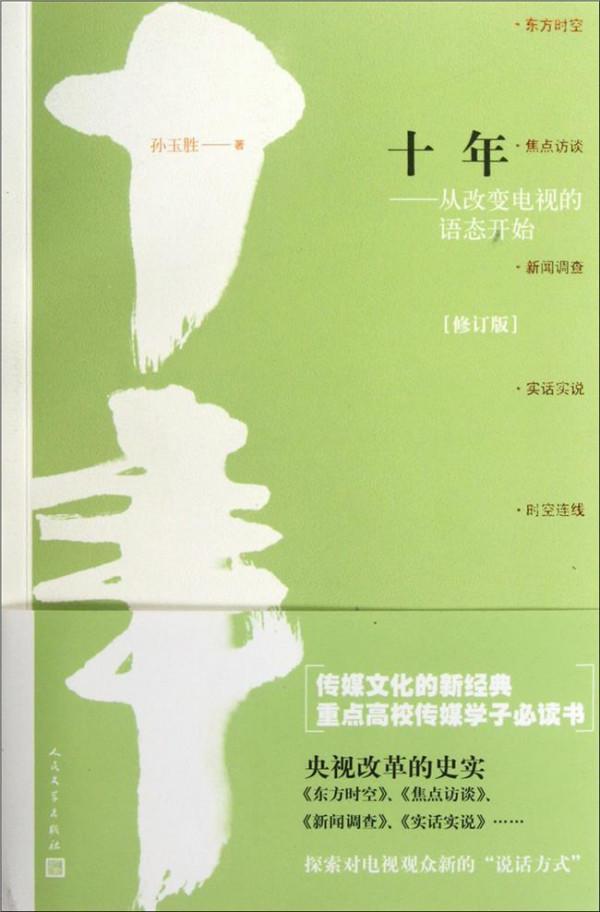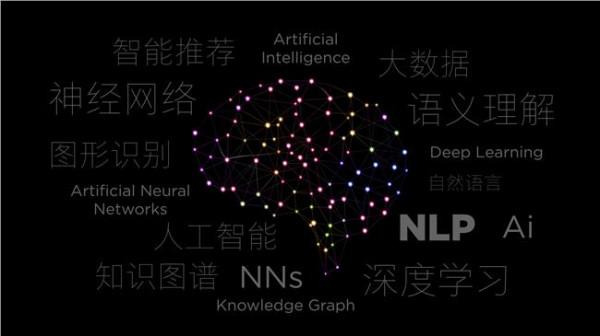孙玉胜电信 东方时空开启电视新闻改革 孙玉胜的路上十年
1993年5月1日,孙玉胜和他那30来人的“临时工”队伍聚集在中央电视台二楼新闻播出机房,忐忑不安地观看他们的第一个爱子:《东方时空》首期节目。当时,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个刚出生的“孩子”,会成长为一个巨人,并开始改变母体的面貌。
“朝发夕至,路上十年。”十年之间,一批制作考究、讲求深度、贴近受众的电视节目从《东方时空》以来,迅速获得不可想象的欢迎。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焦点访谈》早已成为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栏目之一,甚至成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东方时空》团队改变了高高在上的央视新闻节目,重新认识了电视媒体的“家用属性”并将电视节目还原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赋予它生动而丰富的形态。在改变中国最主流媒体的语态、使之接近现实生活之时,《东方时空》改变的是中国大众的思维方式。从此,“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和“让事实说话”成了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圭臬。大众通过最具权威性的主流媒体重新发现了自身,这是一场悄然的启蒙。
回首十年前的那个瞬间,已经成为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的孙玉胜说,他们当初只想把电视新闻节目“做得更好看”。尤其是他谈到当时一同参与那场改革的自己的手下时不是带着居高临下的慈爱,而是对默契友人的亲善和诚恳。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拿着自己录制的奇怪录像带来到他面前,从他那里得到默许,这是所有成功故事的开端。
孙玉胜非常清楚,《东方时空》的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十年前的一位伟人的一次南巡讲话和年底的一次会议(中共“十四大”);其他媒体改革的先行铺路;决策者的远见和魄力……,但是,最让他心荡神驰的,是年轻人追寻梦想时爆发的激情。
按照孙玉胜的发现,电视改革的规律有十年一轮的周期特征。他在其新著《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一书中认为中国的电视改革应该以1983年为元年,央视历史上的一些著名节目,如《丝绸之路》、《话说长江》特别是持续至今的《春节联欢晚会》都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从1993年开始的新一轮改革发端于早间和新闻,它使电视从业者的传播理念及其所制作的节目质量发生了飞跃,如《东方时空》等栏目的先后创办以及大型直播节目的运作等等。
2003年,以新闻频道的开播为标志,中国的电视似乎又面临一个新的改革门槛。在预测未来时,他就像回顾过去一样谨慎,也一样保持乐观。与内心深处的思维习惯进行斗争是如此艰难而迷人,自从他发现这个事实后,所有的终点都消失了,变成了起点。
访谈
问:《东方时空》开播至今正好10年,它的影响是否超过了你的预期?
答:超出了想像。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东方时空》开启了一个电视新闻改革的时代。当时我们只是想把电视新闻节目做得更好看,过去的电视节目、尤其是新闻节目可看性不高,非常呆板,不尊重电视特有的传播规律。现在看来,《东方时空》之所以能成为上一轮电视改革的标志,一个重要因素是其改变了传统电视的叙述语态。
也就是从《东方时空》开始,我们实验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比如表达的态度是真诚的,表达的内容是观众关心的,表达的语言是鲜活的,表达的手段是符合电视规律的,表达的效果是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等等。
如栏目还在筹备初期,就提出要变“新华体”为“中新体”,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变革。媒体和舆论要接近并影响受众,首先必须从语态上开始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这种力量所能产生的效应是我们过去所忽视的。
问:当时意识到需要这样的变革的人多吗?
答:从“语态”一词来说,我感觉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但是当时这个变“新华体”为“中新体”的说法是台领导提出来的,而且是大家的共识,这在我的书里说过。
对电视而言,改变语态不仅仅是文风的改变,更是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段的变革。电视对真实性的表现是其他媒体无法企及的,然而这个表现能力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却被忽略了。
问: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对电视真实感的追求的呢?
答:人们对真实的追求是与生俱来的。
现在国际上的电视表达趋势是新闻娱乐化,娱乐真实化。虽然我不同意那种把新闻娱乐化的理念,但是我们的新闻过去是太缺少生动性和鲜活性了。而我们从“真人秀”受欢迎的程度上可以看到真实感对人们的吸引力有多么大。
我国从1990年的纪录片《望长城》开始采用纪实的方式来体现真实感,《望长城》对中国电视节目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但是《东方时空》所做的事是把纪实的特点用栏目固定下来,给它栏目化了。
问:是什么直接导致了当时的节目形态的变化?
答:一方面,当时人们已经从传播学的角度意识到了过去的电视节目不考虑“受者本位”的局限性;其次,当时其他媒体改革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而且他媒体的实验已经产生了效果,比如报纸的都市化趋向和“大特写”报道,纪实文学的出现,广播的谈话互动节目(比如点歌)等等。在早期的新闻改革中,电视其实是落后于其他媒体的。
《东方时空》的出现是改革大环境的产物,1992年的南巡和十四大带来了各个领域的改革,电视当然不甘落后,电视从业者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特有的传播优势。考虑到改革风险和观众是否能够接受的问题,台领导将改革选在了非黄金时段。
其实,《东方时空》当时的关键在于集中了一批有对电视很有想法而缺少合适空间的职业化的年轻人,比如《东方之子》的制片人时间、《生活空间》的陈虻、《焦点时刻》的张海潮、《音乐电视》的王坚平,还有童宁、梁晓涛、孙克文……其实是一群年轻人成就了《东方时空》的表达方式和风格。当然,这和台里领导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它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
另一个成功的原因在于《东方时空》的用人机制——尝试招聘制,向社会招聘有才华的、有理想的编外人员。当时外部社会已经为此奠定了力量,一个是纸媒体、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有很多对电视感兴趣的编辑记者,另一方面就是院校和地方台培养的职业化人才。
许多这样的人才因为户口和编制进不了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把这个口子打开了,使这些充满激情的理想者们有了精神的家园,这当中的很多人现在都成了制片人。《焦点访谈》将这种招聘制正规化了。此外,制片人制也是从《东方时空》开始的。在事业的成长中,制度建设总是其保持稳定和持久的最重要因素。
问:在未来十年中您觉得中国电视将如何变化?
答:别的节目我没有研究,在新闻方面,过去十年我们解决了新闻报道的问题,特别是其中的调查报道和专题报道问题,如时效性问题,不仅追求“最快”,而且追求“同步”直播;此外,报道的丰富性问题,报道的深度问题也都有所解决或有能力和方法解决了。在上个十年中,特别值得总结的是解决了新闻报道的舆论监督问题,它改变了人们对社会问题报道的认识误区。
上一个十年对电视新闻改革而言是一个报道的时代,下一个十年的电视新闻应当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分析和评论的问题,要使其进入一个分析和评论的时代,这里面也有一个表达方式的问题。分析和评论的表达方式还有待探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以报道的表达方式解决分析和评论的问题。
另一个可能的变化就是正在探索的产业化运作。现在在搞数字电视、付费电视、制播分离也不再是一个敏感问题。上一个十年里电视剧实现了产业化运作,在下一个十年里,除新闻之外其他节目也将探索实现产业化运作的途径。比如说付费电视,观众必须付费才能获得频道的使用价值,这就使电视频道更具有了“商品”特征,它如何运作的问题就迫在眉睫了。
电视剧产业化使我们看到,产业化后的电视剧导向仍然是可以把握的。除了设定管理政策外,播出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购买符合国情、符合文化、符合政策、符合观众习惯等等条件的产品,而制作者自身也会充分考虑和满足购买者的意图。
问:网络对电视的影响在哪里?
答:从前我们传统媒体不报的消息,人们就不知道了,现在他们可以通过网络知道。现在有很多传统媒体的报道加速了。比如“南丹事件”之后,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开始同步报道突发事件了。
问:电视的真实性能够到达什么程度?
答:完全真实是很难很难的。互联网的出现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容忍了不真实性——我觉得这会有损于网络的权威性。而对传统媒体来说,不真实是巨大的敌人。最近披露的11名记者受贿的事是骇人听闻的,绝对应该遭到谴责。
问:《东方时空》作为庞大体系中的实验田,它曾经给你带来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答:刚开始是经费问题,后来节目成功了,广告收入花都花不过来。然后有过人才问题,也解决了。最终,栏目的定位和把握问题是最困难的。它必须符合电视新闻规律、符合观众需要、符合政策要求。比如舆论监督,我们也是一步步逐渐试验来的。
新闻的探索不能超越社会的发展阶段,过去有过这样的例子。我们的舆论监督是带有中国特色的,过去认为舆论监督是给政府出丑,现在则成了政府工作的一部分。这么大的国家,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们报道问题是想推动问题的解决,这在目标上和政府是一致的,是善意的。
所以后来国务院有了监督报道的反应机制,舆论监督完全成了政府工作的一部分,它有助于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本报记者 覃里雯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