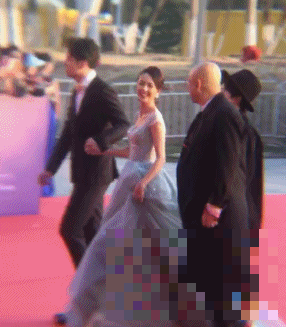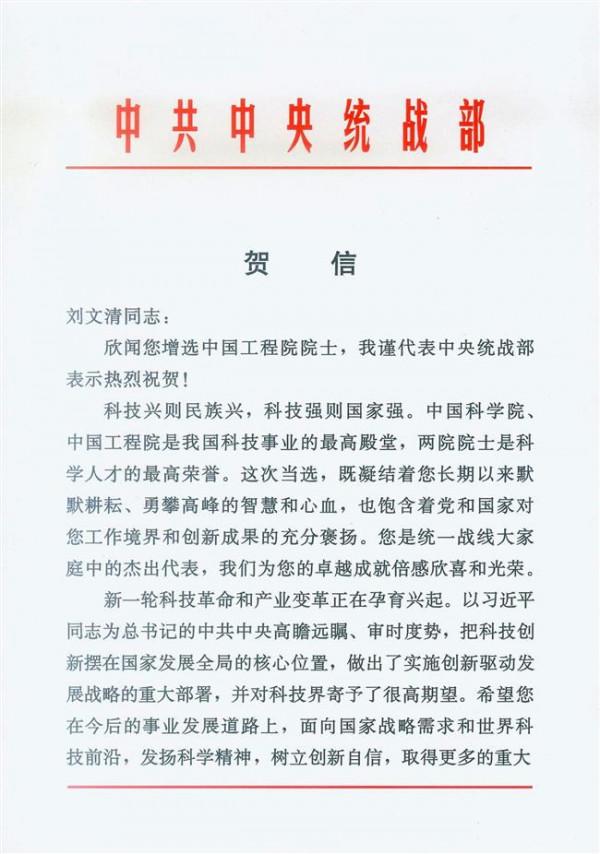孙大雨哈姆雷特 这是读了书后写的哈姆雷特 用的是孙大雨的译本
这里我将从一个分界线,两个世界,和三个阶段阐述我对Hamlet的经历的理解。 以父死母亡(这里指Hamlet所愿望的母亲形象的死亡)为明显的分界,Hamlet的世界被划分为两个。我不得不借用歌德的阐述来完整讲述我的看法。
“这个皇族的花朵,本是娇嫩而高贵的,在国王的直接庇护下成长,在他身上同时展示出来的是正义与皇室尊严的概念、善良与纯正的感情和出身贵胄的自觉。”“他致力国事,只是为了善良的人不受任何阻碍,永远善良。
”按我的理解来转述就是,Hamlet是被保护得很好的年轻人,他不曾受过世间的恶意中伤,罪恶的身姿从未落入他的眼眸,他的思量品行纯洁如处子。他不罪恶,因为不曾见过罪恶。但他又并非全然不知罪恶的存在,他有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辨能力,也有着天性使然的对与善恶泾渭分明的判断。
但是Hamlet天性没有也不必拥有热衷于仗义行侠的热忱,他生活在平静中也喜爱着这种虚幻的平静,“如果出横能够种植在他那仁慈的心灵中,至多也只是为了得体地区蔑视那些狡猾而虚伪的廷臣”。
与小人计较难免要弯下挺直的腰身,骄傲的Hamlet如何肯低下高贵的头颅倾听卑贱的思想?正人君子太擅于宽恕,宽广的胸怀难免为罪恶提供生长的佳苑。
然而现实之门在约定的时间内必然要向Hamlet打开,不管他有没有做好准备。父亲的死和母亲的改嫁产生怀疑,天成的白布上更易显现出略微的斑点。Hamlet的世界变了。最初,他说:“我不懂得什么叫‘好像’。
……它们只是一个人表演的姿态:但在我心中有无法表演的哀痛;这些都只是悲哀的服饰和衣裳。”无论Hamlet是否已经明白,他已经感觉到了这种自我的裂变。与鬼魂对话后,他对世界的怀疑变成了一种狂暴的谴责和批判“我要抹掉一切琐碎的蠢记录,一切书本上的格言,一切形象,少年时观察所所留下的一切戳记;……我该把这个记下来,一个人笑吟吟,笑吟吟,可是个坏蛋;至少我知道在丹麦的确是这样:” 这个极端敏感的灵魂看见了罪恶,就让自己看见了所有的罪恶。
他进入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这时,他怀疑所有的一切。 “这世上本没有什么好跟坏,只是想法使它那么样。对于我这是一座牢狱。”Hamlet发现这个世界一切如常,但是又完全不同了。
但是他没有最好准备,他还缺乏一种“履行职责的理智”,尽管他有“决心行善的欲望”。“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埋怨自己的“生不逢辰”。但他有知道自己不能再“关在个核桃壳里,而把自己当作个无限空间之王”因为他会“做那些个恶梦”。
Hamlet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履行这个责任。因为“每个责任对他都是神圣的,”于是他只能用疯癫去阐述自己对世界的恐惧。对于爱情,他质问“因为美丽有力量很快地使贞洁变成个龟鸨。
而贞洁却没有力量是美丽变得像它自己一样:”他怀疑道德的力量,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能长久。“美德不可能在我们的老干上嫁接新知而使它改变,”他也怀疑自己“我能指控自己那么多罪名,我们都是彻底的坏蛋;”他要求自己依然是那个完美无缺的人,这样履行正义才是光明磊落的,他不允许自己使用恶的手段,于是他就不知道怎样去惩恶,去达到那个善的结果。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Hamlet情节,这世上善花如何开出了恶果,犹豫于借用恶的手段去惩戒恶果能否称之为善举。
高尚的Hamlet不屑于恶的手段,因而他拖延着,思考着,痛苦着。他明白自己“是个懦夫吧?因为我十足是个胆小鬼,没有一点点仇怨暗道被欺辱的苦,否则该早已把这个贼奴才的臭肉喂肥了空中所以的臭鸢:”善的逼迫和恶的担忧下,他怀疑人,怀疑自己,怀疑人生,才有了第三幕的TO BE的拷问。
这里插进另一个角色的讨论,叔王Claudius。
这个年长者明白这个世间的一切,并且总能自圆其说。他一开始就说Hamlet“心胸尚未磨砺,情志太浮躁,智虑过于简单。”他看重的是“势”和“理”,会“迅速作了决断”。他是始终懂得“天下没事物能永远同样地美好……想做件事,我们该做于想做时。
”所以他按照他心中的欲念夺得了江山与美人,因为他懂得“在这腐臭败坏的人间流俗中,罪恶的手镀上金能推开公道”。而他担心的,是“在天上……我们自己会被迫对自己罪辜的凶头暴齿去当面作证。
”却也能“且试行忏悔:它不是什么都能吗?” Hamlet也渐渐的明白了这一切。在第二阶段他寄望于自己判断的在“干什么绝对没有得救希望的坏事儿的当儿……使他……打入永不超生的黑地狱”。
而在叔王先采取行动后,他的大段独白“上帝……博大的智慧,……能前瞻后顾,……当与荣誉有关时,哪怕为一根草,也势必大大争一下。……我得一心去沥血,否则太可耻。”在海上历险归国后对Horatio说“轻率行事有时候对我们有好处”,这时候的Hamlet已经不再沉重于责任的神圣,他在现实中找到了一个可以自我慰藉的行动指南:“可见得冥冥中自有神灵为我们定成败,凭我们怎么去粗试。
”想象Hamlet是怎样从死亡之船脱身的,那还是光明磊落的方式吗?恶与善的冲撞中,Hamlet已经自认“无愧于天良去亲手还报他”(第五幕第二境),而皈依天命。
他超越了痛苦彷徨的第二阶段,走向了新的理解和平和。遗憾的是从文本阅读中我没有找到他的平和之路。 到这里,我的理解叙述完整了,但剩下一个疑问:无愧于内心果断于现实而仅畏惧上天的Hamlet是否已经是一个Claudius?我惧怕我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