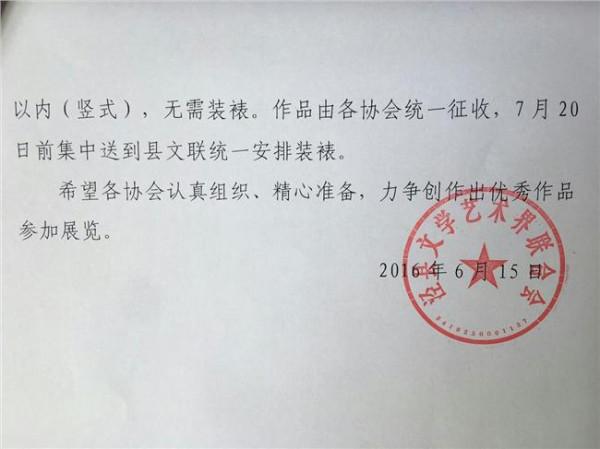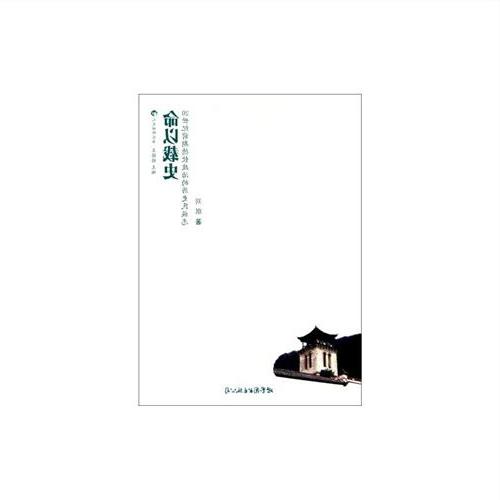王铭铭纪念邓正来 口述史王铭铭 王铭铭: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
还有不少需要解释的事,只好待未来解释。若集中于今天谈的口述史,则还是有一两句话要先说。以往存在的口述史研究,多用一个外在于被采访人的事件框架作为“切割人生”的手段,让被采访人谈他在某个大事件中的经历与看法。
不是说被采访人与大事件无关,而是说,这样做的话,口述史研究就容易忽视事情的另外一面——大事件中的经历,不过是人物的人生史的一个部分。只关注大事件,表明我们对于所谓“不起眼的人物”(被采访人)自身的意义体系并不尊重。
我以为,口述史亟待纠正其“切割人生”的错误,亟待对于“口述者”的人生史整体来展开研究。为了做这样的研究,我们不能将口述史视作惟一的可能。为了理解人生史整体,口述史不过是包括文字史在内的若干方法中的一种。
而对于我们理解人物的人生史,口述史与口承传统之间界线的模糊化,也有不少启发。我要反复强调的是,人生史与任何历史一样,既是人生史自身,又是一种“口碑”,一种“史德”,它在社会中有其丰富的意义。
“民改”
“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试史”研究计划动员了一批年轻学子,他们将对亲历20世纪50年代西南少数民族“民主改革”的人物进行口述史与文字史的综合考察。课题将围绕“民改”这个“事件”展开,属于“事件史”的范畴。不过,为了使研究不至于重复没必要重复的工作,选择以参与“民改”的当地头人与外来人物(如民族学家和有关工作负责人)为主要“研究对象”。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事件的亲历者对于事件是否还会有清晰的记忆?他们所记忆的,是否比我们在文字史中所见的丰富?不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
然而,我认为,相比于漫长的历史,半个多世纪不算长;若无意外,事件亲历者当时正当年,现在处在老年阶段,记忆虽则可能模糊了,但“民改”这样的历史大事件,不可能没有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烙印,他们也不可能不深刻感受这个烙印的影响。
关于“民改”的起因、过程、结果,正式的文字记载至为大而化之,未能充分展现这个深刻影响了少数民族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活生生的历史动态”。这就使口述史研究成为必要。而侧重于口述史,也使我们能够将一个历史大事件放在不同人物——如土司、民族学家、工作队员、士兵、干部、商人、百姓——的人生史中考察,从其在人物人生史中的地位,来反观“民改”的历史相貌。
口述史不得已总是要从历史和人生的总体时间中切割出诸如“土改”、“文革”、“上山下乡”、“民改”这样的块块来,以便集中分析。不过,只有在方法上更尊重历史和人生的整体性,将之视作为“活生生的生命体”,才有可能真正做好口述史。
我们将采访的人物,可以说是历史中的幸存者,他们的生命记载着历史。将他们的人生视作一切,会发现口述史的一个新境界。尽管课题的起点是历史大事件,而该时间与政治史关系更为密切,但课题研究者若是能暂时地忘却“事件”,而将采访焦聚于人生,则所获资料将出乎意料地丰富,具有说明性。
这样的研究没有什么诀窍,“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从内心理解历史;对所研究人物的所有语音进行细致的记录,即使是语法、词汇、发音不准确,即使是言谈中为了表示疑虑、警惕、不屑以至虚伪的沉默,一一记录,都会有收获。
我敢断言,这个课题将触及的故事,都远比流行小说丰满,而研究者却不以写小说为己任。细致入微、不加修饰的记录,使我们不能成为小说家。但这却能表现我们对于历史和人生的起码尊重;能表示,这样的细节所堆积起来的人生,其意义与价值,值得从其最微弱的“语音”中得到理解。
为什么要选择“民改”?为什么今日我们对于理解、解释、分析这个事件会有如此激情?为什么关于这个事件,再小不过的叙说与感叹都值得记载?我自己有自己的激情,而这种激情与我的学术有关。我对西部少数民族研究的冲动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人类学这门学科里工作,我面对老一辈。那些老先生们,曾在20世纪30-40年代期间,投身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读中国人类学史,我感到,最令人振奋的,是这个期间在所谓“边疆”展开的大规模调查研究。
今天的中国人类学如何面对这一大笔学术财富?问题引起我的冲动。另一方面,也还是与民族学的研究有关。学科重建以来,学科的地位提升了,资源渐渐多了,但似乎没有看到比半个世纪前好的作品。比如,抗战期间在费孝通引领下的“魁阁”,所做的工作,出版的作品,到今天都难以超越。
部分是因为存在“魁阁”,所以我对费先生的作品和看法一直很关注,且发现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刚一恢复工作,便对西南民族研究颇关注,提出了有关“藏彝走廊”的概念。
后来,他提出被广为引用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说,实际上,这个理论的说法,就是从有关“藏彝走廊”的相对具体的思考中推导出来的。从“魁阁”那个关注乡土中国的时代,到“藏彝走廊”这个关注民族中国的时代,费先生经历了不少事儿,其中,人生的阵痛也是“常态”。
而其中显露出自身特殊性的经历,是跟少数民族的识别和“民改”息息相关的(费先生全面参与了“民族识别”,却在“民改”后不久失去了正常工作的机会)。
费先生他们这代人和他们的早期学生们如李绍明先生,在中国人类学以至整个社会科学中曾有高度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在海外人类学家看来,稍稍有其不可理喻之处,那就是,它曾与诸如“民改”这样的历史大事件相关联。如何理解人类学或整个社会科学曾经与 “民族政治”形成的关系?如何理解诸如费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所说的一切?对于解答这些问题,我有强烈的冲动。
从东南走到西南,跟随着前辈的脚印,我发觉,东西两端愈发密切关联起来的历史进程,是我们生活的大时代的一个具体表现,而我们这个阶段的人生,无法不受它的影响。
我不认为“民改”这样的事儿,便是一个阶段中人类学研究的一切理由,我不相信,参与、亲历这个事件的人物,不在受到它的巨大影响的同时悄悄摸索着独立思考的路子。我相信,对于“民改”进行人物人生史的口述史调查,能将我们带入一个远比我们的想象丰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