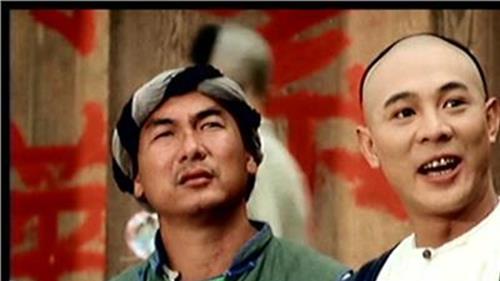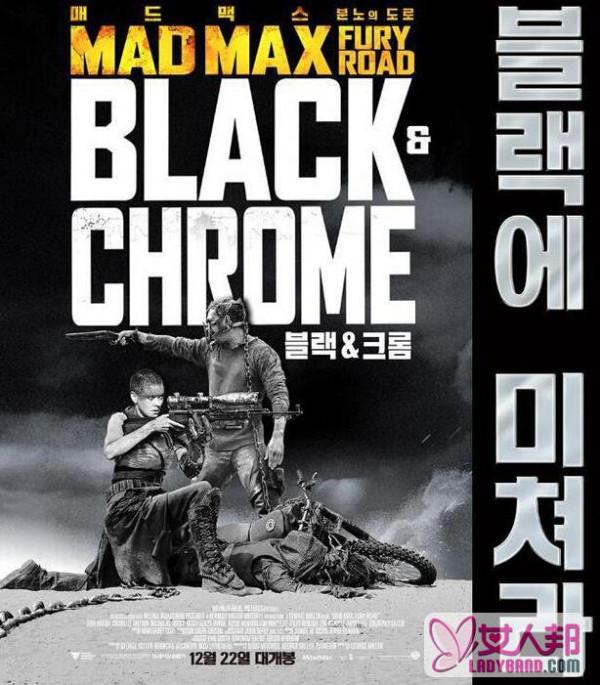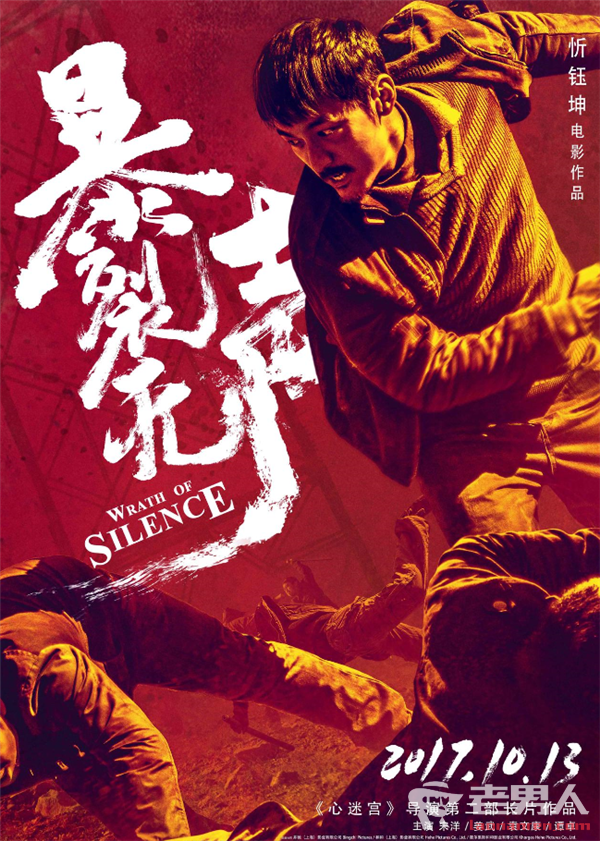《窃听风暴》导演出新作了,这是真实的胜利
获200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窃听风暴》刻画了精准的历史细节和让人信服的历史环境,在方寸之地内尽可能还原东德时代的历史原貌,但它并非基于真人真事改编。
《窃听风暴》(2006)
阔别大银幕多年,在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的新片《无主之作》中,他强调:「所有真实的事物都是美好的」,难道不真实的事物就不可能美好吗?当然不是这样。
《无主之作》借鉴了德国著名画家格哈德·里希特的生平经历,但电影故事仍然是虚构的,真实的是历史氛围,是时代特征,是人心的趋同和异变,并非剧本本身。
《无主之作》(2018)
1937年7月19日的慕尼黑,一场被称为「堕落艺术展」的吊诡展览正在此地开幕,展出从32家博物馆征集来的超过650件作品。这次展览的规格极高,规模宏大,包括毕加索、蒙德里安、康定斯基、恩斯特·巴拉赫在内的名家皆有作品入选,在多达12个城市巡回展出,却从未被视作一种荣耀的象征,而是成为德国艺术界大「清洗」进程的开端。
《无主之作》就在「堕落艺术展」的展会上拉开帷幕,只是将舞台移往格哈德·里希特的故乡德累斯顿。还是孩童的主角库尔特·巴纳特有一双充满好奇之情的蓝色眼睛,他牵着伊丽莎白阿姨的手,站在参观者的前排,目不转睛地聆听讲解员解释这些画作因何毫无价值。
讲解员对现代艺术家眼中的「真实」嗤之以鼻,把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称作视力障碍。他指着康定斯基绘制于1921年的无名画作,大加挞伐,其态度之轻蔑必然影响到天真纯稚的库尔特。
失望的孩子注视画作,声称自己还是不要当画家了。久远之后,当第三帝国的时代终结,柏林墙的倒塌也既成事实时,他一定还会记起伊丽莎白的微笑,记起她凑近的低语:「别告诉别人,我还挺喜欢它的。」
从外表上来看,伊丽莎白是堪为模范的完美日耳曼人,金发、美貌、血统纯正、身材高挑、总是面带笑容。作为人群中的宠儿和焦点,因为外貌出类拔萃,在希特勒访问德累斯顿时,甚至有幸为元首送上花朵。她是应该兴高采烈的,这是何等难得的机遇,然而,凝望远去的车队,虽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她的神色也难掩心中的天人交战。
赤身露体的伊丽莎白坐在钢琴前弹奏,以一种近于说教的态度叮咛身后避开视线的库尔特,「不要把目光移开,永远不要把目光移开。所有真实的事物都是美好的」。
她似乎在微笑,又似乎对自己的言语感到不知所措。实际上,伊丽莎白的失常和困惑全来自于能看透事物本质的她无法直视眼前的真实,或者说,是第三帝国的子民罹患群体性癔症的真实。显然,纳粹主义才是此时此地的真实,真实并不总意味着美好。
看还是不看,这是个问题。库尔特用手挡在自己的眼前,是不想还是不忍看到那个被救护车带走的身影?世界在他的目光中渐渐虚化、失焦,他的确没有移开目光,但他正在看着的世界,就一定是真实的吗?
189分钟的《无主之作》跨越了约30年的时间,从纳粹的崛起到东西德的对峙。其中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意识形态的交锋却是更为错综复杂的三次,每一次都天翻地覆,彻底推翻前一次的论断。
库尔特的家人将十分公平地死于三方之手,他所笃信的艺术形式将被一再否定,从现代主义又回到现代主义,即使成功逃往西德,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校学习,照样无法避免地陷入艺术创作的瓶颈。
「一个人只要宣称自己是自由的,就会同时感到他是受限制的。如果你敢于宣称自己是受限制的,你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如果说,在《窃听风暴》中,最强大的是对自由的信念。《无主之作》同样珍视自由的宝贵之处,生育权是自由,艺术创作的权利也是自由。
终于拥有创作自由的库尔特依然参透不了存在的意义,除了像西班德教授那样顺应时势的人,那段血腥而悲惨的国家历史几乎困扰着战后的每一代德国人,面对不可磨灭的创伤,他又能够责怪、怨恨谁呢?
当库尔特为「无主之作」下定义时,不是在说作品无凭无依,他觉得只有放弃选择和立场,否认由过往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定义的身份,才能寻回他口中真实的和谐。
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些作品都反映着他的人生经历,都体现着「我」的存在。也许最有趣的地方是,现代艺术的本质就是「我,我,我」,那么,也就永远不会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无主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