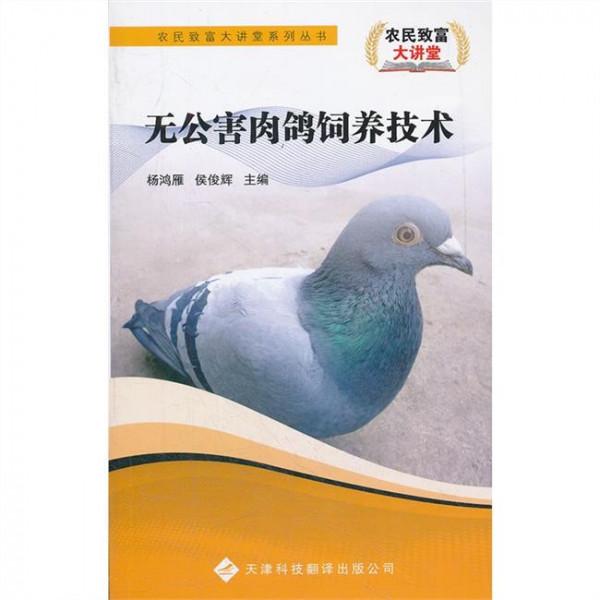张小燕诗词 【记者专访】张小燕、蔡诗萍的专访 ( 2005年2月16
张小燕: 今天很高兴请到余大师,能够一睹您的庐山真面目。 拜读过您的许多著作,也看过你的照片。但我还是担心大师坐在这里感到太枯燥,于是找来一个年轻的作家,他的名字也很有诗意——蔡诗萍先生。 蔡诗萍: 还是余秋雨先生的名字更有诗意,也比较传奇。
《借我一生》的书里提到,有人问余先生这是否是笔名,他回答:不,是真名,而且是不识字的祖母取的。 余秋雨: 名字是随手捡来的,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秋天,正下着雨。 张小燕: 我们今天是电视访谈,由此想到,当年您在大学里做院长,是不是觉得上电视和做学问这两件事并不冲突? 余秋雨: 估计你看到了有关我的一个争议。
好些年前,我刚刚在电视上出现,就有不少人在报纸上批评,说著名学者不应该上电视。
理由是,电视太低俗,不是学者们该去的地方,学者应该坐冷板凳,在家里安安静静地钻研学问,不能分心。 这似乎是好心,但我还是觉得奇怪。既然电视不是学者该去的地方,你们怎么看到了呢?可见你们自己也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那时我上电视,是担任“国际大专电视辩论赛”的评委。这个节目很冗长,等到我讲评时已经是午夜之后,连我自己也没有看到。我想,这几位批评我的先生直到午夜之后还在看电视,可见已经离不开电视了。
把自己已经离不开的东西硬说成是低俗,这就是中国文人的虚假。因此,我不是反对他们对我的批评,而是反对他们对自己的虚假。 当然,这还牵涉到一个基本理念:文化要不要被传播?近代以来,世事巨变,中国文人闭门造车地“钻研”了百十年,有没有“钻研”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出来,提升中国的世态人心? 他们一反对,我倒是认真了,觉得所有昨天留下的文化禁忌,正是中国落后的文化原因,我必须花力气来突破。
结果,反而使我更多地上电视了。
直到今天,虽然总还有人把辛苦的文化传播者说成是“作秀”,但是绝大多数有文化良知的人已经不再反对学者上电视了。 张小燕: 每次文化突破,总有人当烈士,死在众人的枪口之下。没有牺牲的,就成了先驱。
蔡诗萍: 这种情况,在台湾也差不多。十几年前如果有学者上电视,也会与您一样,被批评为“不务正业”、“爱出风头”。现在情况变了,一些青年学者宁可追求自己在民间传播中的专业形象,而不在乎大学里那一套层级森森的繁文缛节。
台湾游乐场里有一种游戏,人们拿着槌子,看哪个洞里先冒出头来就朝那里打下去。在社会改革中,中国人总是习惯于一起敲打先冒头的人,后来大家都学会冒出头来呼吸了,却忘记了那个被敲打得满头包的人当初为什么被敲打。
张小燕: 余大师一生一直在做先驱者的事。在连饭都吃不饱的乱世,就开始钻研中外典籍;在大家都在躁动不安的时候,就埋头几年写作学术著作;在大家都在争着当官的时候,却辞职了;在大家都挤在文化界里你看我、我看你的时候,却选择了远行考察 …… 余秋雨: 您千万不要叫我“大师”。
年轻人叫着玩玩倒也算了,小燕姐您是台湾主持人中德高望重的领军人物 …… 张小燕: 在中国大陆最缺乏知识的年代,您把人类历史上一些很重要的文化艺术经典一点一点地进行诠释和介绍,并变成一部部教材——就凭这一点,我就有称呼您为“大师”的理由。
这种特殊的学术成就,是否与您后来被任命为院长有关? 余秋雨: 有点关系,但不是主要原因。
我担任院长之前,国家文化部在我们学院举办了三次民意测验的投票,我都是第一名。主要原因是,当时文革灾难结束不久,全院的教职员工还都清楚地记得我在灾难年月的表现。我是一个坚决反对造反派的一切暴力行为,而且绝对不会参与整人的人。
当时的民意测验,最在乎的是这一点。 张小燕: 您受到人们尊重,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您有很大的学问,但您的表述却能如此打动人心。一个大学者,一般总会给人一种遥远的、了不起的印象,而您却能这样地接近人。
蔡诗萍: 余先生确实有这个特质。学者出身,有很好的学术成就,可是在文字上非常具有亲和力。这种特质我很好奇。 我在读《借我一生》时,一开头就非常震撼。
您描述父亲停止呼吸后,您用手去合拢他的嘴,才发现自己与父亲的肌肤从来没有亲近过——看到这里我吓了一跳,我也是这样,别的男人也是这样!您一下子触及了中国文化中的父子关系,却又那么感性,让人瞬时直觉。
从书中我也知道了您对读者具有这么大的亲和力的原因。您不像一般文化人那样只从知识里去接近世界。从小,您母亲让您对大地、生命、责任产生亲身体验,后来您把这种亲身体验延续下来了,包括体验世间最丑陋的部分。
张小燕: 把读者引入对历史的共同体验很重要。我们都体验过两岸隔绝的悲剧。我母亲离开大陆时才二十二岁,四十多年后才回去,看见自己的哥哥已经拄了拐杖,白发苍苍,我就亲眼看到了这个历史性的情景。 您亲自经历过文革。
但您书里的描写,好像与我们台湾人原先听说的不大一样。好像没有像原来听说的那样可怕,但细看下去又比听说的更加可怕 …… 余秋雨: 海外对文革的传播,过于着重于上层政治斗争的层面,以及一些著名人物遭遇。
这与二十几年前官方对文革的诠释有关,主要代表了一批老干部的立场。 我一直不同意这种诠释。一些上层官员,包括有知识分子背景的上层官员的“打倒”和“平反”,他们所属的政治派别的争斗和起落,根本不能概括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历史,更不能概括文革灾难。
他们一度被“打倒”,当然也值得同情,但他们几年前也许以更不堪的手段“打倒”过别人。既然成了政治人物,而且在不民主、不透明的构架中主动地成了政治人物,就要承受这样的政治风险。
在我看来,文革之所以成为一场灾难,是放纵了民间的恶,形成了人人都可以互相揭发、互相造谣、互相批判、互相审判的社会风气,使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更严重的是,这场灾难在文化人中培植了一大批整人、毁人的专家,并把整人、毁人当作了一门专业,娴熟地找借口、凑伪证、造声势,成为一种延绵至今的负面文化。
与此同时,民间也有不少星星点点的善良火苗与之相抗衡。这种抗衡并不表现为抛头颅、洒热血式的勇敢,而是拒绝同流合污,努力救助他人。
有的人,虽然同流合污了,却还良知未泯。因此,在那个灾难深重的岁月,还能处处遇到温情,仍然是冷暖人生、啼笑岁月、真实世间。 只不过,在灾难岁月,善的理由很少,因此常常破碎;恶的理由很多,因此常常得势。
甚至到了文革结束,很多文革打手,继续整人,而好人讷讷无言。 好人确实找不到自辩的理由,因为他们从来分不清“两条线路斗争”中的归属,每天只会想着刚刚被抄家的老师和即将要饿肚的家人。
张小燕: 文革把很多人心中的魔鬼挑动起来,却也有天使存在。他们或许与我们素不相识,却愿意伸出援手。我的一个亲戚在大陆另一次政治运动中千钧一发,却被一个人救了。 蔡诗萍: 美好的东西无处不在。
过去台湾曾有很大的批评声浪针对鹿桥先生的《未央歌》,因为那本书写到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有大学生在谈恋爱。其实鹿桥先生哪有写错? 余先生《借我一生》这本书提醒我们两点:一,对文革这样的灾难,我们不能一刀切;二,那个灾难之所以形成,恰恰是因为一刀切。
在文革中,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分割黑与白,革命与反革命,人人都可以被批斗;后来,再用一刀切的办法来分割文革中的政治是非,延续了同样的毛病。 您相信人的灵魂,相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人性总该有很大的活动空间和理解空间。
这与大陆文化界依然很普遍的极端化思维有很大的区别,大概也是您经常遭致他们批判的原因。 张小燕: 其实,这恰恰是您最感人的地方。您即使在灾难中也相信人的真诚、善良、坚持,如果一时找不到,就由自己率先这样做,不管遭受多大的误解。
我发现,您的太太马兰女士也是这样,因此她最理解您。 马兰是内地非常有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十九岁成名,拥有广大的戏迷,包括在台湾。
我看到一些资料,前些年,正当大陆一些人在媒体上向余大师投污的时候,她站出来说:“我的人生因他而完美,嫁给他没白活。” 马兰还这样说您:“他是一个严格的人,会从文化和美学的角度向我提一些更高的要求。
我也用我的方式参与他的工作,他的每一篇文章,我都是第一个读者。我会用不带演员腔的自然声调念一遍,他闭着眼睛在那里听,听完就拿回书房去改。” 这实在是令人羡慕的家庭生活。但是,只要有需要,她也愿意暂停这样的生活。
例如余大师决定亲自冒险去考察人类各大文明时候。她可以陪一段路程,也可以在家里等候,虽然牵肠挂肚,坐立不安,每天祈祷 …… 余秋雨: 我很奇怪,您是从哪里看到她说的这些话的呢?我居然完全不知道。
张小燕: 不知道?我好像到您家去翻过了箱子一般清楚!您听,她还有这样的话:“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吵过架,但他也有急的时候,有一回他在电话里生气了,说我不该这样说,他非常不想听,就把电话挂了。
他让我自己去想,想完了以后再谈。” 余秋雨: 这件事我记得。这些年来,她越来越厌恶大陆文艺界很多人竞相演出那些奉承拍马、伪造精品、伪装繁荣的假大空作品,而整个机制又在鼓励这种风气,她就灰心了,决定彻底放弃表演。
我多次劝她:“我们的父母和我们自己经历过多少灾难,不也一次次熬过来了吗?为什么要彻底放弃?”她有时被我说服了,有时又看到了更多的丑恶现象,又要放弃了。这是我们唯一发生过争执的地方。在我看来,一个深受全国观众欢迎的艺术家,正当盛年就决定放弃演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所以我要她再想想。
因为我是一个很专业的戏剧学者,深知她在舞台上的演出水准,听到她的决绝言词心中就会产生很大的悲恸,为中国的舞台艺术。
所以,我有时会听不下去。 但是,在这件事上我又很佩服她。她从不考虑名利,从不参加层级太低的演出活动,但有时北京层级很高的领导来了,当地官员安排她演出,她也婉拒,因为她觉得艺术应该有独立的地位,不应该受官场驱使。
她的这种想法和做法,在中国文艺界,几乎是空谷足音。 张小燕: 她常常决定不演出,就像您常常不想再写作一样。 余秋雨: 我不想写作,倒是还有其他原因,例如盗版。我的书,在大陆十分之九是盗版,其中还有大量冒着我的名却不是我写的书,包括一些色情小说。
因此我只能告诉读者,我不写了,那些新的书名都与我无关,请大家不要上当。 另外,我也实在太厌烦大陆文化界那些永远都在写文章诬陷名人的人,厌烦媒体对他们的宠爱,厌烦法制对他们的纵容,因此,不想再厕身其间了。
但是,我刚刚有这个想法,那些人又针对这个想法大肆毁谤,真可以说是“毁人不倦”。 蔡诗萍: 我相信你从心底里不会在乎这一切,因为你所经历的都是一些很勇敢的人生故事。
连女性,您的祖母、母亲和妻子,都是那么善良又那么坚毅。 张小燕: 我已经非常确定,大师热爱的是坚毅的女性。您不会喜欢任何软弱。所以,除了对那些长辈的尊敬外,马兰是您心中的最爱。
她也让您的人生更完美,正像她说您让她的人生更完美一样。 今天很开心能与您聊天。无论是您高深的学问还是优美的文学,都抵不过您所倡导的善良、责任和坚毅。下次我如有机会到内地,您一定要让我和马兰见一面,我们肯定很聊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