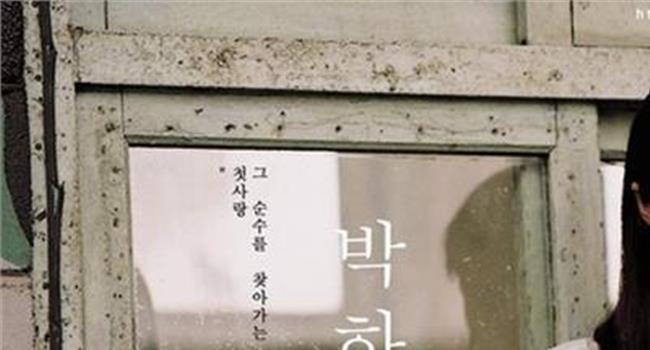毕赣访谈 在凯里 造一艘宇宙飞船|毕赣专访
除了《大鱼海棠》,最近还有一部影片颇受关注:《路边野餐》。如果说《大鱼海棠》围绕着情怀做足了功夫,《路边野餐》则显得”老实“得多。但导演毕赣凭借此片斩获的诸多奖项:金马奖最佳新导演、金马影展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人单元最佳新导演,也为影片赚足了期待。
这个出生于89年的年轻导演,在电影中展现了一种超越年龄的思考面向。相信看过《路边野餐》的人,一定忍不住好奇:是什么样的人拍摄了这样一部电影?近日,书评君对毕赣进行了专访,请他谈谈他的创作、阅读、幻想、梦境与现实。
在凯里,造一艘宇宙飞船
文
利维坦
“伟大”并不是什么伟大的词汇,不是吗?
《路边野餐》是他的第一部剧情长片,接连拿下瑞士洛迦诺电影节“当代影人”单元最佳新导演奖及最佳处女作奖,南特三洲电影节最高奖“金气球奖”,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再回到那个场景:在第52届金马奖颁奖礼后台,有记者想让侯孝贤导演评价一下毕赣,侯孝贤指了指他,说了一句——“看他人就知道。”
毕赣在拍摄《路边野餐》期间工作照
他人沉默而可爱,譬如被问及拍摄期间最怕什么事情,直言两字:“怕死。”或者,被问到这段时间最喜欢做什么事情,脱口而出:“泡奶。”生怕记者没明白,赶紧加上:“给孩子泡奶。”
哦,明白了。
采访在酒店房间里进行,刚进去的时候,前脚刚走一个,毕赣在后面一脸严肃地摆手:“大爷慢走嘞~小弟继续接客了。”
心里一惊,抬头望了望他,俩人会心一笑。
也许因为这会心一笑,每次抛出问题、等待问题的短暂间歇,都会因为“能不能多说几句”的期待变得更加漫长一些。对于一个非传统电影学院系统出身,在大屏幕上使用贵州方言传递想象和经验的电影导演,辅以《路边野餐》略显怪诞的英文译名——Kaili Blues……
《路边野餐》海报
当被问及“你觉得这辈子你会完成一些伟大的事情吗”的时候,他答案是:“我已经在完成了。”
那从未完成的时刻开始。
毕赣,1989年6月生人,苗族,贵州凯里人,山西传媒学院08级编导专业毕业。身材不高,言表率真,爱打“实况足球”。据说拍摄《路边野餐》两个月期间总共经费不过二十万人民币,还时常“资金周转不灵”。演主角的是自家姑父和外公(俩人偶因演技问题争吵),其它演员来自于朋友,朋友推朋友又来几个朋友。
《路边野餐》最后的成片里有个40多分钟的长镜头,后来被世界各地影评人盛赞。长镜头涉及大量场景变化、场景间调度工程量大,不可控因素极多,可他回忆起来只是说当时坐在摩托车上拍“怕得要命,千万别死”。
和演员、工作人员们(一共也没多少个)蹲在路边一起吃盒饭,睡得少、睡不着,当集体士气低落拍不下去的时候还要鼓舞士气。考虑到受众群体会误读太多自己的表达,措辞里加上了很多“也许”、“可能”。譬如谈及这个情况的时候:“可能,我利用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吧。”
《路边野餐》剧照
年轻的时候谁没有点理想主义?
本科期间,毕赣曾打算撰长文批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努力观摩半月。现今再被问及对其电影的看法,先是盛赞了黑泽明“非常了解视听语言,包括剪辑的组接,结构的使用,选材。我从中学到了很多”。转而提及塔可夫斯基,一脸严肃:“这和塔可夫斯基不一样,他是真正推动了电影艺术。”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在自己注述电影艺术观念的著作《雕刻时光》里曾经这样提及:“人类第一次在艺术史上,第一次在文化史上,找到了一种直接留存时间的方法。同时,可以无数次地将这段时间投射到银幕上,再现并回到逝去的时光。人类获得了真实时间的模型。如今,时间一旦被看到并记录了下来,便可长久地(理论上是永久地)雕刻在金属盒上。”
毕赣曾经在一个加油站做过加油工。每次清早,当他还在睡梦中的时候,门外就有司机拍着门大喊“加油加油”。他对于这些未经历的事情有一种诙谐的好奇。当人们评价《路边野餐》是在尝试与时间——这个宏大、空无乃至有些无聊的命题进行对话的时候,他会严肃而真诚地表达他拍电影的初衷:“我完全没有办法描述时间。
这时就需要艺术,需要电影,需要这个媒介去沟通它。与它对话,与记忆去对话。我不知道它在哪,躲在哪个角落,是什么样的形状,是男人还是女人,是怎么样生命的体态。
电影就像是发给外星人的飞船那样,有一些灯光,有一些数字,有一些音乐,那是留给人沟通的。我需要这艘飞船,我需要我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词汇,用我的经验和它沟通。然而,我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它的反馈。”
《路边野餐》剧照
《路边野餐》里塞满了大段大段毕赣的诗作,其中有这么一段:“山,是山的影子 / 狗,懒得进化。/ 夏天,人的酶很固执 / 灵魂的酶像荷花。”这段话会在银幕上被念出,会被坐在电影院里的观众听见。他们会体验一种在银幕上还算陌生的语言——凯里话,或者贵州其它地方的方言。
《路边野餐》里当地地方电视台会用标准的普通话提及“凯里地区近日来有野人出没”,“野人”的段落也不止一次出现在电影的叙述中。现在的小镇青年即使不会来北京,不会去上海,但“全球都在同步,现在大家都去一样的网吧,打一样的游戏,穿一样的衣服。我觉得现在他们同纽约的青年也没什么区别。”
两者并举,更像是一场揶揄。这满是符号的世界。“凯里和北京、纽约,已经区别得越来越隐晦。纽约是一个符号特别丰富的地方,凯里逐渐也把整个城市变成符号了,真正、本质那层东西已经越来越难以找到。当我想找扮演芦笙(剧中人物名)的演员,就发现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个人了。”
Kaili Blues,这部电影的英文译名。《路边野餐》,这部电影里有很多的钟,很多的时间。
“诗意的操作就是要让空无从符号权力中升起——不是对于现实的平庸或漠不关心,而是激进的幻象。”(让·鲍德里亚,《艺术的共谋》)
毕赣还在念本科的时候,拍过一部叫《老虎》的东西——自认失败,“那个时候我还不大会拍电影”;获得过香港ifva评委会特别表扬奖的短片《金刚经》——“一部70多分钟的实验影像”。现在,他会和你说,“我拍电影的过程就是我学习电影的过程”。
被问及怎样看待自己“与传统电影学院出身的电影制作者的关系”的时候,他会望着你的眼睛:“也许我的诉求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是要学会一种生存技能,一门炫耀的工作,成为一名被人尊重的电影工作者。我的诉求和他们不大一样,我的诉求是成为一名科学家,去探索重力为什么可以产生这样的重力,探索时间为什么是这样的时间,或者人与人之间会产生什么样奇妙的事情。”
《路边野餐》剧照
彼时彼刻他并不避讳什么,他笃定地完成了过去,好奇地等待着未来。
下一部电影,暂定名《地球上最后的夜晚》,取自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的同名短篇小说;《路边野餐》,原本被他命名为《惶然录》,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同名作品;《金刚经》——不用说了。“直接找一个别人已经取得特别好的名字,拿来改改用用。”问到为什么要把《惶然录》改成《路边野餐》,毕赣解释:“是因为制片方……我就任他们弄了。”
电影里面有一辆摩托车的车牌是“2666”,数字凑巧和波拉尼奥的另一本巨著《2666》耦合。台湾一位记者注意到了,问他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这书我还没看,太长了。”“波拉尼奥是个吐槽大王,写一句话马上加个括号吐槽一下,而且特别不好好用标点符号,尤其是双引号。”
佩索阿呢?“很有才华。可是他如果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也许是一个微博发得特别频繁的人吧,他就不停碎碎念,需要找个地方发泄一下。”毕赣倒是发泄过,以前做婚庆摄影,拍MV,和老板吵架摔桌子走人,老板大吼着嘲讽他“才华有个屁用,能当饭吃吗?!”现在有了《路边野餐》,才华好像吃上饭了。对于这些,毕赣乐在其中。
毕赣(左)工作照
毕赣,一个诗人,一个导演。他的电影总是在尝试着恢复幻觉、恢复想象的权力。同时也鼓励空白、鼓励停顿、鼓励沉默和无意义。塔可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库布里克们普遍拥有能使观众沉浸其幻觉的能力,《追忆逝水年华》、《尤利西斯》、《没有个性的人》等作品毫无遮掩地直接书写时间与记忆。
“马塞尔·普鲁斯特用空间书写记忆,书写时间,这意味着空间是可以具体到文学里,具体到影像里。虽然他的记忆和我的记忆没有半毛钱关系,可是我时不时会拿《追忆逝水年华》来看一下,因为它实在令人着迷。”
在拍摄过程中,他会反复让大家相信“我们要拍的是世界上最好的电影”。当被问及“你觉得这辈子你会完成一件伟大的事情吗”的时候,他的回复是这样的:“我已经在完成了。我的高中老师,他教完了我们那批人,他就觉得他完成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他完全投入到了那种快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