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策纵与牟宗三 “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读周策纵《五四运动史》有感
研究“五四”运动的著作中,旅美华人学者周策纵先生(1916-2007)发表于1960年的《五四运动史》是较有国际影响的一种。此书因其多方面成就广受赞誉,如史料详实,视野开阔,分析深入,角度多样,尤其是对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思潮的互动关系的梳理非常细致。
拜读一过,收获颇多。阅读过程中得到的最大启发,是它使我对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思潮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有了新的反思。 按照通常的看法,“五四”运动从根本上是反传统的。
这也是周策纵教授《五四运动史》一书的观点。良史亦难完全客观。作者在书中就明显流露出肯定新文化、新思潮的倾向性,而对于当时为传统文化进行辩护的种种努力,则更多表达了怀疑和批判的态度。这种倾向性有时会造成其论述中的一些矛盾。
比如在介绍“五四”运动的主要思潮之一自由主义提倡个人自由,批判中国传统的以家为单位的社会和“家-国-天下”的观念对人个性的过度束缚时,他不无赞同地说:“当大多数国民意识到国家统一与强大的重要性的时候,一些新知识分子就倾向于强调个人主义。
他们坚持认为,不能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去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大多数新知识界的领导人认为,不能以国家的强大与民主(族?)利益作为最高的理想。
”(416页)然而在试图说明“五四”运动中期兴起的整理国故运动的消极影响时,他改变了这种个人自由至上的态度。他说:“虽然吴稚晖和其他许多反对整理国故的人没有认识到旧文化的价值,但问题在于:整理国故能够,而且确实会将青年人的注意力从中国急需的对现代科学的研究中移开。
”(446页)在他看来,科学研究是追求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青年人应该使自己的个人兴趣符合国家利益,投身其中;与之相比,对古代经典产生兴趣,在整理国故上投入精力,即使不是完全无用,至少也是不急之务。
前后两处,在反对传统方面是一致的,但前者认为个人自由不应为国家利益吞没,后者则认为个人自由应服从国家利益。 矛盾源于作者的一个潜在预设:启蒙等于反传统;传统的东西总是与启蒙背道而驰的。
从五四运动前期的状况来看,这一预设是合乎实际的。“五四”运动两大主题是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后者被视为达成前者的手段。应该说从鸦片战争开始,救亡图存对中国来说就开始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
伴随着救亡图存的努力,总会有观念的更新作为预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早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林则徐“开眼看世界”之际就已揭开了帷幕。然而在二十世纪之前的启蒙,多停留于观念的表层,并未触及问题的根本。
因而这之前的变法维新活动几乎总是以失败而告终。一直到1916年陈独秀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提出“此(伦理的觉悟)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的觉悟。
”整个社会才达成共识: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必须从伦理、哲学、艺术等层面上予以根本变革。促成这种共识形成的因素,一是对本国政治腐败和社会落后僵化的彻底绝望,一是国外新思想的大量引进。在五四运动前夕,中国舆论的主流是对旧道德、旧礼教、儒家学说的不遗余力的抨击,以及对西方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不遗余力的引进。
然而到了五四运动的中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欧洲在一战的战火中遭受重创,西方思想界开始对物质文明、科学万能等观念进行深刻的反思,柏格森、倭铿、罗素等纷纷将目光投向古老的东方。
这一信息被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带回了中国。变化之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思想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消化吸收,摆脱了初期的盲信盲从,开始把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进行一个客观的比较。
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是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和张君劢关于人生观问题的演讲引发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这两个变化促使早期新文化阵营的相当一部分人重新拾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
所有这些努力直接肇端了现代新儒家这一重要学术流派,此派思想的特征在于既认可民主与科学,又不放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念,力图寻找一条二者完美结合的道路,如牟宗三所谓“内圣开出新外王”。
这样一种思潮应该说是直接秉承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而来,它属于思想启蒙的另一种形式。然而遗憾的是,在本书中,作者把所有这些为传统文化进行辩护的企图都视为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反动,而没有视作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合理延伸。
倘若认可这么一种分析,则对于“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似乎也可以有新的认识。传统的观点认为,“五四”的核心之一是反传统,理由是它与民主与科学无法兼容并存,“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陈独秀语)。
然而通过后期持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学者的努力,我们似乎可以对这个观点进行一些修正:传统并不天然与“五四”的目标对立;形成对立的是那些僵化腐朽的成分。
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经过一番洗涤剥离功夫,是完全契合“五四”的目标的。 把“五四”运动放在下面这样一种宏大背景之下审视,也许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认识和理解这一复杂现象:任何一种有机事物(生命体)的存在,都有其内质,又有其形式。
内质是事物的内在生命;它的生发流行自然会使该事物具备某些形式。形式一旦成形,就获得了某种相对独立性:一方面它会为该事物的存在发展提供便利(如轨道)和保护(如外壳),一方面又会构成对事物的限制(如轨道)和阻碍(如外壳)。
一旦形式对内质的消极作用远远超过了其积极作用,妨碍了该事物的生机,变革就不可避免了。形式的东西愈顽强,变革愈剧烈。就人类社会而言,人的现实生活需求是其内质,观念、制度、器物等均是形式。
形式的东西再完善,也总有不再适应现实需求的一天。这是社会革命之所以发生的原因。“五四”所要完成的,正是这样一种破旧立新的工作。然而新的东西,不能凭空产生,仍当延续该事物的内在生命。
值得注意的是,周策纵先生在晚年修正了他的一些观点。在他1991年写的一篇应对林毓生先生关于五四反传统主义观点的短文《五四运动与传统的关系》中,他说: “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全反传统。胡适之先生提倡白话文,而白话文正是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其他如陈独秀、吴虞等人也都从道家、墨家等中国传统,找出了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东西,没有人能否认道家、墨家是中国传统的一支,即使由印度传来的佛教思想,也不能不算是近代中国传统的重要成分。
所以,光是要界定 “传统” 的意义, 便已经大成问题。 我认为, 五四时代的反传统,其实反的是“传统主义”。当时的确有些守旧人物相信凡是传统都是好的,五四知识分子所反对的乃是这种“传统主义”。
至于他们对儒家的批判,也并非全无道理。儒家传统也确实有些成分已经不合时代潮流,像陈独秀所批评的“父死, 三年不改其志” “ 、男女授受不亲” 等等礼法观念, 不能不算是儒家传统的一部分,如果依然坚守这些传统,现代民主制度便无从树立。
其实,西方的古代思想传统,其中也有很多不合时宜的东西,扬弃这些传统,并不就是要把整个传统连同其中精粹完全推翻。
五四时代所以激烈反传统,固然有点矫枉过正,但是当时的思想环境中,一般人的论调和心态,都是非常闭塞,在这种情况下,五四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批判,当然无法持平,而一定会走向激烈的道路。如果以此苛责五四人物,实在是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与时代需要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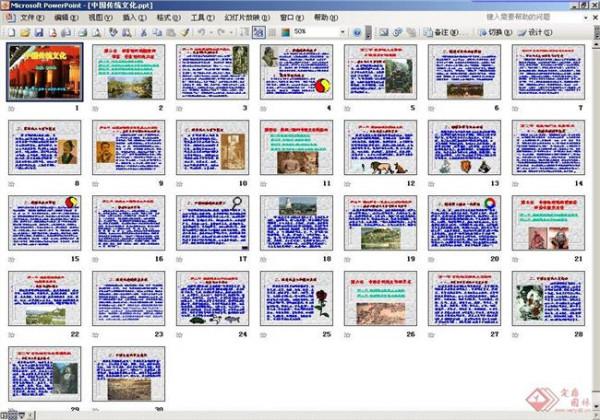














![周自齐被通缉 [图文]被遗忘的中华民国代总统周自齐](https://pic.bilezu.com/upload/9/d8/9d800c55f94e07d022e771fbfa4cc1e1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