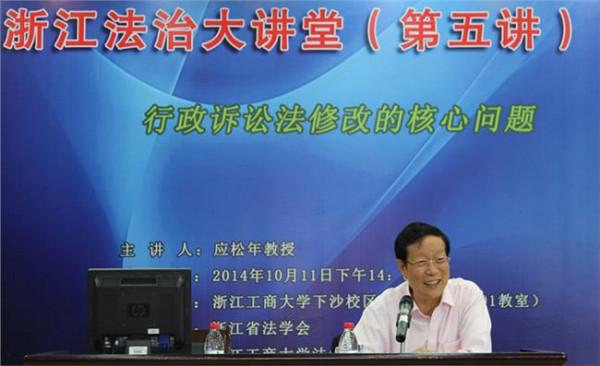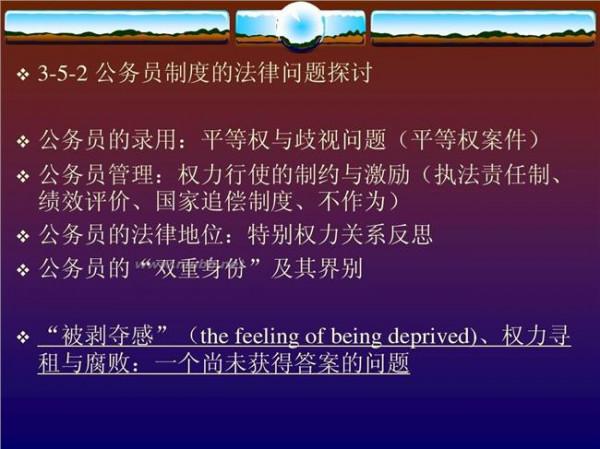应松年行政法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中国行政立法30年
在新一届政府推进职能转变、简政放权,进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当下,对行政权力的约束再度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行政许可法》早已出台,该法已经为行政部门审批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制,行政审批制度需要的是依法行政,严格执法。”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应松年日前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行政法是将“权力关进制度”的关键笼子之一,是“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力量权衡的天平。“应该凡是市场能管的事统统回归市场,市场管不了的交给政府,这就是政府职能。”应松年说。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强制法相继诞生,行政法已成体系。然而,行政程序法、行政收费法至今难产,其中曲折与拉锯可见一斑。
行政法系的立法过程,是政府权力收缩的过程,更折射了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的路径较量。
改革探路启行政立法路
文革十年内乱,全国上下缺乏行为共识。粉碎“四人帮”后,恢复社会秩序,为自由边界“划圈”,成为首要问题。
据《邓小平时代》记录,1978年12月,邓小平亲自修改其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发言稿,他向起草者列出讲稿提纲,其中第二条写道:“发扬党内民主,加强法制。” 而这不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及“法制”。
1979年2月,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长期主管立法工作的彭真复出。2月17日后的一周内,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法制委员会80人名单。彭真出任主任,胡乔木、武新宇、陶希晋等10人为副主任。文革后中国立法之路自此开始。
1986年,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宣部等单位参与的座谈会上,当时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顾问陶希晋提出了“新六法”主张。
“新六法”是针对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提出的概念。陶希晋提出:“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但不能没有自己的法律体系。应该建立一个‘新六法’。现在看来,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有了,缺的就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了。”
有了立法动议并得到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肯定后,陶希晋立即行动起来,着手筹备。然而此时百废待兴,人才成为最大难题。
应松年对记者回忆:“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基本没有人做行政法研究。‘文革’时期大学连法律系都停办了。五十年代时,曾有个别学者开始研究行政法,后来都改行了,到八十年代开始研究行政法时,都已请不回来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办公室原主任高志新自1985年底开始担任陶希晋的秘书,他这样描述当时行政法学人才的匮乏:“那时中国行政法学研究还很薄弱,各大院校还没有设立专门的行政法教研室,专门研究行政法的专家更是屈指可数。”
基于人才之缺,陶希晋于是提议成立行政立法研究组,由专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同志共同组成。这一建议获得了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肯定。
时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的江平,此前参与了民法通则的起草。因其在法学界的影响力利于研究力量的调配被陶希晋“看中”,据应松年回忆,江平起初不干,说“我是搞民法的,不懂行政法”。陶希晋最终说服了他。
1986年10月4日,行政立法研究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研究组共14人,江平为组长,罗豪才、应松年为副组长。小组成员包括朱维究、姜明安、肖峋、高帆、费宗袆、张耀宗、方彦、张焕光、王向明、皮纯协和郭阳。陶希晋、龚祥瑞等8人担任顾问。这20余人,对我国后来近30年行政立法的影响至今犹在。
顺势而为行政诉讼法破冰
行政立法研究组成立的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为“为重要的行政法提供毛坯”,即为立法提供草案。陶希晋最初希望是可以参照《民法通则》,制定《行政法通则》或《行政法大纲》。然而,行政法区别于与民法、刑法的特点之一,就是行政法由成千上万的行政法律规范组成,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典。
制定一部《行政法通则》有无可能引发争议。应松年将年轻学者和当时一批硕士生组织起来,共同起草了多份草案,先行交由陶希晋审阅。
“陶老认为立法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部法律所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抓准了问题才有写条文的可能,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草案被一次次地退回。”应松年回忆。
尝试行政法典的路子并不顺畅,但实践的需求不经意间打开了另一道门。
1987年1月1日生效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明确规定治安行政案件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修改了1957年版本中“治安行政案件只能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而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
这一变动对司法实践影响巨大。基于庞大的治安行政案件的基数,每年因此增加的治安行政案件数量不可忽视。
为此,最高法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审理治安行政案件与审理民事案件在程序上应有区别,例如把当事人提起的行政复议作为一审,而向法院提起的一审就成为了终审,如果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不服,可以申请复核一次,但不得再上诉。时间、程序等方面区别于民事诉讼的规定,为行政诉讼提供了最初的实践依据。
同年,行政诉讼法的契机也到来了。
1987年,对《民事诉讼法(试行)》的修改亦在酝酿中,其中涉及《试行稿》里的第三条第二款: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适用本法规定。即由单行法律规定的可以提起诉讼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按民事程序进行审理。
这一条款其实早有讨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主任顾昂然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1982年在起草制定民诉法时向彭真同志汇报,地方和群众有一种说法,“官告民一告一个准,民告官没门”。“彭真同志对此极为重视,并指示我们对行政诉讼问题进行研究。”于是,增加了上述条款。
而眼下《民事诉讼法(试行)》修改在即,第三条第二款何去何从?行政立法研究组召开专门研讨会,会上有学者提出:既然要改,何不制定一部《行政诉讼法》?
这一倡议得到江平的支持。江平认为,先制定程序法,再制定实体法比较容易。有了程序法后,在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才能对这一方面的法律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才会在制定实体法时更有把握。
法工委也对起草《行政诉讼法》的工作表示支持,顺势而为,研究组从1987年开始起草行政诉讼法草案。6月便起草了试拟稿。
10月17日,法工委把试拟稿送各地和有关部门征求意见,于1988年7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再一次发各地、各部门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成草案。11月,行政诉讼法草案在《人民日报》公布,广泛征求意见。
然而,行诉法立法的难不在研究组,而在于主管行政部门,对权力的限制与监督越大,反弹就越大。
“制定行诉法的阻力是很大的。特别是一些行政部门的同志当时有不同意见。1989年1月,国务院法制局召集30多个省、市、自治区政府和部分较大市政府法制局、处同志开会,座谈行诉法草案,会上反映了不少不同意见,包括对是否搞行政诉讼法都有不同意见。
有的说,如果公民可以告政府,政府还有什么权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不敢管了,会增加政府与群众的矛盾,影响稳定。有的甚至提出,这样会助长‘刁民’告状。有些是颠覆性的意见。”顾昂然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听了地方政府法制部门同志反映的意见,我深深感到问题严重,同时也越发感到制定行诉法的重要意义。
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行政诉讼法》。
1990年《行政诉讼法》正式生效。在此促进下,1993年时任总理李鹏在向人大作工作报告时提出了“依法行政”,其后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
化整为零“先解决市场最迫切的”
从立法小组成立到《行政诉讼法》颁布不到三年时间,《行政诉讼法》的迅速出台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旗。
“《行政诉讼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一个诉讼制度,也是一个‘民告官’的民主制度,而这正好适应了当时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应松年说。
而从《行政诉讼法》之后,行政法其他法律的相继问世,无不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依法治国、法治政府的建设,实际上和经济的发展是一体的,依法治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只能依靠法律进行规范。经济要快速发展,法治建设也不能滞后。”应松年称。
应松年回忆:“出台了《国家赔偿法》后,我们考虑应该制定一部行政程序法,但条件还不成熟。怎么办?干脆化整为零,先把对市场经济影响最大的几个行为单独列出来,把实体和程序问题先解决。当时列举一下,有四个: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发展影响最大的行政权表现在这四个方面。”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论及四部单行法出台背景时称:“由于违法处罚被撤销的案件增多,所以先搞《行政处罚法》;后来搞审批制度改革,于是又搞《行政许可法》。”
《行政处罚法》的出台姗姗来迟。1996年通过的这部法律明确了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与基本程序,成为行政立法上的重大进步。处罚法规定了处罚的种类、设定权和处罚程序,都为后来立法所效仿。在一般程序中,该法规定了专门的听政程序。这是听证程序在国内首次应用。
“(该法)强调了程序的正当性,强调了要听取意见,处罚的时候重大问题要进行听证。听证是第一次应用在中国,在起草这部法律时,费了好大的劲,很多人反对,但听证引入《行政处罚法》是民主机制的一大胜利,未来将到处开花。”应松年认为,“但是有一个担忧,引进来以后,我们没有根据不同的听证制度制定不同的实施程序,所以也出现一些问题。”
《行政许可法》则在《行政处罚法》得以实施的7年后才通过。
“经济发展,市场处于自由状态,在运行中市场有失灵处,政府要管制。在中国,还有管制过多,影响市场和经济发展的问题,要回归市场,放松管制,而许可法是调节政府管制的重要法律。”在应松年看来,这部法律的意义显著得多,“政府职能应该转变:一方面,市场能调节的政府不要管;另一方面,市场管不了的政府一定要管。这两者都要通过许可法的实施得到落实。”
《行政强制法》最晚于2011年6月30日通过后,四个单行法中仅剩下《行政收费法》。因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关联一波三折。尽管多有人大代表、官员与学者的呼吁,仅在2006年初看到一则新华社关于“全国人大将行政收费列入立法规划”的消息后,似乎再无“胎动”。
至于最早提出讨论的行政程序法,已经开始实践了“从地方到中央”的思路。
2008年10月,我国首部规范行政程序的省级规章《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颁布实施,从源头对行政行为进行了规范。继湖南后,山东省在2011年成为第二个行政程序立法的省份。目前,重庆等地进行的相关工作也在讨论研究中。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和增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进一步加强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执政,成为当前法治建设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应松年认为:“从行政诉讼法开始,中国正向着完善行政法制建设的轨道前进,而行政程序法应成为中国行政立法制度建设的‘收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