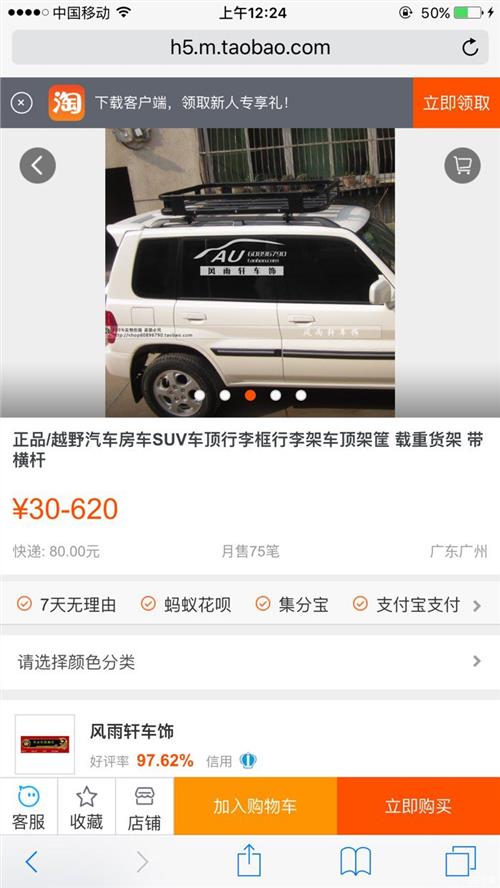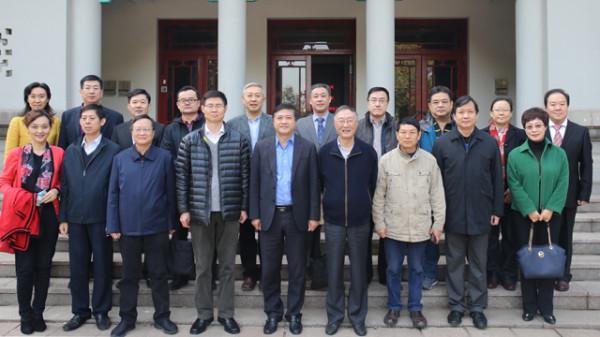哈佛教授:专注力,获得一种与岁月对抗的力量
哈佛教授:专注力,获得一种与岁月对抗的力量
可能心理学
“时光无法倒回。每个人都会老去,青春逐渐被岁月腐蚀成记忆。慢性疾病的警钟已经敲响,我们的健康和力量都在消退。一旦疾病缠身,我们将自己交给现代医学,祈求最好的结果。在岁月面前,我们无能为力,唯有平静的接受命运。但是,果真如此吗?”
在《倒时钟》的序言中,心理学家艾伦·朗格(Ellen Langer)这样写道。朗格教授今年63岁,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获得教授席位的女性。在美国心理学界,她是一个异类。一件小事可以说明她的异类程度:
去年夏天,一个朋友给她讲了多年前在印度的一次奇遇。他们在路上遇到一位宗师,请路人一起拍了照。他们用两台相机,拍了两张照片。但是,当照片洗出来以后,站在中间的宗师却不见了。
一个科学家似乎不该相信这种灵异故事,但朗格教授却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博客。她说,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个故事不可信,或者无稽,是因为他们思维封闭,没有向可能性开放。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朗格教授用一字之差来解释她的研究与传统心理学之间的差异:传统心理学研究的是“什么”,而她研究的是“可能是什么”(could be)。
她将自己的研究称为“可能性心理学”,不是描述普遍的真相,而是寻找个别的可能性。在社会科学中,与实验假设不符合的数据会被视为噪音,比如在研究年龄与记忆衰退之间的关系时,一个记性极好的老头往往被忽略掉,但她研究的重点恰恰是这个老头,因为这个老头身上包含着同样真实的特质,是人类思维中尚未被发掘的潜力。
朗格教授热爱网球。年轻的时候,她摔断了脚踝,医生说她从此会瘸腿,再也不能打网球了。但现在她双腿健康,仍然在打网球。30多年“可能性心理学”的实践,使这位心理学家将身体和心灵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度过了一段非凡的岁月。她觉得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她不敢尝试的。当别人告诉她“不”的时候,她一定会反问一句“为什么不?”。她50多岁开始画画,画她的朋友和狗。她不从素描的基本技巧学起,而是让线条引导自己,关注当下的体验与愉悦。现在她的画正在纽约最好的画廊里展出。
什么是专注力
“可能性心理学”的第一个假设是,我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或者能变成什么?一切皆有可能。但人是**惯的动物。我们如此容易被僵硬的世界观、惯例、偏见或者刻板印象所麻痹,我们的很多行为往往是先入为主、不假思索,或者想当然的结果,而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或者认知过程。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知道,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朗格教授做过一个“复印机”实验:几个人在排队复印东西,实验者问前面的人能不能让他先复印。只要这个实验者给出了理由,人们通常都允许他插队。有趣的是,这个理由本身是否合理却并不重要。无论你说“对不起,我赶时间”,或者“对不起,我想复印文件”,人们的反应是一样的。
“并不是他们没听见你说什么”,朗格教授说,“而是他们根本没意识到你说了什么。”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都是像复印机实验里的那种“自动”状态下做出的。比如把自己锁在车里,或者把袜子扔到垃圾箱里,而不是洗衣筐里。威廉·詹姆斯讲过一个关于奔赴晚宴的故事:主人公宽衣解带,开始洗漱,最后居然**睡觉去了。
“所以,我们需要时不时的停下脚步,思考一下我们正在做什么,在某个情境下是怎么反应的,为什么会这样反应?还有没有别的选择?”朗格教授说。
这就是所谓“专注力”(Mindfulness)。在她的学术生涯中,这是一个核心概念。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专注力”其实是一种很简单的实践——留意新事物,积极寻找差异。无论是关于你自己的,还是关于周边环境的,无论这个新事物很傻,或是很聪明,只要它是新的,是不一样的,就会将你置于“当下”的状态,让你对人和环境重新敏感起来,向新的可能性敞开,形成新的视角。而那些我们多年来称之为“智慧”的东西也会变得可疑起来——事实上,在她看来,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质疑的。
弗洛伊德曾说,“我们知道通往神秘智力世界的第一步就是去发现使混沌万物井然有序的最基本的准则、法则和法规。通过这种脑力活动,我们简化了这个充斥着现象的世界,却不避免的扭曲了世界的本原,尤其是当我们处于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时。”
为了适于生存,我们的脑海里保存了无数的规则与分类,以快速有效的指导当下的行为。这也是文化对人的教化功能——通过传达“绝对”的概念,我们的文化得以代代相传。这无疑带来了稳定,但也让我们付出代价。因为很多时候,情境已经变化了,我们还一如既往的坚持着那些规则和分类,不加思考的运用它们。
从这个角度而言,“专注力”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它并不意味着否定,而是存疑和追问,从传统、权威、成见、惯例、约定俗成中,收复自己的头脑,对塞给自己的信条问一句“真的吗?”、“为什么?”、“万一呢?”
朗格教授向我说起年轻时的一件小事:有一次她在跑马场,有人请她帮忙照看一下马,因为他要去给马买一个热狗。她当时觉得这个人的脑子恐怕出问题了,马怎么会吃热狗呢?但是当他拿着热狗回来的时候,那匹马果真津津有味的把热狗吃下去了。
这件事情给她很大震动,马不吃肉的结论到底是怎么得出的呢?多少马参与了测试?谁决定用哪些马?给马吃了什么肉?“马不吃肉”的结论背后本来附带了许多的条件,但我们却把它当成一个“绝对的真实”接受下来,然后再也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传统医学的问题也在于此。医学是一种不完美的科学。它能提供的只是概率,一种抽象的数学概念,但到了病人那里,却经常被作为唯一的正确答案接受下来。事实上,任何一种疾病,一旦落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性,没有一个人是概率,没有一个人是“大多数”。
“我并不反对传统医学”,她在《倒时钟》中写道,“我只是反对对医学测试和医生的无条件信任与依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无意识状态——我们太容易接受一种疾病的标签了,比如癌症、抑郁症。”
一个患抑郁症的人经常认为自己一直都处于抑郁状态,因为抑郁症是一种“慢性疾病”——这个词暗示了一种不可控制的长期性。到底多长时间才算“慢性”呢?真的无法控制吗?事实上,很少人是“一直”抑郁的。即使有这样的人,他每天抑郁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如果他有意识的把一天的心情记录下来,就会发现,一天中有很多时候,他是不抑郁的,或者抑郁程度低于其他时候。这样,他就有了“抑郁”的数据和“不抑郁”的数据。这种比较会使抑郁变得不那么绝对和可怕。他会开始问自己,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抑郁呢?有没有可能避免那些让人抑郁的事情?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我们中的绝大部多数人只使用了很小一部分潜力。只有在某种建设性的压力或某种特殊的场景下,比如伟大的爱,宗教热忱,或勇气之战——人们才可能去拓展自己创造力的深度和广度,发掘沉睡在我们内心巨大的生命能量。”
在朗格教授看来,人类的潜能很大程度上是被“无意识状态”(Mindless)抑制了。“一旦你相信某件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你就不会愚蠢到要去尝试。但如果你意识到,这个结论并非对所有人都适用,就开启了一个可能性的空间”。
“因此,训练专注力的第一要义是接受‘不确定性’”,朗格教授说,“当你对某件事情不确定的时候,你会留意到问题和差异,你会向可能性敞开,创造可能性……反之,如果你对某件事情很确定,就很容易陷入单一化思维,不再关注那些可能与之相反的信息。”
“现代人应该对‘不确定性’有更健康的尊重”,她说,“‘不确定性’才是现实世界的本质状态。现实从来不是静止的,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得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一旦我们看清自己是如何自我束缚在文化、范畴、语言和思维模式的陷阱里,就会发现,人生中我们可以控制的部分,包括健康和快乐,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返老还童的可能性
在一部即将开拍的好莱坞新片《倒时钟》中,詹妮弗·安妮斯顿将出演朗格教授,电影主线是她在1979年做的一个实验。
一个匹兹堡的老修道院里,朗格教授和学生精心搭建了一个“时空胶囊”,这个地方被布置的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他们邀请了16位老人,年龄都在七八十岁左右,八人一组,让他们在这里生活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里,这些老人都沉浸在1959年的环境里,他们听50年代的音乐,看50年代的电影和情景喜剧,读50年代的报纸和杂志,讨论卡斯特罗在古巴的军事行动,美国第一次发射人造卫星。他们都被要求更加积极的生活,比如一起布置餐桌,收拾碗筷,没有人帮他们穿衣服,或者扶着走路。唯一的区别是,实验组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循现在时——他们必须努力让自己生活在1959年,而控制组用的是过去时——用怀旧的方式谈论和回忆1959年发生的事情。
实验结果是,两组老人的身体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他们刚出现朗格的办公室时,大都是家人陪着来的,老态龙钟,摇摇欲坠。一个星期后,他们的视力、听力、记忆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血压降低了,平均体重增加了三磅,步态、体力和握力也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不过,相比之下,实验组,即“生活在1959年”的老人进步更加惊人,他们的关节更加柔韧,手脚更加敏捷,在智力测试中得分更高,有几个老人甚至玩起了橄榄球。局外人被请来看他们实验前后的照片,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么多年来,关于这个实验的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毕竟,这是一个田野实验,因为缺乏实验室的控制,一个结果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事实上,直到今天,朗格教授仍然难以解释,那一个星期里,这些老人的大脑和身体之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交互?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老人在心理上相信自己年轻了20岁,于是身体做出了相应的配合。为了维持时间感,那些“活在1959年”的老人必须付出更多的“专注力”,即更有意识的“活在当下”,因此他们的改善更明显。虽然不至于“返老还童”,但这个实验至少证明了,我们生命最后阶段的衰老并非不可逆转的。
“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她说,“老年人的虚弱、无助、多病,常常是一种**得性无助,而不是必然的生理过程。”
关于衰老的很多思维定势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人老了,记忆一定会衰退吗?
脑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其大脑活跃程度与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区别。他们在短期记忆力、抽象推理能力以及信息处理速度等方面的能力都不应差于年轻人。那么,到底是什么抑制了他们真实的潜能?
根据朗格教授的分析,这是因为我们身处一个崇拜青春,而厌弃老年的社会。年轻的时候,我们想当然的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老。与此同时,我们固执而轻率的认定衰老和能力减弱有着必然的联系。某天早上我们醒来,惊恐的发现自己已步入老年,这种思维定势往往极具杀伤力。当我们发现自己记性越来越差时,最现成的解释似乎就是——我们老了,而很少再去寻找其他的可能性,比如也许是我们失去了记忆的动机和意图?
事实上,很多心理实验都证实,一个人衰老的速度与环境暗示很有关系。与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结婚,往往长寿;相反,与一个比自己年老的人结婚,往往短寿。社会经常规定了,什么样的年龄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否则就是为老不尊。因此一个经常穿制服的人往往不容易显老,因为制服没有老少之分,没有年龄暗示。
“如果我们不是将‘变老’看成是一种时间的遗失,一条单向的下坡路,而是一个时间的过程,一种自然的变化,我们会发现年老的许多好处。”
在20多年前的一个养老院的实验中,她发现,当一个老年人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控制权时,比如他能决定在哪里招待客人,玩什么娱乐节目,自己照顾房间里的植物,他会比那些被全方位照顾的老人更加快乐,更爱社交,记性更好,而且活得更久。
当我问朗格教授,是否想过让自己回到30年前?
她笑着说,“如果你是一个懂得专注力的人,年龄从来不是问题。无论你20岁,30岁,或者60岁,你都是在体验当下,你在自己的时间里加入生命的体验。这是一种生活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