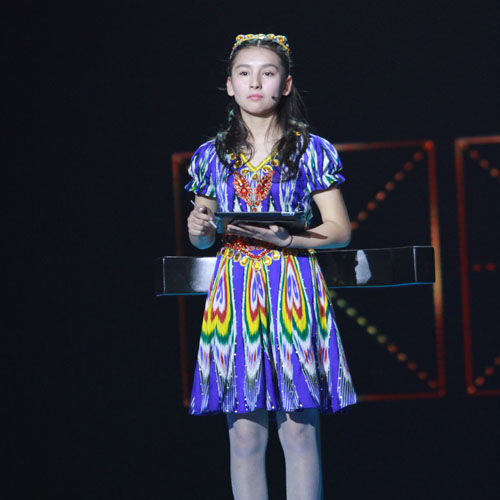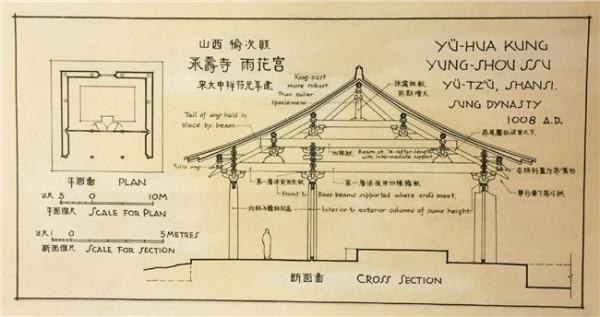骆以军梁文道 梁文道VS骆以军:文学两岸
提问:骆以军作品听起来很黄很暴力,但人看上去温和羞涩,为什么反差那么大?
读者提问:听了您的推荐以后我特别想看骆以军老师的作品,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名正言顺的在大陆看到。我特别想看的原因也是我想问的问题,您开始说骆以军的作品很黄很暴力,可是我看到骆以军老师好象是特别温和、羞涩的人,他的作品为什么会反差那么大?
骆以军:我昨天跟《新京报》的朋友聊,台湾比较年轻的读者、比较熟悉我的读者都知道我爱说人渣这个词,可是人渣这个词在大陆是非常负面的,我高中的时候是有一群人渣朋友,我特喜欢讲人渣朋友的故事。我没有办法像天文她们那样达到极限,感官到最极限的那一刻的时候,感官的光亮会暗灭,可是在暗灭掉的那一刻,最后的微光又会照亮起极限的情感。
其实那不是云端的哲学话语,不是抽象的语言,也不是赤裸裸写一些黄色书刊。其实好象是深海里面鱼吃的东西,一层一层的腐蚀,是一层一层落叶腐败累积下来的。
我特喜欢这种人渣,像赫拉巴尔写的小说《恶意喧嚣的孤独》,就是布拉格底层的,把这个城市所有的文学,所有伟大的歌德的小说、圣经、马克思主义,甚至希特勒纳粹的宣传手册,屠宰场粘着动物油污跟血迹的油脂,戏院的戏票,所有的东西像金字塔倒过来,把人类所有的梦境,高贵的丑恶的全部在最底下。
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小说就是我心目中的小说,小说家本来该是吃这个城市所有的梦。
保罗奥斯特特爱写纽约的人渣,保罗的故事最喜欢的就是酒馆、咖啡屋、二手书店,保罗也没有那个精力去做一个大冒险,可是他采集故事的方式就是利用一个一个的废才们,特点被这个城市伤害,可是问题他们又对这个城市充满黄金时光的爱,他们是这样讲故事,我后来变成非常喜欢这样。
提问骆以军:年轻时面对现实的压力,是什么让你有勇气继续讲故事
读者提问:我想问一下骆老师,您在跟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是否也面对很多现实的压力和选择,那个时候是什么给了您那么大的勇气让您继续做一个讲故事的人。
骆以军:我生命有一些时光很奇怪,很像希腊戏剧,剧作家把人物写的太惨了,舞台的机关就会有一个台子降下来,然后拿棒子问题全部解决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就是这样的。我要特别感谢朱天文和朱天心,我在大学以前是人渣,就是废才,整天跟哥们鬼混,可是后来在大学的时候,我的阅读是抄读,但是让阅读过程变成很缓慢,但对我来讲是非常棒的过程。
我也曾经有三到四年的时间一个字没写出来,那时候也结婚了,突然意识到我要工作,所以到出版社当了三年编辑,才上了一个月班就哭着回去跟太太说我不上班了,我非常焦虑那种办公室情感,我感觉办公室那种是斗争的,我是没办法上班的。
在那个出版社要倒了之前我出了一本书,记得在出书那一天我和我太太去出版社拿20本,我那时候本来准备开始卖串烧,结果这时候我遇到朱天文、朱天心,那时候跟她们完全不熟,我大概30岁左右,她们是我非常尊敬的人,她们跟我讲骆以军你要写,你是可以写的。
可是当最困苦的一段过了,后来有一些名声、名气,可以接到大的收入,可以写专栏了。所以你也要加油。
提问骆以军:创作时如何处理距离问题?怎么把握说故事?
读者提问:提到讲故事,我突然想到赛义德,我很喜欢他写的东西。是不是写故事的人都是作为外来人在场?说故事和距离中间有很微妙的关系,一件事情距离的近,道德感可能更强。一件事情越远,可能不会有那么强道德感,但是可以轻松的说出来,骆以军老师在创作时怎么处理距离问题?怎么把握说故事?
骆以军:我也是在摸索的过程,其实我跟大春、天文、天心他们不一样,我也许跟各位是比较接近的,我是在一个物质相对好一些,但是压力大一些,生活上的空间变小的过程。你刚才讲的问题特好,其实台湾的小说几乎到了大春、天文、天心他们这辈才真正到了成熟期,可是台湾的现代诗在60年代的时候达到不可质疑的高峰,很奇怪他们在苦闷的年代,跟各位某部分有点像,台湾那个年代你乱讲话、乱写文章可以带走。
另外不一样的是,台湾在那样一个高度管控的年代,蒋介石非常痛心疾首把大陆丢掉,其实一直在维持着早期现代主义小说,早期的现代主义风的小说反而表现出一种白色恐怖下的状况。
我们在学习写作这个过程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不是光小说这件事,所有文学第一个提问,所有你写的第一个字,所谓的文学就是独特的语言去看日常生活习以为常的语言,你如果在一个公车上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姑娘,你如果跑去跟她讲嫁给我吧,你马上就会倒掉。
但是如果你跟他讲你是我尚未失去的童贞的新娘,她听不懂什么,但是却成功了。
我后来在写《西夏》的时候,我放了一批西夏字,是伪造的。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看到一整本书,好象是用汉人的读法在读它。在我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不想写成一个亲子书,他那时候大概两岁,当有一天他90岁的时候我替他写一篇追忆,而里面主要的冥思的课题就是我,那个记忆是有问题的,台湾那时候可能是两岸关系最紧张的,外国外省人士非常焦虑,我不想变成直接这样写,我拉开来,像科幻小说那样写。
骆以军:会把已经结构非常漂亮的东西弄进来再变一下
读者提问:我看到骆老师有一篇文章提到日本的游戏道路十六,跟道路十六相关的是您写了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您非常大的特点是虚构的很多小故事非常华美,您可不可以以这个故事给我们讲讲您的想法和您的体会。
骆以军:我那个小说好象是二十五六岁写的,我其实也忘了。那个时候年轻,大一点的时候会知道所有的谜题的谜团是不能放故事的,而那时候年轻所以比较浪漫。我蛮爱玩儿这些的,我在《西夏》里面有一段写父亲,那里面的父亲不是我父亲,因为我父亲的故事我之前已经在别的小说写光了,我是要伪造一个集体的外省人想象中的父亲形象,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其实那个故事是我年轻时候很爱看的小说《心境》,一个年轻人遇到一个长辈,这个长辈很有学问,可是这个先生非常孤僻,很愤世嫉俗,很忧郁,他很爱那个先生,所以跟在他旁边讲大道理。
到小说最后才揭开了前面为什么所有的文字会有一些暗掉,在最后才会告诉你,原来这些伤害是更早前发生的。这个先生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爱的,比如我跟梁文道,我觉得梁文道比我帅,比我优秀,我们一起住出租公寓,我们两个一起暗恋房东太太女儿,有一天我跟梁文道散布的时候,梁文道是一个非常拘谨害羞的人,却告诉我说其实我喜欢房东太太女儿,结果我非常卑鄙在当天趁梁文道不在跟房东太太求亲说要娶你女儿,房东太太答应了。
过了一个礼拜以后他最好的朋友自杀了。那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画面。我就把它伪造成这个叙事者跟《西夏》里的儿子讲这段故事,我把它乱改,我会玩儿这些东西,我会把已经结构非常漂亮的东西弄进来再变一下。
梁文道:时间关系这场对谈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