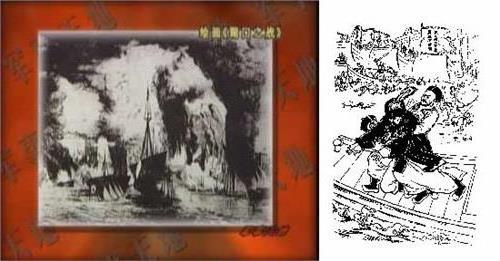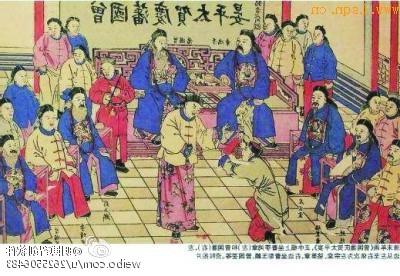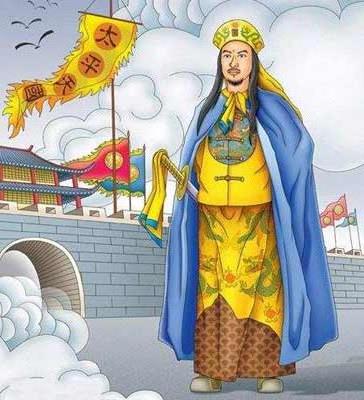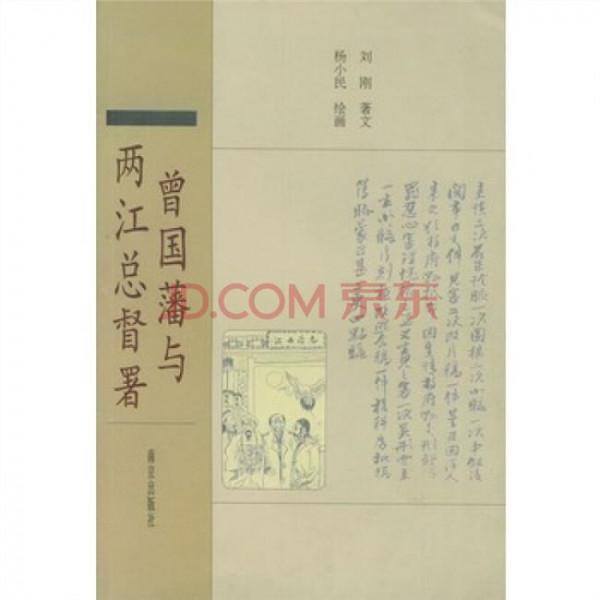曾国藩和石达开的比较
我认为曾国藩无论如何都不可原谅的只是他一贯性地纵然甚至鼓励对平民进行蓄意戕害、掠夺,“中国之兵,固不足以御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则有余。自屠割其民,而受大爵,膺大赏,享大名, 瞷然骄居,自以为大功者,此吾所以至耻恶湘军不须臾忘也”,至于闹自杀、谎报军功、篡改历史之类的,诚然并不光彩,甚至都是污点,倒也不一定只有“不折不扣的奴才”才会做。
维护清廷,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让中国白走了半个世纪的弯路,付出了惨重的选择,但身处在那个时代的人,不能看清楚清廷以及朽木不可雕,幻想着保住了清廷便保住了大局,便可以忍辱负重、缓谋强国之道,未必不是真诚的想法——其正确性则是另一回事了。
曾国藩死于1872年,如他有通天眼,能看到未来半个世纪的东亚历史,能看到几乎是同时开始的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带来了怎样天壤之别的结果,而为了挽救清廷这颗不可能挽救的朽木而让中国耽误的三十年,又是何其珍贵的三十年,又让中华民族承受了何等惨痛的代价,他当初未必不会多考虑一下部下、亲友甚至是敌人的建议。
当然,曾国藩维护清廷,除了对清廷抱有幻想之外,被扭曲了、和奴性的服从混淆在一起忠义观,及对自身利益的瞻前顾后,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也许正是这些东西遮住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清楚历史的方向,将他和历代名臣们的作风一比较,他身上的奴性与怯懦一面便会彰显出来,和那些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舍声忘死、前仆后继的草根阶层相比(不只是石达开、李秀成,还包括许许多多无名英雄),他是相形见绌的,“英雄”这两个字,他永远配不上。
不过,自私和怯懦是人的本能,当不了英雄也不见得就是“不折不扣的奴才”(即使英雄,也不是完美的,或多或少也会有过自私、怯懦的时候),个人以为,所谓“不折不扣的奴才”,是那些连起码的自尊与羞耻之心都丧失掉的人。
只要一个人被奴役时还有羞耻心,便不能轻易给他扣上“不折不扣的奴才”的帽子,就曾国藩来说,他还不是那种唾面自干、毫无羞耻之心的人,还没有麻木到只要保全了自己的利益就对国家民族的耻辱毫无感觉的地步(尽管没有足够的勇气去亲手洗刷耻辱),在这点上,他跟“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慈禧之流还是有区别的。
至于左宗棠,他身上比曾国藩更多了几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血性,他选择维护清廷恐怕更多还是缘于历史局限性,太平天国有很多英雄,但并非拥护太平天国的就是英雄,清廷有很多奴才,却也并非效忠清廷的就一定是奴才,左宗棠的一生虽然有许多可争议之处,但英雄二字,我以为他是担得起的。
曾国藩与手下谋士赵烈文的一番谈话中,他早就看到清朝50年内必亡,但他没有勇气去推翻清朝
------------------------------
纠正一下,说清廷50年内将亡的是赵烈文,不是曾国藩,曾国藩本人是极不愿意相信这一点的,他还问赵烈文,假如真到了那一天是否可以南迁偏安,最后还说,宁可自己早死,不用为此担忧。而且赵烈文虽然认为清廷50年内将亡,却也认为必是中心先先垮掉,再导致四方无主,各自为政,他在同一番话中也表示,当时中心尚有威望,四方风气未开,还没有到“抽心一烂”的地步,因此在这个时候造反是不会成事的,也就是说,断言清廷50年内将亡的赵烈文也在同时断言清廷在短期内不会灭亡。
李秀成劝他做皇帝,曾国藩的孙女回忆‘文正公不敢
------------------------------------
再纠正一下,这则口碑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转述她母亲曾广珊所说的话,但是曾广珊是曾国藩死后二十多天才在南京出生的,连曾国藩的面都没有见过,更不可能亲自听曾国藩讲述他不造反的理由。而且,曾广珊自己也不知道她母亲是从谁那里听说的,她说“可能是听曾国荃说的,也有可能是听曾纪泽说的,也有可能是听外祖母郭筠说的”,这些完全是她自己的想象,没有任何直接间接的依据。
另据俞大缜说,是她母亲某天跟几个人闲聊到了她母亲出生在总统府,而那里过去时天王府,后来又提到了李秀成,正是在这次聊天之后,她母亲跟她说了“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这句话,但是,她母亲和那些人的谈话内容,除了“从总统府聊到天王府”这一点是确定的之外,别的内容她也一律不记得了,包括话题是怎样转到李秀成身上的,也说不清楚,说是“大概因提到天王府,就提到了李秀成”,也纯属她的猜测。
至于一起聊天的都有什么人,是什么身份,和曾家特别是曾国藩本人有什么渊源,也一律没有提到。
我觉得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曾广珊、俞大缜本身并不会说话,但这则口碑的可信程度却非常可疑。因为曾广珊的消息来源完全不可知,她固然有可能是从真正知情人那里听说的,但也可能听到的只是别人的臆测之词,同时俞大缜对曾广珊提到这句话的背景也完全不清楚,也有可能是她母亲从那几个人的闲聊中听到了大家的议论。
这次谈话发生在1946年秋,即曾国藩死去74年之后,那时曾国藩同时代的人早已都不在人世,连曾国藩死后才出生的孙女都74岁了,也就是这一群人基本上都是曾国藩曾孙一辈的人,对那段的了解都不会太多——说两江总督府就是天王府,就是总统府,其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湘军入天京后,抢完了财宝将天京付之一炬(放火的是湘军而不是太平军,这是罗老自己的考证),“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后来的两江总督府,是1870年-1872年才在原来天王府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说两江总督府过去是天王府,这种台词也就是后世人出于凭吊、宣传、旅游之类的目的硬把总统府和太平天国扯上关系才会说的,这一群人显然对过去的事情所知甚少不仅如此,俞大缜对这些人的姓名身份也一概不记得了,否则,1946年距离记录口碑的1977年不过30年,某些当事人可能还在世,说出他们的名字来也许就可以向当事人直接了解当时聊天的详情了,就算他们不在世,也有可能对他们的子孙谈起过什么,或者留下过日记之类的记录。
对比一下沃邱仲子回忆石达开在四川受审时期的经历,基本上每一则口碑都能指名道姓,因为沃邱仲子得父亲就是四川总督府的幕僚,;骆秉章的幕僚都是他的叔辈父辈,这些人又都是有身份的人,所以即使事隔多年以后还是可以清楚地道出所有相关人士的姓名,每件事情的因果原委(即使这样,沃邱仲子的文章中也有很多错谬,很可能是多年过后的记忆偏差、混淆),而不像俞大缜的口碑那样,几乎对所有细节都说不去年高出,只有一句“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是清楚的,其他的不是一律不知就是纯属猜测。
像这样的史料虽然出自相关人士之口,但相关人士并非亲历亲闻,也不能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严格说来属于“无根史料”,如果这则口碑是批评太平天国的口碑,我想罗老早就把我上面指出的那些疑点一一指出,断言其绝不可信了,他认为这则口碑是“铁证”,个人以为,只是这则口碑刚好支持了他的学术论点而已。
综上所述,我认为曾广珊、俞大缜所说的话大概并非说谎,俞大缜教授说不清情况有可能是因为年事已高,记忆模糊,但同样,也有可能是隐瞒了一些情况,只选择性地说出了自己知道的事实,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在讲述口碑时,不只陈述了自己亲历亲闻得,还加上了自己缺少根据的猜测,比如说猜测母亲的话是从曾国荃、曾纪泽、外祖母那里听来,又强调外祖母“是有学问的人,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不作无稽之谈的”,很明显,她在主观上极力想要增加这则口碑的份量,想所以,虽不至于故意造假,但有没有隐讳、断章取义的地方就不好说了。
无论如何,除了两个人身为曾氏后人(但都在曾国藩死后才出生)的身份之外,口碑中并没有保护其他可以显示它来源可信的证据,曾国藩的孙女大约确实说过“李秀成劝他做皇帝,文正公不敢”这句话,但无法确定是来自知情人的叙述还是别人的猜度谣传,即使它确实来自知情人,由于没有上下文,谈话的因果原委也不清楚,同样无法证实其可信度,举例而言,如果它是曾国荃说的,有可能是曾国荃怪他老哥不肯听他的话而说的气话,如果它是曾纪泽说的,曾纪泽的所说的“不敢”极有可能是指“不敢为不忠之事”,而不是说他老爹自私懦弱,虽然曾氏后人不会故意丑化曾国藩,但曾广珊的大半生是在民国渡过的,俞大缜懂事后清朝就灭亡了,她们的思想很有可能受晚清、民国大环境的影响,即推崇太平天国,而把所谓的中兴名臣视为“汉奸”,对其不肯参与反清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实际上,比如前面提到的沃邱仲子,虽然父亲、老师、世交不是骆幕就是老湘军,但他们这一辈大都推崇太平天国,敬仰石达开,看不起骆秉章等人,以自己父辈的所为为耻,所以曾广珊、俞大缜虽然不会造谣诽谤曾国藩,但对有关曾国藩的负面说法轻易地相信却不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说他骨子里是个奴才,石达开为什么造反,用他自己的话说’拯乾坤于元元‘,我们讨论的是人格,人格,曾国藩在人格上是个奴才,石达开在人格上是英雄
----------------------
我在前面说过了,我认为判断是否“人格上是个奴才”的标准不能用英雄的尺度来划定,不能说达不到英雄的标准就是奴才,自私懦弱是平凡人都会有的弱点,你我难道就没有自私懦弱的时候,就没有在权势、形势之下低头,就从未有过因为嫌麻烦、怕惹麻烦、怕徒劳无功、认为不值得之类的原因,而放弃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时候?如果我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尚不能做到每一次都抗争到底,不接受任何不公正、不公平的妥协,又怎能说曾国藩不肯为天下人造反就是奴才呢? 曾国藩不造反,既有不敢的一面,也有不愿的一面,既有害怕自身利益受损的一面,又有囿于忠义观的一面,从大义上讲,曾国藩的选择误国误己误人,但从人格上讲,他的忠义观诚然是被有清一代的舆论政策所扭曲的忠义观,诚然包含了奴性,却也同样包含了美德,是混合了糟粕与精华的复杂混合体,“本质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奴才”显然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一味美化曾国藩的“忠义”,而无视其奴性、重小义轻大义的负面意义,和完全否定其“忠义”在人格上的正面价值,认为不肯造反就是奴才,都是片面而极端的。
如果曾国藩真的“本质上是个不折不扣的奴才”,其部下、亲友焉敢向其提出造反的建议,赵烈文焉敢在他面前预言清廷五十年内必亡?
再举个例子,在借师助剿的问题上,曾国藩曾经数次表示明确反对,“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因为上海遍地是外国租界),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中华之难,中国当之”,“岂轻借洋兵而贻讥于后世”,“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蹂躏中国之土地”,当然,他只是表态反对,清廷不接受,他也就算了,在这点他没有太平军“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於不顾”的气概,但如果他是“不折不扣的奴才”的话,只要洋人不跟他抢打天京的功劳,不去蹂躏湘军的老家,他会为了借师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跟朝廷唱反调么?
而且曾国翻若反,那是万万不会成功的
---------------
个人以为这个“万万”实在不大实在。由于太平天国战争,清廷原来依靠的八旗、绿营已经彻底没落了,所以淮军才会升格成为国家正规军,湘军虽见暮气,难以再用,但有多年战争中培养提拔起来的一大批将领在,要重新招募、训练有战斗力的部队并不需要太长时间,曾国藩的亲友、旧部、门生故吏在遍布各省,掌握着兵权、政权、钱粮,如果策划得当,在最开始的阶段能打出比较好的局面,产生一呼百应的连锁效应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亦也可以满足许多人当开国元勋的野心。
地主士绅们激烈反对太平天国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太平天国危及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如果曾国藩只反清廷不反地主,甚至还对他们许以好处,是有可能拉拢他们的,再说湘军本来的口号就是“卫道”,打出“恢复中华”的口号顺理成章,同样可以号召汉族知识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