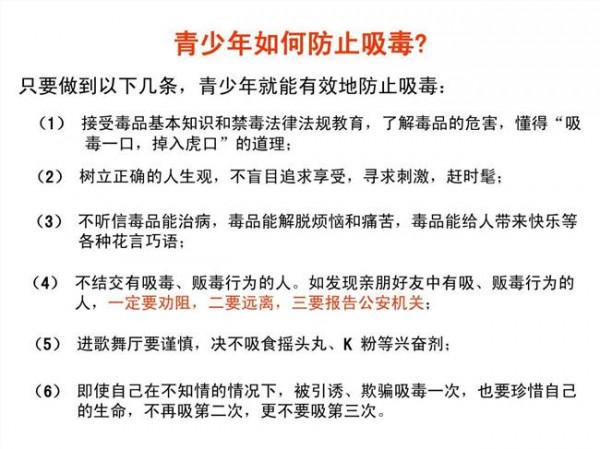乌仁娜的歌曲 乌仁娜 世界是没有边界的歌唱
乌仁娜也许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唱歌了,鄂尔多斯草原是歌儿的海洋,那里的每个人都会唱歌。在她的童年记忆里,她的母亲和祖母成天唱歌取乐,不论是在家里或在草原上放羊的时候,乌仁娜在一旁听着,唱歌就是这么自然而然学来的。
在蒙古,人们总先聚着喝茶,过会儿再喝点儿酒,然后就开始唱起歌来了。 乌仁娜出生、成长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草原,游牧生活是她童年的基调,蒙语、草原、牛羊和马群,是她少女时代所知道的整个世界。
当时,她向一位汉族老师学习扬琴,一般人四年的课程她半年就全部学完了,惜才的老师建议她到上海音乐学院深造。十八岁的时候,不懂一句汉语的乌仁娜第一次坐上火车离开家乡奔赴上海。这是她人生之途的转折点,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位为我们餐桌上驱赶羊群的牧羊姑娘,却幸运地诞生了一位能够以歌喉开启人们生命与灵魂通道的即兴长调女王。
城市见证了人类的统治,那自然呢?我问乌仁娜,你在国外闯荡这么多年,而你的歌声中依旧充满了草原、骏马、羊群、生命、童年、梦想等等这些内容,没有丝毫城市生活的印迹,这是本能,是乡愁,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她告诉我,音乐就是她的生活,是她的血液。
她在草原上出生长大,母语不可能忘掉,她的家乡鄂尔多斯草原,那里有她的亲人和文化血脉,这都是上天赠予她最珍贵、最美丽的礼物。
她只是用她的天赋打开一扇窗,把这些最美好的礼物用歌声展现在世界面前,与聆听到她歌唱的人们共同分享。美的东西永远是真实的,乌仁娜歌声中包含的情感便是如此真挚和深沉,以致,我们必须斟满伤感地聆听才能真切地理解她的音乐,但内心却是由衷的欢乐,正如卡夫卡所言,“忧愁强于喜笑,因为面带愁容,终必使心喜乐。
” 在音乐学院,乌仁娜并没有选择声乐专业,而是主修扬琴演奏。
我问她是不是觉得很幸运?她的回答坚决而肯定,“我庆幸自己没有选择学习声乐专业,在上海音乐学院我遇到了许多有特色、宝贵的声音,那些来自不同民族、地区充满天赋的学生,经过四年的学习之后,他们唱起来都一样,唯一不同的只是演唱的语言。
我真觉得很可惜,中国有着底蕴厚重的文化,有如此丰富的表达方式,我们应该带给人们更多选择,而并非仅此而已。” 尽管乌仁娜不归属于任何宗教信仰,但她遵照自然法则思考、行事,她即兴地练习和创作音乐。
乌仁娜说自己从不坐下来练歌,“小时候我放羊的时候唱歌、骑马的时候唱歌,工作的时候也在唱歌。每个人出生的时候都会用自己的声音来问候世界。我从来不练歌,但是我常常唱歌,我从来都不是为了提高技巧或者表演才去唱歌,我是为了唱歌而去生活。
”有时,母亲正在厨房里干活,会被隐在角落中的乌仁娜发出的突兀声响“惊吓”到,她就会问,“乌仁娜,你唱的究竟是什么呀?”乌仁娜则笑而不答。
谈到“即兴”,我们要拜国人竟未同化全部草原个性的恩典。“即兴”是乌仁娜的才能也是她的生活方式,即“游牧精神”,她永远不会为了即兴而即兴,这种“技巧”她生来便有,这就是她的生活,一切顺其自然。
如果说,“世界音乐桂冠女高音”是对乌仁娜某种程度的限定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将世界音乐的概念理解成一种即兴音乐的殊途同归。所以她创作的音乐每时每刻都不一样,“旋律永远没有边界,音乐虽然只有七个音符却能创造出无数的旋律。
旋律和歌词都来自我的生活,某些时刻我会有所感动,这些都是我创作音乐的基础和源泉,这是流淌在身体里的和谐”。 而提起乌仁娜的第一次登台演唱非常有意思,在此之前,她一直作为扬琴演奏员,而从未以歌手的面目出现在舞台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乌仁娜与一班朋友同台演出。她的前夫罗伯特仍然清晰地记得她突然变成歌手的神奇时刻,“演出《交汇》这首曲子时,当进行到扬琴独奏的部分时,乌仁娜断然做了个决定,说:‘我想唱。
’于是,她开始即兴演唱,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事实上,即兴演出对她来说还是未曾经历的新尝试,但是她的表现已然非常成熟。”自此,乌仁娜开始以自己独特而自然的歌唱方式,活跃于世界音乐的舞台之上。
然而,这其实是一直埋在她的灵魂里自然体验,当然也有未被同化的幸运成分。 如果时光倒流,真的难以想象,乌仁娜穿着华丽的晚礼服在电视台黄金播出段的综艺晚会上,按照规定的技术参数把一首著名的蒙古歌曲唱到了两万米的高度,并垂直降落在爆发出雷鸣般掌声的观众席上,我将会多么空虚和悲伤。
如果你想要寻找到进入内心的门道,乌仁娜的即兴歌声是一把万能钥匙,即使你对音乐并不在行,并且对蒙古语也一无所知。“有时候我会用属于我自己语言或者即兴演唱。
因为,语言有边界,有时候它是沟通的障碍,而旋律没有边界,所以我唱的时候一定不把自己关在语言的笼子里,没完没了地考虑歌词和旋律的平衡。我创作那些自由的旋律,配上一首小诗,有很多办法可以把生活中美好的感觉变成旋律,这让我觉得很幸福。
唱歌也是生活,有些音乐家为了音乐而去做音乐,另一些音乐家则把音乐当作生活,那么生活就在路上。” 乌仁娜相信,她这十几年在全世界各地的巡回演出中,从未遇到过不理解她的音乐的听众,“尽管语言、文化和思想有着差异,但人类的情感是共通的、是超越语言的。
我在舞台上常常感觉到台下的观众像是我的孩子一样,无论我的听众是五、六岁的Baby,还是九十多岁的老人家,我感觉到我和他们融为一体。
”乌仁娜的音乐具有如此魔力,在她的音乐中,语言已失去界分人们思想的能力,成为充满感情的旋律的延伸。聆听乌仁娜的歌声我们获得不仅是美丽的旋律和感情的归宿,还有一种寂静,在这寂静的世界里,人们从内心获得自由,无需逃避,也无需恐惧和冲突。
人们之间的交流可以不用再艰难地越过语言的阻隔,因为,世界在她的心中是没有界边界的歌唱。 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有很多人问乌仁娜为什么不用德语或者汉语唱歌?她每次都会回答:“如果想要尊敬重其他的文化,首先就要尊重自己的文化,这是我自己对待文化的一个态度。
我现在熟练掌握着蒙语、汉语和德语,并且正在学习阿拉伯语,但不论走到哪里我还是会使用蒙语演唱,我很尊重自己的文化,更何况汉族人用汉语唱歌肯定也比我强。
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我的母语,我的母语是蒙语,我游历了那么多国家,他们不一定能听懂我的语言,但我相信音乐传递的情感并无疆界,更何况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理解力。
” 由此也能够看出一个文化传承和认同的问题。文化传承之根本是自我认同,自我认同是一种精神上对本民族文化的尊重和推崇,如果没有这种尊重作为前提,一切继承和发扬都是徒劳。而且,也只有互相尊重,不同的文化才能平等交流,才能形成多样性的文化,多样性的文化是文化生态的良性土壤。
九十年代中期,因为爱情和音乐事业发展的需要,乌仁娜随前夫罗伯特来到德国定居。到了德国之后,她感觉这里做音乐的环境非常好,自己不用去做很多音乐之外的努力,只要专心做想做的音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如果那时我留在国内发展,很可能会走一些歪路。
德国还是一个很注重接纳和保护全世界不同形态文化的国家,在这方面他们有着非比寻常的责任心,这点尤其令我感动,同时我也接触到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音乐如此丰盛。
据我所知,国内近些年的改变和进步也令人赞叹,我们有那么多神奇的旋律、美妙的声音和丰富的色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
”乌仁娜如是说。 从家乡到省城,从省城到上海、北京,现在她已经离开了生活了十余年的德国城市——柏林,目前在开罗定居。除此之外,她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世界各地巡演的路上,然而乌仁娜对待这种漂泊生活的豁然态度着实令人惊讶。
“现在的交通很方便,旅行也很方便,我们能去很多地方,能够接触到不同国家的文化,这对自己的文化发展也非常有利,尊敬每一种文化,也就是尊敬自己。我选择居住在开罗,一方面是它的文化和音乐很有意思,而且它是一个很神秘的古老国家,这很吸引我。
我是一个游牧民族,我知道我不会永远住在开罗,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 尽管乌仁娜已经走得太远,但我们从她的歌声中听到,她从未离开过她这片从小出生、生长的草原,每年,她都会抽出时间回家探望她的双亲,或是把他们接到身边。
她依然眷顾着她的家乡鄂尔多斯,希望帮助家乡的人们改善一下生活境况。2000年的时候,她的父母来德国探亲,母亲告诉乌仁娜家乡有很多贫穷的孩子因为没钱交学费辍学在家,乌仁娜决定帮助他们。
在她的专辑《生命》出版以后,乌仁娜回到家乡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做一些帮助贫困孩子的项目。2006年,她开始在一个学校里帮助24个孩子,支付他们的生活费和学费。
乌仁娜的亲力亲为地做这件事情,也占用了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乌仁娜的只是希望,“我一心总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事情,总把家乡放在前面。我现在不能说很多,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希望能够坚持下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孩子们。每个人只能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情,我当然希望我的能力能够超过我的意愿,去做的更多。”(文/刘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