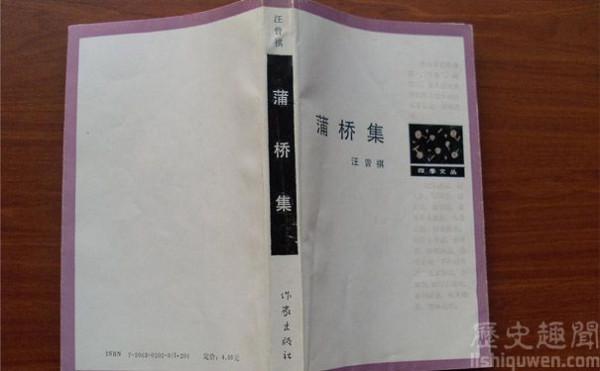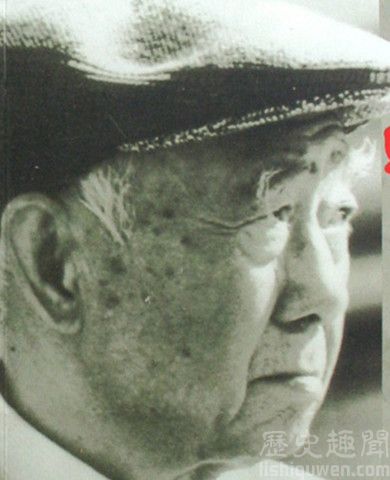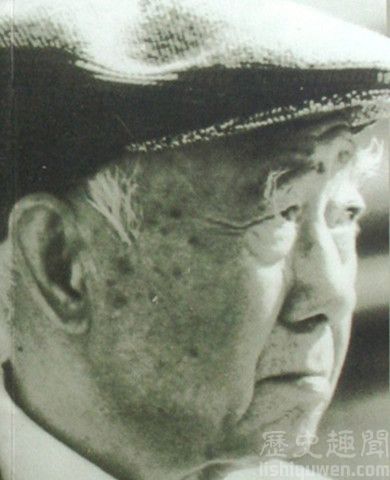汪曾祺与施松卿的爱情故事
在作家汪曾祺的生平介绍中很少提到他是华侨的女婿这件事。汪曾祺夫人施松卿,我的姑妈,是南洋长大的。在马来亚,松姑一家的生活倒也衣食无虞。她父亲很热心于当地的社会公益事业,后来成了著名侨领。由于他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即使在日本人占领马来亚期间,到处捕杀爱国侨领,他也没有被人告发和出卖,他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而安然度过了那腥风血雨的三年八个月。
福建长乐是个出人才的地方,现代著名作家郑振铎、冰心都是长乐人。施松卿的祖辈是赤贫之家,她的父亲施成灿自幼跟随我的祖父在南洋闯荡,我祖父在那里是唱戏的。她父亲后在马来亚开了一家药店,日子才逐渐安定并慢慢变得好起来。
大哥深感没有文化的痛苦,下决心让弟弟一边在药店当学徒,一边上夜校。几年下来,施成灿学有长进,考上了“医士”。有了这样一个名分,找工作就容易多了。不多久,他应聘到一个小镇的诊所当上了医生,施家的日子进一步变好。又过几年,施成灿回老家福建结了婚,随后把妻子带到马来亚,不久生了大女儿施松卿。
我小时候本来在本地读英文学校,我的叔公施成灿不以为然,要求我转学到他的道北镇读中文学校——育智小学。这时,松姑已经回国念书了。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施松卿小时候的生活很不安定。她跟随着妈妈,福建、海外两边跑,时而在老家,时而在南洋。她的小学、中学是在福建老家、马来亚和香港相继读完的。1939年,施松卿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和汪曾祺同一年。
她先是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学。不久感到功课繁重,十分吃力,加之这期间得了肺结核病,难以跟上课程,便在一年后转到了生物系,想向医学方向发展,以期有朝一日继承父业。但生物系的课程也不轻松,而这时,她的肺病趋向严重,其时昆明的物质条件太差,无奈之下,只好休学一年到香港养病。重回学校后,施松卿改读西语系,并一直坚持到毕业。
施松卿毕业后,因战争原因,家中无法对她给予正常的经济支持,一时又找不到工作,生活变得拮据起来。为谋生计,她也到了中国建设中学任教,和汪曾祺成了同事。两人在联大读书时虽不认识,却也对对方情况有所耳闻。汪曾祺听说过,西语系有个女生,性格温和、善良,秀丽的脸上总是挂着亲切的微笑;她长得挺清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虽有病,但那副慵慵懒懒的样子,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人称“病美人”。
相比之下,施松卿对汪曾祺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
她不止一次听别人说过,汪曾祺是沈从文先生的得意门生,以后又不断地在报刊上读到汪曾祺的作品。施松卿原来就爱好文学,上高中时还曾获得过香港国文比赛的第一名,这就很容易对有西南联大才子之称的汪曾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她喜欢汪曾祺凭借厚实的古文基础,把精炼的古代语言词汇自然地消融在他的创作之中,读来只觉得上下妥帖、顺畅,不似常见的那种诘屈聱牙。施松卿觉得,这种水磨功夫决不是一朝一夕能达到的。
当她把这些读后感当面说给汪曾祺听时,汪曾祺迅即产生了喜遇知音之感。他没有想到,一个专攻英文的女子居然能有这一番不俗的见地。两人相见恨晚,随着接触的增多,爱情也于不知不觉中悄悄滋生。
教学之余,同事们常见到他俩结伴而行。当汪曾祺在欣赏一大片胡萝卜地所呈现的堆金积玉的美景时,施松卿则兴致勃勃地向农民买来一大把胡萝卜,洗了洗,放在嘴里吱嘎吱嘎地嚼。昆明的胡萝卜很有特色:浅黄如金,粗而且长,细嫩,多水分,味微甜。
联大学生爱买了当水果吃,因为便宜。女学生尤其爱吃,据说这种胡萝卜含有少量的砷,吃了可以驻颜。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根据,不得而知。年轻的汪曾祺觉得,施松卿吃了胡萝卜,越发变得秀美可人。
生活中有了爱情,再困苦的生活也是甜美的。汪曾祺甚至在创作时也情不自禁地将心爱的人写入作品之中。在他的早期小说《牙疼》和《落魄》中都有施松卿的影子。在小说《牙疼》一文中,他写道:“我记得很清楚,我曾经三次有叩那个颇为熟悉的小门的可能。
第一次,我痛了好几天,到了晚上,S(指施松卿)陪着我,几乎是央求了,让我明天一定去看。我也下了决心。可第二天,天一亮,她来找我,我已经披了衣服坐在床上给她写信了。信里第一句是:
‘赞美呀,一夜之间消褪于无形的牙疼。’
她知道我脾气,既不疼了,决不肯再去医的,还是打主意给我弄点什么喜欢吃的东西去。第二次,又疼了,肿得更高。”
“还好,又陆陆续续疼了半年,疼得没有超过纪录,我们当真有机会离开云南了。S回福建省亲,我只身来到上海。上海既不是我的家乡,而且与我呆了前后七年的昆明不同。到上海来干什么呢?你问我,我问谁去!找得出的理由是来医牙齿了。S临别,满目含泪从船上扔下一本书来,书里夹一纸条,写的是:
‘这一去,可该好好照顾自己了。找到事,借点薪水,第一是把牙治一治去。’”这短短的一段描写是多么情真意切。
施松卿和汪曾祺携手在中国建设中学一直呆到1946年7月,然后才结伴离开了昆明,一个回到长乐,一个到了上海。正巧那时我刚从南洋回来,我们又一次聚在一起了。
在建设中学教书的日子里,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小学校的钟声》、《复仇》、《落魄》、《老鲁》诸篇,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如《复仇》,早在1940年初就写出了初稿,但他不满意,又一直没有时间修改。
现在,有了较为宽裕的时间,有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于是,他坐下来,认认真真地把《复仇》精心地改了又改,直至自己满意为止。有些作品,如《老鲁》,直接取材于他在建设中学教学生活中遇到的真人真事。他按照他所信奉的“写生活”的创作原则,把建设中学一位姓鲁的校警写得栩栩如生。
汪曾祺在中国建设中学教书的这两年,是他离开学校门走向社会大课堂的人生第一站。在这两年中,他最大的收获是,生活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使他能睁大眼睛,近距离地、真切地观察复杂的社会与人生。正因为如此,他把这两年的生活深深地珍藏在他的记忆之中。
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他还写出了情真意切的回忆散文《观音寺》和《白马庙》,由此可见,汪曾祺对走出校门后所接触的饱含磨难的人生第一课,在记忆中留下多么深刻难忘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