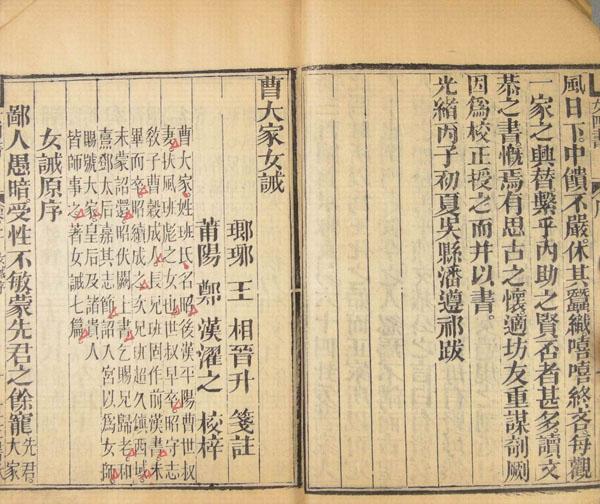杨念群的夫人 中西医及医学人文——读杨念群的《再造病人》
杨念群在文末说道:本书从现代“帝国”的殖民品格、“地方性”的确认和重构,以及“现代传统”的实践作用三个方面力图诠释“医疗”行为与“政治”变化的关系。通读全书,本书论述的绝不是简单的中西医孰优孰劣的檄文式论述,而是将中西医发展的历史及二者的相遇及之后的冲突置入更大的历史政治背景之下去考察,从而发现其背后的历史政治发展趋势和政治对现代科学的利用,考察现代政治如何将西医这样一个现代科学符号化的标志纳入政治合法性的框架内,从而为新政权服务等。
而我想在此文关注的更多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西医之争及其背后诡谲多变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渗透对当下医学人文的一些启迪。 中西医之争自从西医进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背后还有一套“全盘西化”的论争余韵。
前段时间的徐晓东打假太极,引出中国功夫花架子的质疑,有激奋者和痛心疾首者于是乎提出中国文化花架子太多,假功夫的背后还有假中医,看来中西医之争的问题似乎从未停止,只要有一定的刺激条件,中西医之争就会被挑动起来,其背后暗含的实际是现代科学逻辑霸权与传统文化的经验哲学之争。
现代科技的发展更进一步强化了现代人对科学的迷恋甚至迷信,科学的霸权话语在后现代虽然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却因为其给现代人带来的深刻变革,其霸主地位难以撼动,于是提到中医,反对者就会以“不科学”为由作为最直接最强有力的批驳武器,而处于同一科学话语逻辑之下的支持者无论如何论证“中医”的科学性都无济于事,在科学话语之下,中医支持者的声音只不过是矛盾地陷入了科学话语的意识形态里,不可能做到有力的辩驳,只有走出科学话语的霸权话语,中医的辩驳才会有前进方向。
建立于生物医学(biomedicine)之上的现代医学(西医)实际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一种治疗方式而已,其背后所依赖的哲学基础乃是启蒙运动之后的科学话语,随着科学话语逐渐取代传统经验成为统御一切的霸权意识形态,西医也一同获得了这种至高无上之感,让所有人都自觉生发出一种西医亘古至今的永恒感,所以,以经验哲学为依据的中医想要和西医有平等对话的可能性,要做的应该不是在西医的地盘里用科学话语辩驳自身的科学性,而是走出科学话语的霸权,将科学话语本身视为对话对象,只有这样,中西医的对话才有可能以一种平等的身份更深入下去。
每当一个人说中医不科学,只有西医科学时,我很想问:那西医进入中国之前,中国人生病靠什么医治?难道没有西医,中国人的身体全都是被“假中医”、“不科学的中医”碰巧治好的?且西医在西方也不是亘古至今就用,也是从启蒙运动之后,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现代科学的发展给西医提供了发展的基础,因此,西医本身也是一种后生的建立在生物医学基础之上的现代发明,是建立在笛卡尔身心二分的哲学基础上的一种现代产物。
近年来的医学人文首先反对的就是笛卡尔的身心二分,只有破除这种身心二分的哲学霸权基础,现代科学话语的霸权才会有所撼动,仅仅关注生物身体而非“整体身体(包括社会身体、心里身体等)”的缺憾才可能有所改善,这其中,人类学的整体观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人类学强调整体观,近来又强调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与生物科学的结合,考察人文、自然与社会多方面互动的关系,而不是仅从一面来决定一个人的健康状况等,因此,医学人类学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仅要关注生物身体,而且要关注生物身体之外的人,这里就会牵涉到当前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医患矛盾话题。
医患矛盾不仅发生在中国,但在当前中国却尤其突出,从本书中可以得到一些医患矛盾发展的启发,从传教士初次将西医带入中国引发中国人对西医的妖魔化和对西医空间的恐惧,甚至之后的“教案”等,我们就可以看到医患矛盾从来不是一个现代才有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的医患矛盾早在西医进入中国就已经开始,甚至可以说早期的医患矛盾更激烈,只是表现形式和政治话语表述不同,建基于生物医学基础之上的西医无论从生理治疗还是其配套的外部环境都是一个封闭的空间,这与传统中国社会独有的透明开放式的乡土社会关系格格不入,传统中国乡土社会看病首先是将中医视为乡土社会里的一员,中医在乡土社会里除了会看病之外,其他角色与乡土社会中的个体并无太大差异,且开放式的空间也提供了一种乡土社会特有的人情伦理关系,使得看病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处于可以预测和可以观看的状态,也将看病这种行为自然纳入到了乡土人情关系里,但西医封闭的空间就不同,他讲看病这个行为本身隔绝出来,将治疗行为用封闭空间隔绝,且生物医学涉及到对身体的手术,这又触及到中国人的身体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因此才给中国人妖魔化西医提供了土壤,也给西医进入中国带来了许多障碍,也为此,才有早期的“大树底下动手术”的事件发生,可以说,早期西医进入中国需要与传统中国文化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伦理及中医进行艰苦的斗争才能在中国大地有立足之地。
而这种中西医空间的不同而已为当今的医患关系提供什么样的启发呢?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和抗争,及政治意识形态利用西医合理化新政权的阶段后,西医早已成为当今中国人无意识的霸权科学之代表,但西医封闭的空间特点并没有多大改变,甚至在站稳脚跟后更加强了本身空间的封闭性,难以想象西医会如上个世纪初为了“在地化”(适应当地文化)而发生“大树底下动手术”的事情,但恰恰是这种封闭性,成为医患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西医在中国的空间设置从里到外都是一个科层制的封闭式的空间,病人完全不知道空间之内发生的事情,同时到这种封闭空间的体验也和中国文化中的乡土人情相悖,病人去看病可能最欣慰的并不是医生告诉他(她)某某器官或某元素升高的专业医学话语,而更欣慰的是医生能对生物身体之外的事更多一些询问,用更生活化的语言与患者交谈等。
因此,医学人文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希望现代医院能适当地开放一些封闭空间,将封闭空间里的事“去神秘化”,这里并不是简单地指“观看”本身,而是指这种封闭空间如何打开来适应当地文化,这有利于医院融入当地社会,同时也有利于患者对封闭空间中的医生多一份了解,很多时候,封闭空间中的医生很辛苦,但患者看不到,所以这是一个相互的行为,未来医学的发展可以朝这个方向做一些改变,有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
书中提到的另一个有趣的观点,指出西医进入中国也让看病行为变成了一种被动行为,患者从一个自由选择看病方式的主体变成了一个被客观化的被动的客体,过去中国人看病选择权在自身,患者及其亲属会一同选择大夫,患者是选择的主体,但今日的看病行为变成了患者只是看病行为被动的客体,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现代医院制度让医务人员这一方成了强势的一方,而患者只能成为弱势的一方,在权力关系上不对等,因此也造成很多内在的紧张和外在的矛盾等。
其次就是凯博文(Kleinman)在《疾病与苦痛的社会根源》里提到的一个观点,说中国人倾向于将精神疾病用身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即疾病躯体化的概念,凯博文给出的解释指出中国人追求集体利益、宗族和家庭利益这种特有的传统文化里排斥个体感情的表达,因此患者不善于表达内在的精神问题,从而将精神问题用“身体形式”表现出来,造成“躯体化”,而杨念群在本书中对此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他以北京周边农村对民间“四大门”崇拜和祭祀行为指出中国人并没有将精神问题身体化,在中国人的世界里,身体问题靠人,靠大夫,但精神问题靠神,有了精神问题往往求助于菩萨和一些小的信仰等, 两这各得其所。
实际在我看来,凯博文和杨念群的观点并不矛盾,凯博文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做的研究,那时候中国民间信仰已经被高度激烈的政治运动破坏殆尽或者压抑着,中国人的精神问题在他的临床观察里倾向于身体化表达是一种普遍现象,同时他用中国重视集体主义的传统文化来解释也是可行的,而杨念群的历史研究主要考察的“四大门”信仰考察的是传统中国社会,是新政权建立之前的精神问题的解决方式,那时候民间信仰还非常普遍,没有被后来的政治意识形态破坏和取缔,因此杨的观点也非常有说服力,两者只是考察了了不同时间中国人的身体和疾病观念,并没有本质上的冲突,只是杨在他书中将凯博文的观点作为一个批驳的对象于我看来有一点牵强。
最后,就是西医为什么易被新政权和政治意识形态重视和利用,就是因为西医最大的一个特点是集体防疫,与分散的、一盘散沙式的中医治疗特点不同,西医集体防疫的特点有利于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和新政权权力的向下渗透,有利于通过医疗的手段将大众纳入新政权的意识形态规训范围之内,有利于实现新政权的合法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