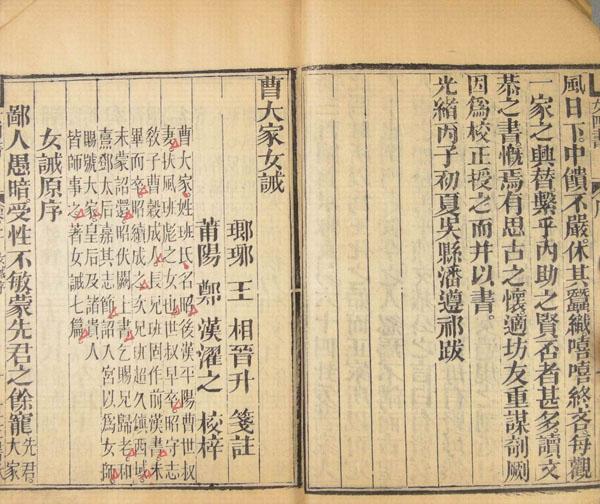杨念群的夫人 赵园、杨念群谈古代士大夫的生活世界
赵园:《家人父子》不是在最好的状态下完成的。那时候写完《想象与叙述》,还没有退休,我觉得必须再接着做点学术,否则跟单位不好交代。
我现在回想为什么会写《想象与叙述》?当时我集中的读了一些明清史的书籍,今人、古人的著作都看了,另外也读了一些国外汉学的著作,注意到他们关于1644年3月19日常常有一些渲染的,比如那天的天气如何,而且彼此之间有比较大的差异,所谓传闻异词,甚至同在北京的人的记述互相都不同。
有意思的是,郭沫若1944年发表的《甲申三百年祭》,选的日子也是公历3月19日。我觉得很奇怪,1644年3月19日被定为明亡的日子,就是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的日子,是农历,并不是公历,公历应该是4月25日。可是为什么延安《解放日报》会选公历3月19日发布这篇文章?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他们宁可忽略公历和农历,这样就觉得这个题目有了点意思。
我在北京大学跟学生们讲《家人父子》这本书的时候说过,我在伦理问题上有特殊的敏感,有时候甚至有一点自虐的倾向。我常常会记得很久以前的事,这好像像是一个虐心的那种行为,自己完全不能克制。比如现代文学里,有两篇小说涉及到母子的,我都很难忘记。
一篇是蹇先艾的《水葬》,他写一个贫苦农民偷了东西,大概是小偷小摸之类,当地乡民为了惩罚他,把他水葬了。可就在那天晚上,他双目失明的老母亲,还在家门口的院子里等着他归来。这个小说使我无法忘却,我会反复地想,这个老母亲等来的会是什么?下面的日子该怎么过?
还有一篇是蒋光慈的《田野的风》。现代文学研究的人可能知道这篇小说,一个革命者在当地发动农民,搞农民运动,农民要烧他家的庄园,这个时候他的心情非常矛盾,矛盾在什么地方?他想到了卧病在床的母亲。我想就是现在想来,这也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我们很多人热炒其实我也并不认为那就是伪命题。但是最终大家都能够了解,革命和恋爱是可以兼容的,但是还有一个难题,比革命和恋爱之间的关系更难处理,就是革命和家庭、亲情。我现在也不能够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像古人说的忠孝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类似之处。
前一时期我看到媒体上报道有的革命者在自己的晚年,想起了自己的双亲。有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曾彦修,他说在1934年的时候,他离开成都的家参加革命,事后才知道,他母亲哭瞎了眼睛。他后来1964年回到家乡,到晚年他很后悔没有向他母亲下跪,因为下跪是政治不正确的。
我看了他的回忆录就想,你1934年离开家,为什么到1964年才回去?你1949年不就可以回去么。这个故事该怎么解读呢?这些内容,跟我们的题目不能说毫无关系。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推动力,就是对当代伦理问题的关心。
社会家庭角色明确:强悍官吏也是温存丈夫
我在写《家人父子》的时候,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古人把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区分的很清楚。比如我写祁彪佳这个人,据说他是一表人才,夫人也很美貌,当时被称为金童玉女。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很强悍的官吏,杀起人来毫不手软,而且确实有能力。
可回到家里,扮演家庭角色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温存的丈夫。他最后自沉殉明,甚至没有拉着老婆一起死。在那个时代,拉着老婆、妻妾、一家人同死的大有人在。可见,他把臣子的角色和家庭的角色分得很清楚。
人伦之变,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我写到刘宗周门下一个知名的儒者张履祥,他遇到一个很尴尬的事,他的女儿被他的女婿和妾毒杀了,周围朋友都劝他不要深究。张履祥处理这个问题是很痛苦,这个事例其实说明了在晚明,已经出现了人伦之变。
这种事情并不是明清之际才有,但一旦发生在明清之际,人们马上会把它嵌在当时社会的大图画中,好像所有家庭事件、社会事件都必由当时的大背景来解释,这可能也是理解历史的误区。
其实,文革中也如此。比如北大教授季羡林被关在牛棚,当时的处境就十分尴尬,他甚至也想过自我了断,但他又想到家里有两个妇人在等着他,一个是他的妻,一个是他的婶母。他想到家里这两个女人,这条温柔的绳索就把他从悬崖上拉了回来。 所以家庭的作用,真的不能小看,它很重要。
我后来看到两篇评论我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表达对冒辟疆的义愤,说他是一个渣男,配不上董小宛这个女神。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响呢?我绝没有不能容忍冒辟疆的意思。
我觉得冒辟疆很坦然,这么坦白的讲自己家事,不只是跟董小宛,也包括和他的妻子,他的弟弟。现在看来,有的会被认为是丑闻的,他都写了出来。当然,那个文集是他的后人整理的,我不知道冒辟疆是否愿意把有些内容公诸于世,但反正是收入文集了。
我觉得,冒辟疆做的事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其实,有一个更知名的人物就叫吴梅村,他有一个比较相好的风尘女子,就是秦淮八艳中的卞赛。卞赛曾向吴梅村表达,想嫁给吴梅村,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人们都想找一个稳定的归宿。但吴梅村装聋作哑,卞赛就放弃了,当然,她内心很痛苦。
事后,吴梅村曾在一首小诗中写到了当时的情况,他当时是如何反应的,过后又怎么样与卞赛重逢,以及重逢之后的情景。我在《家人父子》的附录里,谈到吴梅村并没有表示悔意,他不能接受卞赛有各种原因,尤其是家庭原因。他想到要为一个女子负责,他不答应也可能是一个负责的态度。所以大家不要对冒辟疆过分苛责,我们不能够这样苛责古人。
我们只能够苛刻一点要求我们自己,你怎样对待女性,但是不能够要求古人像我们一样。我看到这样两篇文章,觉得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而且我觉得对于中国古代士大夫的婚姻生活,应当有更丰富的了解。
多年父子难成兄弟 父子关系更有压抑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今年的热门话题,现在还有一个又一个的讨论会。我在各种场合都说,就我现在的认知,不足以推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基本判断,包括家庭压抑了性,男女不平等,女性受到的压迫等等。但是,如果读了我的《家人父子》,它会丰富你的了解,在古代并不到处都在压迫,到处充满苦难。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歌唱到:“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到现在我还记得这首歌,但是古人的生活其实是各种各样的,不能一概而论。
这里引用了一种说法叫“古风妻似友”,这是归庄说的,显然归庄跟他的夫人关系很好,从诗里就能看出,他夫人是一个精灵古怪,极其聪明的姑娘,我相信他妻子与归庄是可以做朋友的。
我没有看到有人说父子“似友”的,父子“似友”这种情况在古代未必没有,但我没有看到这种表述。有人提醒我,说汪曾祺有一篇小说叫《多年父子成兄弟》,这个很有名。昨天晚上,我和一个老同学一起用餐,我还问他,《多年父子成兄弟》有所本吗,他说好像没有。汪曾祺这么一说就成了名言了,但是古人未必没有多年父子成兄弟这种现象,只不过没有这种表述。但是父子关系,在我的感觉中,确实更有压抑性。
历史不是干枯僵尸 须有血肉情感
杨念群:我看了赵老师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我就立刻成为她的粉丝,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觉得在历史学研究领域里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被扣“帽子”,第一,太注重理论。第二,太注重叙事。我觉得第一个“帽子”实在冤枉,因为我一直说,理论只是工具。
另外,我特别注重历史写作中的叙事问题。我们知道,在古代文史不分家。司马迁的《史记》,叙事是非常精彩生动的。但是后来历史学越来越抛弃了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使得所有研究都变得面目可憎,产生了单一的形式,也使得长期生产出所谓知识或者学术的产品跟机器一样。
我们生产这种产品,不能说是学术本身的错误或者学术本身的含量不好,而是我们在操作学术的过程,本身就是在戕害对历史知识感觉的把握。那么历史的感觉怎么体现出来,历史是活生生人的活动,而不是各种各样外在条件制约着你。
我看了赵老师《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之后,对赵老师的研究,包括对她所有的著作概括出两个关键词:第一,感性。第二,困境。
我先说感性,为什么提到感性,到底在历史研究和写作中的地位,如何来定位?这是未来历史学如果要继续走下去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现在历史写作是排斥感性的,追求客观,追求历史规律,追求大的结构,大的演变。
这样是没有错,但是不应该成为历史研究的唯一的道路和唯一的选择,历史研究应该凸显人本身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和他存在本身的活动方式,而不是我们把所有条件摆列出来以后,最后人消失了,没有人了。
我们现在很多研究是缺乏对人的基本理解,即对人的命运状态和他所处环境里面感受的状态,那样的一种活动方式的基本理解。所以我觉得把感性重新请回到历史现实中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赵老师提到,无论是研究明清士大夫还是研究家庭本身的时候,实际上都涉及到她自己表述的一个词——痛感,即研究一段历史或者写作一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带入了感情,当然这个感情是有一定限度的。
刚才赵老师说不能滥情,不能随意介入(感情),历史有本身的脉络在里面,但是感情的带入是不是就是一种罪过?写漂亮文字是不是就是历史的罪过?是不是文学归文学,历史归历史?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应该给历史学叙事正名,让历史学所有东西写得好看一点,可读一点,可读未必就是浅薄。
我们常觉得有可读性就是浅薄,故作高深的讨论就是深刻的,一定要打破这种二分法,使历史写作归于一种比较人性的写作。这是我与赵老师观点相似的地方,因为我在历史学研究里面,同样是被边缘化了。
我不是主流,各种奖我也拿不到,当然他们不会给我(奖),并不是我自己自吹,可能因为他们觉得我写得太好看了。我并不是说真好看,我觉得我自己不满足,但是他们觉得很好看了,这就变成了历史学的罪过,应该改变这种现状,为什么不能写得好看一点?
所以感性如何带入到历史研究的写作中,使它重新拥有它的位置,我觉得非常重要。
这是我想接着赵老师的话继续表述的内容,因为赵老师她觉得历史学不太认可她,但是不管其他任何人是否认可,我来认可,我来给她站台,其实我比较喜欢读那种漂亮的文章,漂亮的叙事,漂亮的表达。
历史学已经改变,不要排斥感性,不要排斥痛感,不要排斥对历史深刻的个人理解,也不要排斥人性,否则历史学将变成一种干枯僵尸一样的东西,摆在那儿,没有血肉,没有温度,谁会去看呢?这是我想特别谈到女性的时候,因为赵老师本身就是一个女性学者,所以她的敏感度和对历史的切入的那样一种感觉,这让我感到非常敬佩。
第二,我想回应一下赵老师,我觉得赵老师这本书跟以往不太一样的是关于中西方的问题,赵老师在这本书里一直在回应中国和西方两个不同的世界,甚至不同的学术界,包括对女性问题、父子问题、家庭问题等问题的一些看法。同时包括书里面引了很多当代美国汉学研究比较优秀的著作,比如《闺塾师》等等,赵老师实际上是自觉回应世界范围内如何来看待中国历史的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美国汉学家反五四 认为古代妇女有地位
杨念群:回到赵老师这本书,我有两个话题跟大家交流讨论一下,第一点,现在有一种极端的看法,即对女性、家庭的研究有两种过度的想象。其一,我们所接受的传统教育,就是五四以来的家庭叙事和对性别的理解。
比如我们脑子里,大家可能在课本里看过《家》、《春秋》、《雷雨》,这些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叙事方式,实际上都是五四的叙事方式,描述家庭非常黑暗,大家庭里面明争暗斗,但是争斗的根源就是它的宗法制度,家庭制度的黑暗性。
五四以来的叙事一直把批判和推翻或者清算家族制度作为我们的使命。这样的一种叙事和命题,贯穿着我们所有历史研究中,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家庭被妖魔化了,极端的妖魔化导致我们一想到家庭,想到的就是那个老太爷和一种冷暴力的家庭,在他底下一切的不管是夫妻还是父子,还是子孙几代都是受害者,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所接受的是一种传统的支配的思维。
第二个思维与第一种恰恰相反,即把世人跟女人的关系美化和过度理想化,比如钱谦益和柳如是在江南两人诗酒唱愁,我们看到很多美国汉学家作品,包括西方性别研究作品,都是为了刻意反五四的叙事,把五四以来所批判的封建大家长、大伦理脉络下的那样一种东西颠倒过来,重新加以定位和肯定。
但是我觉得从研究的角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我们称为后现代叙事的方式,反而把五四一直批判的那套东西,从过度的妖魔化的一种状态,倒转过来变成过于美化和理想化。
这是现在对中国家庭研究最大的问题,甚至有的书把颠倒祥林嫂形象作为它的出发点,认为鲁迅对祥林嫂所有的描述都是不对的,表示江南很多上层妇女可以随便跟丈夫出去夜游,可以出自己的诗集,可以参加很多活动,所以有很多著作描述江南女性的优雅自由。
但是这样过度的美化和理想化,同样不是历史的真实,这跟五四叙事那样妖魔化传统家庭就像一个银币的两面一样。我想这一点上我们要重新反思,我觉得赵老师刚才特别谈到书里面她引的材料和谈到的很多事例,其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即不是要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也不是为了某个群体去辩护什么,比如说很多作者,直接介入到女性的状态里面,为女性辩护、呐喊。
另外,赵老师想把女性和父子的关系放在非常复杂的现场状态里,看他们所身处的困境,其实历史学带给我们的任务,不见得要得出一个确定的结论,而是要描述出当时的状态,甚至把那种状态提供的矛盾和困境呈现出来,这就是人生。你会从中得到一种启示,会反馈到自己的人生境遇里,来看整个的历史脉络,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正如赵老师所说,其实当时的士大夫,或者我们现在所谓的知识分子,是非常复杂的。有的人可能是一个儒,或者是一种士,但是表面看起来是拥有很高深的知识,身份也很高,但是实际上他非常迂腐。
当他处理一个具体事件,具体场景的时候,不要把自己限制在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框架里,应该可以看到在具体场景里,可能在某一件事上可能会漏,但是在某一件事上会非常明智,所以人性的复杂会在一件事上表现出来。
赵老师书里比较了冒辟疆和董小宛,比较了钱谦益和柳如是,钱柳是悲剧的,但是董小宛是一种非常忧郁的状态,因为钱谦益是不顾世俗的,所以柳如是活得很潇洒,两者是不一样的,但是冒辟疆也不是渣男,因为他也有对董小宛温存的一面,只不过在家庭非常复杂的脉络里面,他处理的更加艰难而已。
而钱谦益是江南大佬,翩翩君子,他处理家庭的时候有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资源,他有能力处理这个,但是冒辟疆没有。但是钱谦益有时候也很渣,最有名的故事是他要投水自杀的时候,他的手伸到湖里说这个水太冷了,算了,咱们别投湖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如何在具体的脉络里面看待人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