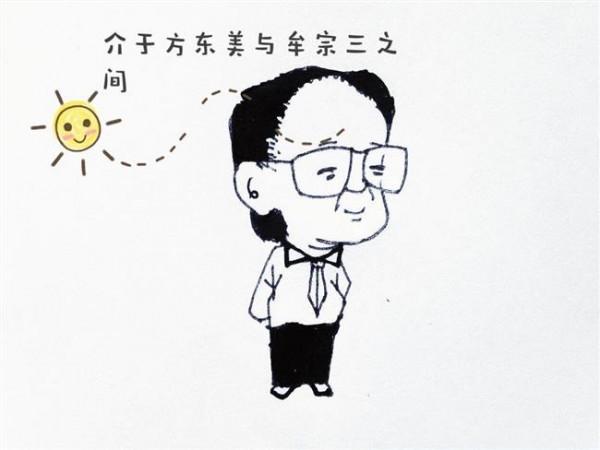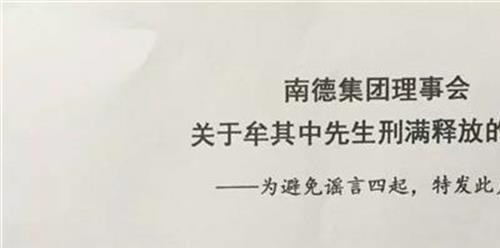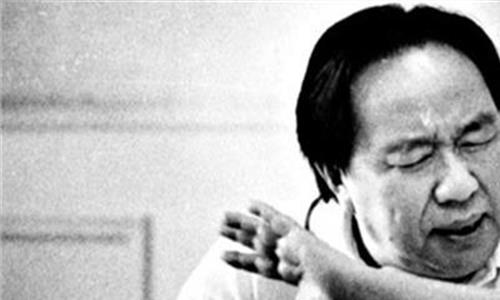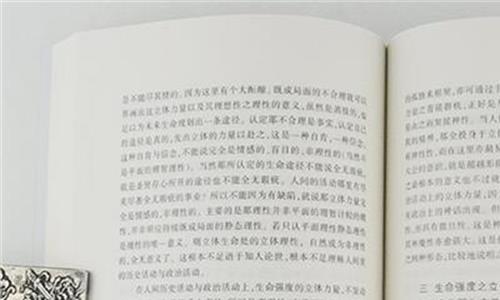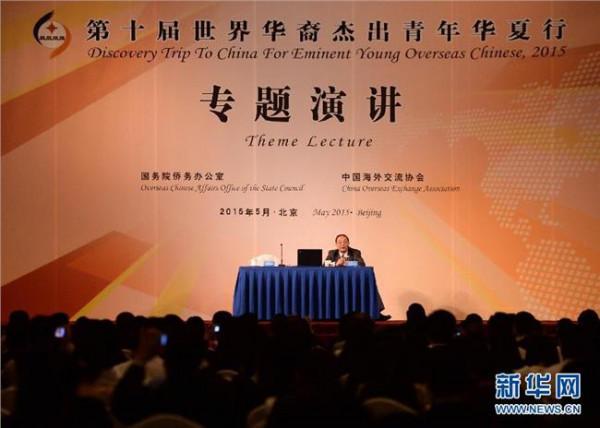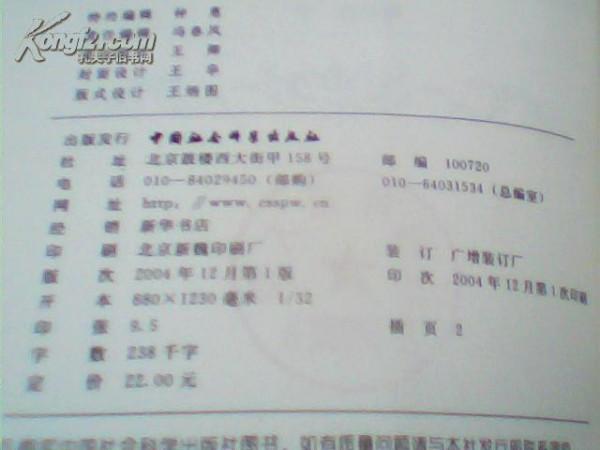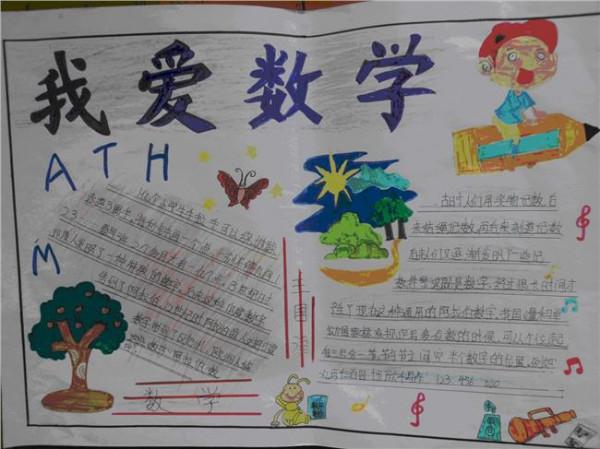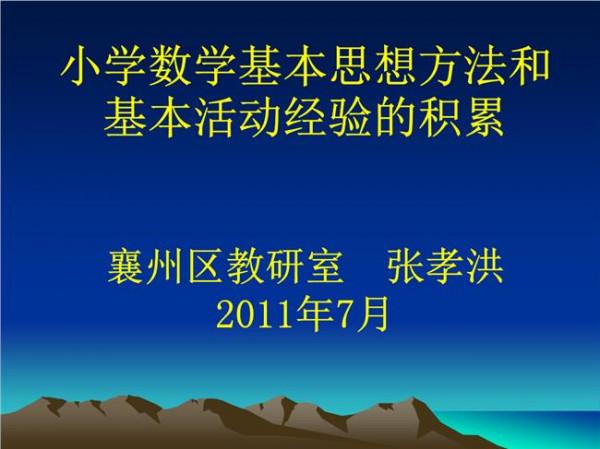牟宗三书法 论牟宗三儒学思想方法的缺陷
内容提要:尽管牟宗三儒学思想作出了杰出贡献,但其思想方法也存在着严重缺陷。这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对良心本心的理解过于陈旧,未能摆脱感性理性的两分模式,总体上坚持的仍然是两分方法;二是对康德智的直觉思想理解有失准确,认为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即是智的直觉,不仅直接将其创生的对象称为物自身,而且以此作为一种基本范式,扩展到圆善论和合一论之中。
从整体上看,这种方法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发展空间,可以说已经终结了。
关 键 词:熊十力/十力学派/牟宗三/现代新儒家
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重要代表人物,牟宗三对儒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必须承认的。但同时也难以否认的是,其思想内部也存在着一些缺陷。在笔者看来,牟宗三儒学思想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方法的不足。
说到牟宗三儒学思想方法的缺陷,首先要提到的是他对良心本心的认识过于陈旧。牟宗三对良心本心有深切的体悟和简洁的阐发,特别是他所记述的熊十力关于当下呈现的论述,堪称20世纪儒学发展史的经典案例,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他的思维方式仍然是传统的。良心本心是儒家心学的立论根基,孟子如此,象山如此,阳明如此,牟宗三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牟宗三并没有超越前人。检查牟宗三的相关论述,他只是强调良心本心是大根大本,非常重要,教导人们必须按照它的要求去做等等,而未能对其作出深入的理论探讨,有一个学理上的交代。
笔者对牟宗三儒学思想有所不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笔者看来,按照古人的说法,纵然可以体会良心本心作为道德本体的重要,但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比如良心有无时间性,有无空间性,是不是可变的等等,并没有办法得以解决。
因此,这些年来笔者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分为“何为良心”“何谓良心”两个层面来进行。
第一步是“何为良心”。这是指首先要通过生命体验体悟到良心的存在,明白自己也有良心,不能只将其视为文字上的符号,或理论上的共相。第二步是“何谓良心”。这是进一步要求在理论上说明良心究竟为何物,不再满足于只说其如何如何重要。
笔者认为,人之所以有良心,有两个必不可少的原因:第一,来自人作为一种生物的先天禀赋,这种情况笔者叫作“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第二,来自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智性思维的内化,这种情况笔者称为“伦理心境”。
(参见杨泽波,第64-86页)“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是“伦理心境”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伦理心境”便没有一个附着之地,也无法说明“伦理心境”何以会对人自然有吸引力的问题。“伦理心境”则是“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的进一步发展,没有这一步发展,人也不能与一般的动物相分离。
“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属于人的自然属性,“伦理心境”则属于人的社会属性。“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是先天的,“伦理心境”则是后天的,但同时又具有先在性。从这两个方面说明“何谓良心”成了笔者整个儒学研究的基石。
对良心本心的认识过于陈旧,对牟宗三最大的影响,在于决定了其儒学思想从整体上说仍然是一种两分方法。所谓两分方法简单说就是将人的思维分为感性与理性两个部分的一种方法。西方哲学在认知领域虽然也有其他模式,但在道德领域,流行的则一般都是这种方法。
在两分的架构下,感性是导致人们走向恶的力量,理性是引导人们走向善的力量;人们的任务就是运用理性的力量,制约恶,走向善,但这种方法并不完全适合于儒学。在研究孟子性善论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笔者称之为“三分方法”。
所谓三分方法是将人的道德结构横向划分为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的一种方法。在笔者看来,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讲道德就没有简单划分为感性、理性两个部分的做法,实际上坚持的是欲性、仁性、智性三分的格局。
欲性的作用是负责人的物质生存,仁性的作用是听从良心本心的指令,智性的作用是发挥学习和认知的功能。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孟子与荀子、心学与理学之争,但在孔子那里,这三个部分齐备不欠。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哲学的传入,两分方法作为一种思维模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开始不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看待儒学,研究儒学,未能对其加以反思,从而在研究中遇到了很多困难。牟宗三在儒家心性之学研究中存在的诸多缺陷,均与此有或紧或疏的关联。
比如,牟宗三不恰当地判定伊川、朱子为旁出,就是这样造成的。牟宗三一方面看到良心本心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潜意识里又受到西方感性理性两分的影响,不自觉地认为,道德根据只有一个,这就是良心本心。象山、阳明重良心本心,讲良心本心亲切入里,故为正宗。
伊川、朱子虽然也讲良心本心,但其讲法有缺陷,不到位,思想的重点置于《大学》之上,以格物致知来讲道德,故为旁出。这种做法明显存在不足。从孔子创立儒学的那一刻起,儒学就没有感性理性两分的思想方式,而是实际上将人的道德结构分为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
在这三个部分中,仁性和智性都是道德的根据,相互补充,并不互相排斥。儒学历史上心学理学之争尽管非常热闹,但都可以在孔子学理中找到根据,都有自己的合理性。
象山、阳明来源于孔子的仁性,伊川、朱子来源于孔子的智性。如果说伊川、朱子不合孔子的仁性是旁出的话,那么象山、阳明同样不合于孔子的智性,也未必不是旁出。牟宗三没有看到这一层,强行划分正宗与旁出,表面看界限分明,立意超拔,其实是以心学而不是以完整的孔子思想为标准的,而其思想基础恰恰就是十分陈旧的两分方法。
又如,牟宗三无法真正说明理论何以具有活动性,也属于这种情况。牟宗三判定朱子为旁出,一个重要理由是批评朱子是道德他律。牟宗三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朱子一系不以良心本心讲道德,其学理来自《大学》,是以知识讲道德。
凡以知识讲道德即为道德他律,朱子以格物致知讲道德,所以朱子为道德他律。笔者的研究证明,牟宗三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疏忽,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嫌朱子的道德不具有活动性,道德他律只是其为朱子误戴的一顶帽子罢了。
不仅如此,在此过程中,牟宗三也没有能够真正说明一种理论如何才能具有活动性,而只是说在一种道德理论中必须有“心”义,这个“心”就是孟子意义的道德本心。有了道德本心,理论就有了神义,有了兴发力,有了活动性,不至于沦为死理。
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但遗憾的是,牟宗三并没有再往前走一步,未能从理论上将这个问题真正说清楚。如果有了三分方法,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说了。按照三分方法,道德结构由欲性、仁性、智性三个部分构成,欲性和智性居于两端,仁性在其中间,负责传递信息,是欲性和智性之间的一个桥梁。
由于有了这个中间环节,凡是智性认识为正确的,仁性便会发出一种力量迫使人们必须去做;凡是智性认识为不正确的,仁性便会发出一种力量迫使人们必须去止。
一旦听从了仁性的命令,就会得到内心的满足,体验到道德的快乐。儒家学说系统中并不存在休谟伦理难题,最深厚的理论基础即在于此。换言之,儒家道德学说是三分的,西方道德哲学一般是两分的。
在儒家三分系统中,欲性和智性分别大致相当于西方道德哲学中的感性和理性。儒家思想的可贵之处是从孔子开始便特别重视仁,强调仁性的重要,多了仁性这个因素。牟宗三创立的“即存有即活动”这一概念虽然非常重要,有极高的价值,但其理论意义始终隐而不彰,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没有能够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其方法总体上说仍然是两分的。
再如,牟宗三在论述情感问题上遇到麻烦,同样与此有关。在将朱子判定为道德他律的过程中,牟宗三不得不处理道德情感问题。在康德看来,道德情感虽然不同于经验情感,本身有很强的意义,但没有普遍性。为了坚持道德的纯粹性,必须将其排除在外。
在这个问题上,儒学与康德有着明显的不同。尽管儒学同样坚持道德的纯洁性,但并不反对道德情感,认为人们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是非常自然的,正是由于这种敬重,人们才愿意成就道德。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成就了道德,必然有内心的满足,产生内心的愉悦,这完全是理之常情。
牟宗三看到了情感问题的复杂性,希望以“上下其讲”的办法加以解决。他认为,情感可以上讲,也可以下讲。上讲可以提升至道德高度,下讲则降到幸福原则。
幸福原则的情感是不能要的,道德高度的情感则不能不要。尽管牟宗三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他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不管怎样解释,在康德那里道德自律必须排除情感,而儒学反而对道德情感大加赞扬。
这两者完全不同。这种困难局面之所以出现,从根源处分析,还在两分方法的不足。在康德那里,只有理性才能成为道德的根据,而理性必须是普遍的,道德情感只具有具体性,不具有普遍性,所以必须排除在外。而依据儒家的三分格局,并不这样看问题。
儒家既讲仁性又讲智性。仁性是良心本心,是“伦理心境”,有丰富的情感性,所以一定要讲情感。智性是学习和认识,为了保障学习和认知的客观性,则不能讲情感。要从根本上克服在道德情感问题上遇到的麻烦,简单说一个“上下其讲”不足为用。
这不是一个能否在道德原则中加入情感的简单问题,而是能否充分认识儒家心学与康德道德哲学之区别的问题,是能否充分把握儒家道德学说之三分格局的问题,否则这个“加法”做得再彻底,也还是不能将儒学与康德区分开来,从根本上彰显儒家道德学说的特性。
牟宗三儒学思想方法的缺陷,不仅表现在对于良心本心认知的陈旧,以及由此导致的两分方法,更表现在智的直觉问题上。牟宗三早、中期即已涉及智的直觉问题,但重视程度不够,直到写作《心体与性体》仍然是如此。他自己讲过,《心体与性体》的一个重要不足,就是未能充分重视智的直觉的问题。
为了作出弥补,他开始写作《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正式从康德哲学进入,大谈智的直觉。在他看来,西方哲学不承认人的无限性,不承认人可以有智的直觉。
所以只能执于现相,是一种“执的存有论”;中国哲学承认人的无限性,承认人可以有智的直觉。所以可以直达物自身,是一种“无执的存有论”。由此出发,牟宗三还对康德物自身的概念进行了自己的诠释,强调物自身不是其他东西,只是智的直觉的对象;物自身并不是一个事实的概念,而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
康德不认为人类可以有智的直觉,所以物自身只有消极的意义,没有积极的意义。但康德毕竟还是肯定了智的直觉,只不过把这种能力完全归给了上帝而已。
与康德不同,中国哲学承认人可以有智的直觉,智的直觉所面对的不再是现相,而是物自身。智的直觉源于自由无限心,自由无限心与道德相关,包含着价值意义,所以物自身是一个价值意味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事实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