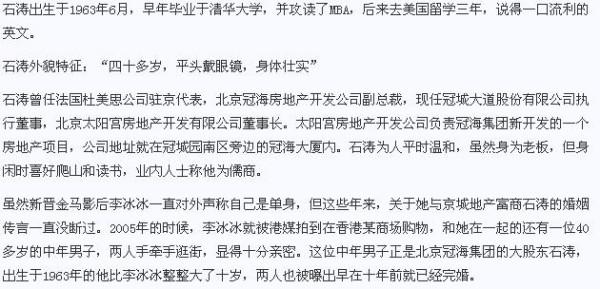石涛画语录 从《苦瓜和尚画语录》谈石涛的美学思想
自苏轼等诗人涉足绘事,并提出了“诗画一家”的观点,便有了文人画之概念。晚明之际,书画巨匠董其昌“南北宗论”的提出确立之后。中国画坛“文人画”与“院体画”昔日齐头并进、相互融合的局面,便有被“文人画”所一统的趋势。
崇尚作画时享受清澈、自在的快乐与悠然自得的心境,以趣味、意境、神韵、情态和品格作为品评绘画的第一标准,写形则次之。亦如苏轼所云:“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模糊了绘画个体,而讲求“使望者息心,览者变色”,造化中法,画的是作者之性情。
在山水画一科,每言便是上追“董巨倪黄”、“南宗正统”。自此之后,追求“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的文人画风格蔚然成风,不但董其昌个人影响之大,还有清代皇室追捧,加之附庸风雅者,“文人画”一统天下。
在董其昌“尊德性”和“道问学”辩证思想的影响下,清初画坛出现了各取一端实为一体的“正统派”的“四王”和“非正统派“或者称之为“野逸派”的“四僧”。
“四王”是典型的儒生风范,主张在继承中求发展,坚守儒家的中庸之道,被清初画坛奉为正统,并受皇家推崇;“四僧”中八大山人和石涛都是明代皇室后裔,对清朝统治者不是国仇就是家恨,另二位渐江、髡残都属明朝移民,剃度为僧,因此“四僧”更多趋向禅道。
整体来说,“四王”是儒家义理熏陶出来的平正中和,清丽典雅之画风;“四僧”则和而不同,貌离而神合,整体都趋于禅房花木的清幽空灵,淡泊明净的浑厚苍然。尤其是石涛在以“四王”为正统派“摹古”之风盛行之际大肆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和“我自用我法”的“妄言”,此与董其昌“尊德性”及“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如出一辙。
现在我们已正视石涛和王原祁为双峰并立之势,但在当时画坛,是以王原祁为首的“正统派”为主导,“摹古”之风盛行。石涛却如郑板桥所言:“石涛名不出吾扬州”。
石涛一生都在束缚与反束缚中挣扎,内心极度矛盾与苦楚。在其四年北京之旅中,一面求被皇家赏识另一面又不愿趋炎附势。这个自当是容易被人理解的,怀才之人当然愿意施展才华,望“文能提笔安天下,武可上马定乾坤”。如李白,起初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到不被重用而只作为玄宗的弄臣来填词作赋,诗酒赏花时,李白便“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直至“不可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拂袖而去,只演绎出风流才子和一代天骄的浪漫佳话而无丰功伟绩。石涛也是如此,在北京生活的几年中有赏识亦有强勉欢颜,所以最终石涛同样选择离去,回到扬州。重见旧友,把酒狂歌,吟诗作画,风流雅集。
重回扬州这一时期,石涛之画日臻完善,“看似无纪律,而纪律自在其中”。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大醇小疵,如邵松年言:“一生郁勃之气,无所发泄,而寄予诗书画。故有时若豁然长啸,有时若凄然悲鸣,无不于笔墨中寓之”。
可惜“古来圣贤皆寂寞”,“青天一明月,孤唱谁能和”。雕塑大师罗丹同样如此:“罗丹未成名前是孤单的。荣誉来了,他也许更孤单了吧。”(【奥】里尔克 著 梁宗岱 译 《罗丹论》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5月版 第1页)的确,艺术家是极其孤独的。
因为艺术家的脑袋在天上,全是纯真与美好,天马行空;可是,其脚却踏在大地,世俗名利之纷扰,拙劣之人的谬误。这些都拼命将其向下拽。艺术家一方面要立定脚跟,一方面又要直冲云霄,这是多么矛盾与不易。难怪吴冠中先生言:“艺术是从苦难中来的”,所言极是。
石涛实乃才华横溢卓越之士,当然希望被赏识,渴望展现自己。所以他“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论知遇”;而另一面却又说“欲明玄武歌中月,不照咸宁创国心”,难以忘怀的故国之思。这是石涛在期冀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亡国之恨中的矛盾与挣扎。
石涛一面抵挡着“正统派”之异样眼光或攻击之词,一面以自己的方式叛逆的继承着传统,沐浴董其昌之余泽。批判着清初“摹古”之风,曰:“今人不明乎此,动则曰:‘某家皴点,可以立脚。非似某家山水,不能传久。某家清澹,可以立品。
非似某家工巧,只足娱人。’是我为某家役,非某家为我用也。纵逼似某家,亦食某家残羹耳。于我何哉!”于是,大呼:“古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古之肺腑不能安入我之腹肠。我自发我之肺腑,揭我之须眉。
纵有时触着某家,是某家就我也,非我故为某家也。”挣扎于当时求“笔笔有来历”,与古人“同鼻孔出气”的画坛之风中,癫狂悲愤而言“我自用我法”,“无法而发乃为至法”。这又是大涤子叛逆的继承传统,张扬个性的欲望被传统程式压制的苦和与当时画坛主流膜拜的继承传统之意见相左所引发的矛盾。
难怪其时而把酒狂歌、飞扬跋扈、放浪形骸,时而却凄然悲鸣。矛盾使然也。
面对风雨晦暝、变化万千的大自然,以及纷繁复杂的人世,逍遥的庄子不免发出《人间世》的处世之道。对于像李白、张旭、苏轼、徐渭、八大、石涛和西方的梵高等这样的炽情之士怎不寄情诗画,以宣泄情怀。李白诗中充斥着愁杀、笑杀、狂杀、醉杀、恼杀,这些极度夸张的字眼。
他开心时便言“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杀人!”,癫狂时便言“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愤懑时便言“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我倒却鹦鹉洲”,愁苦时便言“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徐渭也是如此“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朱耷将八大山人写为“哭之笑之”,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在看到他们愁苦郁结的同时,不免也读到他们的对自己所坚持理念的执着。
冯友兰先生在《论风流》一文中提出了界定风流之士的四个基本要素:其一,玄心。即超越、打破自我境界。其二,洞见。即直觉人生真谛的能力。其三,妙赏。即具有深切的感知及美妙的情怀。
其四,深情。即一往情深的寄托、信念。正因为有了“玄心”,“洞见”,“妙赏”,“深情”为保障,纵使有人批评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也毫不足介意,“我自有我在”,且“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曲高和寡”哉。
“真名士自风流”,所以石涛难免自信的道:“此道有彼时不合众意,而后世鉴赏不已者;有彼时轰雷震耳,而后世绝不闻问者,皆不得逢解人耳。”并言“余画当代未必十分足重,而余自重之”,“后世自有知音”。此与黄宾虹:“五十年后识真画!”的感慨同出一由。石涛之作不免有瑕疵,但这“小疵”自瑕不掩瑜,正如俞剑华先生所言的“大醇小疵”,不会影响石涛在中国绘画史上独步古今、傲视诸贤的圣手之地位。
这些自信与桂冠,都源于石涛跨时代的美学思想。
《苦瓜和尚画语录》(以下简称《画语录》)的《了法章》中有言:“古人未尝不以法为也。无法则于世无限焉”此言尽显石涛对文人画观念的师承。石涛是认可法度的,但其更注重不能因有法而障于法,所以言“无法而发乃为至法”。
“是一画者,非无限而限之也,非有法而限之也,法无障,障无法”此体现了大涤子的辩证法观,即“亦一亦二”矣。如果作画没有了法则、法度,那么画家就没有任何束缚,就可能使绘画立而无物、无从着笔、不得要领,导致极端的虚幻色彩,少了可以交流的绘画语言范式,信笔涂鸦,而漫无标准了。
石涛有了此点的认识,便保证了他可冲破羁绊而又不至趋于失控。所以石涛之作笔无定姿,多变化;尊成法却不拘成法,不“画地为牢”。石涛画跋曰:“画有南北宗,书有二王法。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今问南北宗,我宗耶?宗我耶?一时捧腹曰:我自用我法。”
石涛在绘画实践中,也如其所言,身体力行。在《画语录》的《笔墨章》中,石涛提出了“蒙养”、“生活”这一对概念。“蒙养”取《周易》“蒙以养正”之意。《周易·蒙养卦第四》:“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利贞。”蒙卦的卦形是下坎上艮。坎代表水,艮代表山,合起来便是山水。《周易·序卦传》开头言:“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
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笼统来说“蒙养”是修养习练,“生活”乃体验事物之意。“蒙养”“生活”是一个整体,相互交融渗透乃至转化,若阴阳之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既受“蒙养之灵”,又解“生活之神”,不即不离,可谓我与物接,物为我化,有笔有墨。也就是中国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之境。以此可见,在绘画上石涛是相当重视“笔墨”的,如黄宾虹言:“石涛全在墨法力争上游”。但这笔墨是为表现作者内心最纯真、最美好向往及其真性情的,不能表现生活,虽笔挺力拔、墨汁淋漓,终将成玩弄笔墨的形式主义,虽然满幅笔墨,仍然是无比无墨、无病呻吟的拙作。
山川脱胎于大涤子,大涤子脱胎于山川,是“代山川而言也”。既然代山川而言,那山有是形,且“满目云山,随时而变”,就必然使石涛之作面貌多变。造化寄予石涛启迪“无间于外”,石涛迁想妙得“无息于内”,最终将胸中丘壑化为纸上林泉了。
石涛一则画跋写:“点有风雪雨晴四时得宜点,有反正阴阳衬贴点,有夹水夹墨一气混杂点,有含苞藻丝缨络连牵点,有空空阔阔干燥没味点,有有墨无墨飞白如烟点,有如胶似漆邋遢透明点。更有两点,未肯向学人道破:有没天没地当头劈面点,有千岩万壑明净无一点。噫!法无定相,气概成章耳。”这些对石涛绘画样式多变可见一斑,也是他在皴法、苔点上独树一帜的体现。
石涛之作的另一大特点是意境构建上雄奇、匠心独运。这与他“苍山四海”的通感是分不开的。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又有王观诗云:“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
”难怪古人将美女的双眉形容为“远山含黛”。石涛山亦海,海亦山的观点与诗人山水即眼眉,眼眉亦山水有着同样的情感联想,就是顾恺之的“迁想妙得”。有了妙得再配上千变万化的笔墨,当然别开生面,“外师造化”,而“中得心源”了。
吴冠中先生在《我读石涛画语录》中言:“程式化的山水构图可归纳为四个字:起(用石或树从画幅下边开始向上方发展)、承(用树或山继承接力,再往上伸展)、转(树或山改变动向)、合(与高处远山合抱成一体)。”石涛却是将地、树、山,景、云、山贯通一气,不拘泥成稿古法而独立思考。此与“正统派”代表王原祁“终不敢出公望门一步”成鲜明对比,石涛是“借古开今”,显然胜于“正统派”画家。
有人说石涛最大的成就不是绘画上的贡献,虽然其画作笔无定恣,画风纵恣放达,诗书画世称“三绝”。而他奋力挣脱古人和成法的束缚,尤其是在“摹古”之风盛行的清初画坛更是难能可贵。石涛那高度追求张扬自我个性及艺术解放与创新的思想,给清初画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
从“不立一法,是吾宗也”,“不舍一法,是吾旨也”到“一画之法”; 从“我自用我法”到,“无法而发乃为至法”;从“笔无定恣”到“笔墨当随时代”;从“搜尽奇峰打草稿”到“无间于外,无息于内”等等。
曹玉林评价为:“作为中国绘画史上一位最具创造活力和艺术个性的天才人物,石涛终其一生,都在与因循守旧,重复蹈袭的人类惰性作斗争。”石涛的选择无疑是勇敢的。
梁漱溟先生对“勇气”有过这样一段论述:“没有智慧不行,没有勇气也不行。我不敢说有智慧的人一定有勇气;但短于智慧的人,大约也没有勇气,或勇气亦是不足取的。怎样是勇气?不为外面威力所慑,视任何强大势力若无物,担荷任何艰巨工作而无所怯”,以及“没有勇气的人,容易看中即成的局面,往往把即成的局面看成是一不可改的”,看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石涛这个画僧,他可谓是有大勇之人。
在“四王、吴、恽”为代表的时期,赫然提出“我自用我法”,“搜尽奇峰打草稿”,“笔墨当随时代”这些观点。
没有疯狂似的野心巨胆,是不能作此想的。然而若无智慧,则此想亦不能生发。“智也,勇也,都不外其生命之伟大高强处,原是一回事而非二。
”无论何事,总要看其是否可能、不可能的。无论何成法定论,总要“气吞事”,而非被事所慑着。王勃《滕王阁序》中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此亦便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也!
无论石涛对传统持多么反叛和超越的态度,但其总不是“空诸依傍”,总有着对传统继承发展的一面。这就是谢稚柳先生言的:“流派的新生,从没有脱离先进高雅的熏沐与真实华美的感受,而能绝缘弃祖,混然自生的。”像“凤歌笑孔丘”的李白也好,还是“万点恶墨,恼杀米颠;几丝柔痕,笔倒北苑”的石涛也好,都是汉文化传统熏陶出来的文人。
石涛《画语录》中全是儒、释、道三家义理的融会贯通。像“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观物取象,通德类情”,“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等思想皆出于儒家义理;“天人合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有生于无”,“有无相生”,“朴散为器”,“道常无名”等说法则出于道家;“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诸佛圆通,更无增减。流入六道,处处皆圆。万类之中,个个是佛。譬如一团水银,分散诸处,颗颗皆圆,若不分时,只是一块。此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大知大授,小知小授”等等原出于佛法。无论石涛绘画作品还是美学思想皆如傅抱石所言“全自经典中出”,与古人“貌离而神合”。
石涛云:“是竹是兰皆是道,乱涂大叶君莫笑。香风满纸忽然来,清湘倾出西厢调。”显然看出石涛继承文人画那种自娱自乐,“以画为寄”的思想了。石涛的精神内涵与哲学思想都与文人画所追求的相吻合,可谓是叛逆的师承,而非“空诸依傍”。
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石涛借古开今,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搜尽奇峰打草稿”和“笔墨当随时代”的宣言。
时至清代,笔墨程式被推至极端,本是为艺服务的技却反客为主,凌空于艺术之上了。在这种背景之下,石涛提出“搜尽奇峰打草稿”给其有力的回击,无疑是兴衰继绝之空谷足音。这也成为创作源泉的至理名言,而永被赞颂。石涛的“搜尽奇峰打草稿”并不是单纯的描摹,而是“神遇而迹化”,为山川代言。
此便是“蒙养”、“生活”之功,以“知觉明灵”去体悟生活之趣,不仅非画地为牢、泥古不化,同时还非描摹、复制自然。所以,真正的艺术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亦是罗丹所说的“比真实还真实”。
《大涤子题画诗跋》:“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风气所转。上古之画,迹简而意淡,如汉魏六朝之句然。中古之画,如初唐盛唐雄浑壮丽。下古之画,如晚唐之句,虽清丽而渐渐薄矣。至元,则如阮籍、王粲矣。倪黄辈如口诵陶潜之句:‘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
’恐无复佳矣。”石涛要为山川代言,要自有我在当然要随时代风尚,发我之肺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面对着醉心于笔墨,膜拜于成法的清初画坛,石涛企图用“搜尽奇峰打草稿”来为其注入新鲜血液;另一面又企图用“笔墨当随时代”来唤醒迷醉的人们。真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石涛借古以开今的认识和贡献,与王原祁相比实在是胜之甚远。
《论语·子路》曰:“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狷者”可谓“正统派”的“四王”,是“改良派”在法度成法中改革变化,就是董其昌所言的“道问学”;“狂者”可谓“非正统派”的“四僧”,是“革命派”求张扬个性,求出奇制胜,自觉性更高,亦是董其昌所云的“尊德性”。
“正统派”的代表王原祁与“非正统派”的代表石涛实则同出一母,在文人画精神的余泽中各取一端,他们可谓双峰并峙之势,只有既恪守法度、循序渐进,又变幻莫测、出奇制胜,才能如《孙子兵法》所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曹玉林评价《苦瓜和尚画语录》的最主要成就有二:一是,“力排时风,强调作为绘画主体的画家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倡不拘成法,勇创新法,‘我自用我法’。”二是,“不囿于陈言和定论,大胆的将一系列全新的概念引入画理,对绘画美学的外延和内涵进行全方位的拓展,为绘画理论建设和绘画实践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
唐人韩愈云:‘惟陈言之务去’。”的确,石涛一面在他人醉心于“摹古”之时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慨然提出“一画之法”,主张“师造化”而“搜尽奇峰打草稿”,主张“我自有我在”而“我用我法”、“无法而发乃为至法”,主张“迁想妙得”而“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主张“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笔墨当随时代”……另一方面石涛确实是一位实践家,他身体力行无论在美学思想上还是绘画表现中都不拘成法,勇于创新,在古代经典中汲取营养加之自己的理解创制了许多如“蒙养”、“生活”、“氤氲”这样的概念,在用笔上“笔无定势”,“笔意纵恣”,“峰与皴合,皴自峰生”是也。
《画语录》整体是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其中又融汇儒、释、道三家经典,不免使之抽象难懂,产生误解。石涛作文如其作画,声情并茂,扬扬洒洒,使人沉醉在一种醍醐灌顶式的阅读快感之中,为文章气势所慑、为文章情思所感、为文章措辞所震。就如俞剑华先生言的:“《画语录》是一本伟大的杰作,虽有缺点,可以说是大醇而小疵”矣。
参考文献:
[1]【清】石涛 著 俞剑华 注译 《石涛画语录》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2007年8月版
[2]吴冠中 著 《我读石涛画语录》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9年5月版
[3]杨成寅 著 《石涛画学》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9月版
[4]曹玉林 著 《王原祁与石涛》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4年8月版
[5]卢辅圣 主编 舒士俊 副主编 《朵云第五十六集·石涛研究》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2年10月版
[6]张善文 著 《周易·玄妙的天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7月版
[7]唐·惠能 原著 邓文宽 校注 《六祖坛经·敦煌坛经读本》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5、年1月版
[8]林语堂 著 《中国印度之智慧·中国卷》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10月版
[9]李长之 著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年5月版
[10]洪治刚 主编 《冯友兰经典文存》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年5月版
[11]梁漱溟 讲 《朝话·人生的醒悟》 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年5月版
[12]【奥】里尔克 著 梁宗岱 译 《罗丹论》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