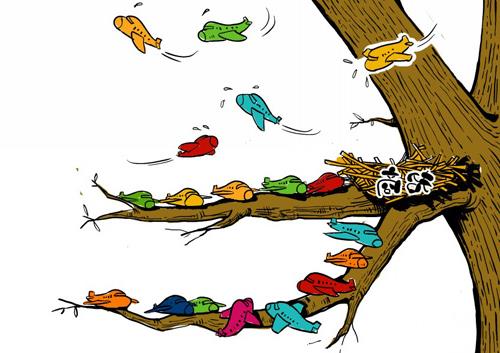于坚故乡 于坚:“我一直是个故乡诗人”
安琪:你一直坚持诗歌的中国性和民间性,中国和民间在你的概念里是什么样子的?“汉语”是你近几年强调很多的一个词汇,请给我们经过于坚自己定义的“汉语”。你在强调汉语之光的同时,却看得出你也是大量西方译著的阅读者,这是否构成一种矛盾? 于坚:这种强调是“在什么山说什么话”。
其实没有什么意思,完全是废话,如果存在者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已经被连根拔起,说这些话完全是废话,这是一个我们时代的话题。
一个认识论的话题,而不是本体论的话题,只是针对一些现象而言。因为我作为汉语诗人,有一种很现实的危机感,汉语这一百多年真是命途多舛。回忆一下,当年甚至到了要取消汉字的地步。
现在英语成为第二国语。普通话在消灭汉语方言,而且是制度保证的。普通话令写作者丧失身份,你再也听不出一个讲普通话的人来自哪个故乡。英语逐步成为一种生存工具,进而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最后导致汉语本身更书面化,也许有一日最终从日常生活退出,这不是不可能,因为未来是由今天正在学校里为普通话和英语焦头烂额的人掌握的。
有日语的现实可以参考,我曾经与一个研究人类学的日本人谈到语言,她说用假名译音的名词到现在都非常隔、生硬,用汉字翻译的才贴切。
但日语几乎已经面目全非,无数的翻译名词充斥日语,假名加速了外语进入日语的速度。语言的改变最终影响到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日本要再出现像石川啄木那样的诗人恐怕都很困难了。
汉语的危机,不是我在杞人忧天,诗人的地位降到中国历史的最低点,曾经是不学诗无以言的民族啊。今天在中国用汉语写诗的人,完全可以叫做“国难识忠臣”。西方译著的阅读与汉语写作是矛盾的吗?中国学校里西方译著式的教育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我所受的教育完全是西式的(它也许不是那么理性化的西式教育,但它肯定不是中国古典诗人曾经接受的那种教育),阅读西方译著恐怕不是什么新鲜事,在这个时代里,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阅读《圣经》很正常,阅读《论语》却有点标新立异。
安琪:你认为诗歌的标准不是根据教科书或者某个权威所确立,那它应该是什么样的? 于坚:标准各式各样,一个刊物有一个刊物的标准,一个诗歌圈子有一个诗歌圈子的标准,每个人也有自己的诗歌标准,但好诗只有一种。
这是一个玄学问题,用科学主义是无法回答的。标准就是一个科学主义的名词。
诗歌有无数标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标准,每个圈子有每个圈子的标准,但好诗只有一种。好诗就是可以蛊惑人心的诗歌,那些语词经过诗人的组合,具有返魅的力量。狄金森说:“它令我全身冰冷,连火焰也无法使我温暖。
我知道那就是诗。假如我肉体上感到天灵盖被掀去,我知道那就是诗。”说得好,诗是一种带来感觉,令人心动的语言。 诗是语言创造的一个存在之场,离开了这个场,诗就不存在。
谈论好诗必须知行合一。我的意思是我们只能在路过一首诗的时候指着它说,这就是诗。就像指着一棵树说,这就是树一样。关于苹果树的一切描述都与苹果树无关,而且越精确距离苹果树越远。
而什么语言会构成一个得人心的场,这是无法确定的。任何语言都存在这个可能,任何组合方式都存在着这个可能。场的大小、力度都要起作用。我最近说:“一首好诗是一个塔。
基础部分人人可进可懂。修养决定你可以进入诗的哪一层。诗的最深核心,塔顶部分,只有少数人可以进入,自古如此。但如果只有这个高处不胜寒的少数而没有下面的基础,塔就飘在天上。” 好诗就像中国哲学中的“心”、“仁”这些思想一样,无法概念化。
牟宗三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开端处着眼点是在生命。这个着眼点也是汉语诗歌的着眼点。诗歌是语言的寺庙,就是最高的语言,但它不是上帝的语言,是活的,生命的语言。
克尔凯郭尔说“上帝不是理解,而是行动”。有人否定诗歌的生命性,这是受西方诗歌概念的影响,把诗歌理解为对世界的理解。而中国传统是对世界的感悟。“好诗”就像“仁”、“心”这些思想一样无法定义,只能在知行合一中去妙悟,在具体的作品中去格物致知。
古代中国的诗论非常清楚这一点,古代诗论从来不说好诗是什么,只说诗如何才是好。“诗言志”并不是一个定义,只是描述了诗歌的可能性之一,“诗者,吟咏情性者也”也一样。
心的复杂性在于,人心所向,各时代并非完全一样,所向有普遍性的,有时代性的,有当下的,有永恒的。那些当下所向的诗,对永恒所向的诗歌是一个遮蔽。 在诗歌上,诗人必须承认不可知,诗歌具有巫术的特征。
这也是诗歌得以在技术时代独立并高踞于精神生活之巅的原因。没有比诗歌写作更困难的事了,每个诗人都知道,他不是在白纸上写作,他是在语言的历史中写作,你写每一行,都有已经写下的几千行在睥睨着你呢。
诗人永远不可能从第一行写起,他总是从过去已经开始的第某行继续写下去。因此你的写作总是与过去的写作有一个上下文的关系,通顺的关系。在我看来,那些通顺的诗歌,必然是可以继续下去延续时间的诗歌。
我认为诗歌是语言的如何说的历史,而不是说什么的历史。“什么”,其实自人类出现以后,再没有进步过,将来也不大可能进步多少,因为“什么”的进步在二十世纪的种种实验中已经被证明是灾难性的。
人类关于“什么”的在权力驱使下的探索、革命,一旦稍停,人类就重返故道。人间正道是苍桑。诗歌上的石破天惊总是在如何说上,它令已经趋于沉闷的“什么”再次活过来,成为我们时代的最通顺的感受。
“如何说”实际上总是“石破天惊”地重返“说什么”的历史,就像大海,总是崭新的波浪,总是陈旧的大陆。所谓“具体的普遍性”,它与过去诗歌传统之间的关系是活力复活的通顺而不是标新立异的断裂。 标准完全可以确立,像考试分数一样,如果确立者再有点儿权力的话。
例如掌握着出版发表的权力,例如博士先生具有讲授的权力,例如资金。完全可以把狗屎或者黄金作为标准确立起来。这要看确立者的目的是什么,是为天地立心还是沽名钓誉了。
安琪:你如何看待第三代之后关于中间代、70后、80后的代际命名? 于坚:我开始写作的时代完全是彻底的个人写作,写作行为就是自我娱乐。
后来被归到一个代里面去,给人的印象是好像我们是一个写作集体。其实在1983年与后来叫做第三代的那些诗人认识之前,我都是一个人在写,昆明的几个工人、学生以及尚义街六号的那些朋友是我的读者。
我觉得今天诗人热衷于巨大的群体命名与时代风气有关,也是一种中国特色。我个人不喜欢这种命名,容易把具体的诗人消解在一个大括号里,误导读者的阅读。例如“第三代”被概括为“口语”、“平民”、反文化、反英雄什么的,而我的作品似乎并非这些可以概括的。
我相信有容量的诗人肯定是大于这些括号的,括号只是平庸诗人的避难所。 安琪:1999年的盘峰论争影响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你作为当时的在场者和后来民间一方的主将,在事隔数年之后回顾这一事件,最大的感想是什么? 于坚:盘峰论争对一百年来已经成为“文化正确”的拿来主义的反思,对“民间”、原创性、生命感、身体性、对技术性写作的警惕的强调都是时代的先声。
我相信历史最终会意识到,那次会议的意义不只是相对于诗歌界的,而是相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我已经看到7年前中国诗人的声音已经成为今日整个中国文化界正在思考的最时髦的问题。
安琪:根牢牢扎在大地,树干却伸向蓝天,这也许是你诗歌写作的一个通俗表述,也就是说,你的诗歌写作是有深度有高度的,你是如何达到今天这样的写作境界?在当下诗坛,你是否有独居高处不胜寒的感受? 于坚:道法自然。
像一棵树那样诚实地,一截一截地生长。不要指望越过某些阶段,一次搞定。
今天的写作青年以为可以通过直接学习最时髦的例如“后现代”来搞定,但这是写作,不是玩摩托车,在诗歌上没有什么型号会过时。你越过的阶段最终会报复你。写作是你一辈子也搞不定的事情,总是重新开始,日日新,但是重复最基本东西,一次次回到大道。
是的,在精神和思想上我越来越孤独。存在就是孤独。但在日常生活中,我有很多好玩的朋友,我不是自命清高的人。 安琪: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吗?请原谅你的许多文章让我产生这样的联想。
于坚:我确实不知道民族主义是什么意思,如果它是一个概念,例如意思是非我族类,就可以灭绝,例如纳粹,我肯定不是。
但我确实对这个词有好感,我是母语崇拜这个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我很难想象一个不热爱母语的诗人。语言交流当然必要,但那是一种技术,而诗人与神灵世界的联系肯定是母语的,祖国众神肯定是说母语的。
安琪:你经常出席各种国际诗会,中国当代诗歌在国际中处于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它的前景如何? 于坚:曾经一直是古董和意识形态小摆设的位置。现在有些改变,逐渐正常,那也就是一个中国诗人在中国的位置。我的意思是你的诗在中国处于什么位置在世界上也差不多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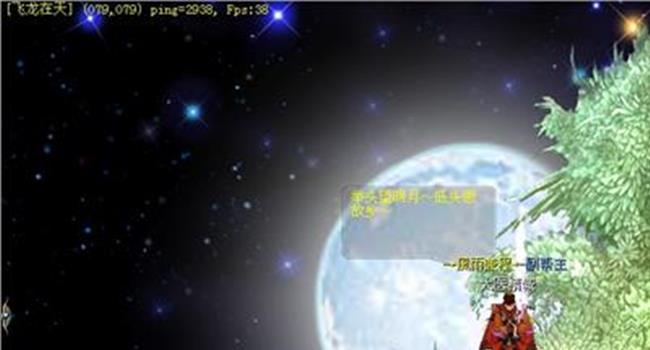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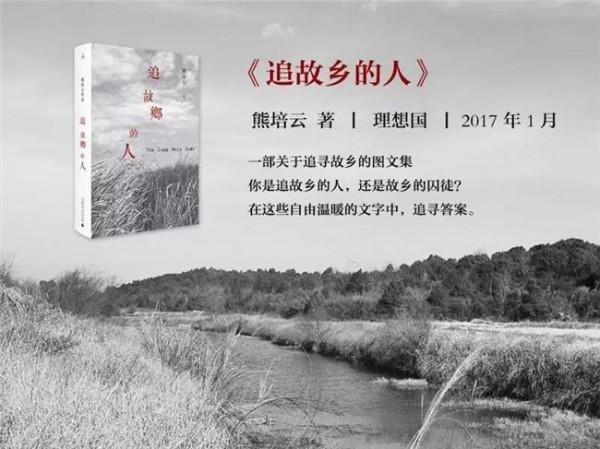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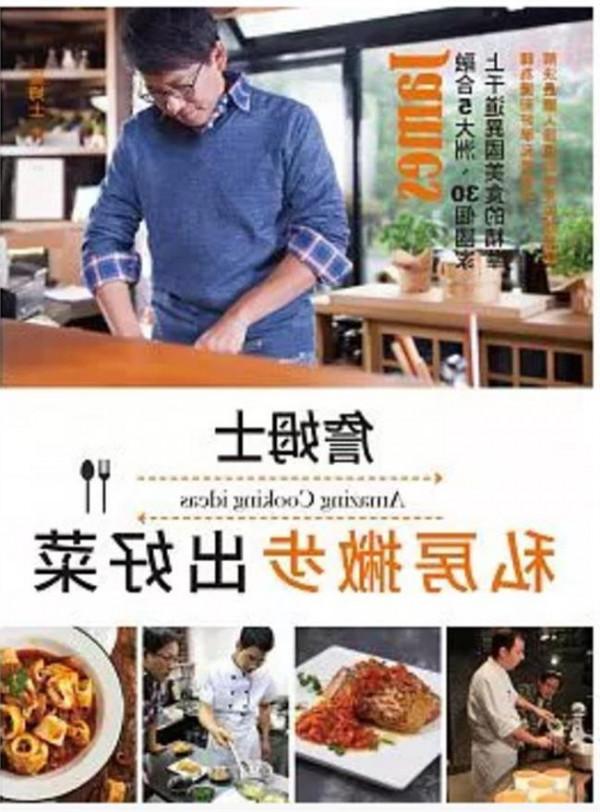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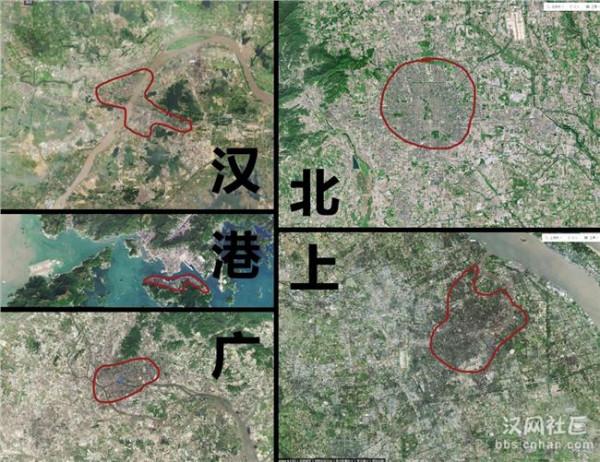




![>马坚古兰经 古兰经 马坚译本 普通话[男声]诵读](https://pic.bilezu.com/upload/b/b5/bb5697da1e86c19b3cd078af931c7459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