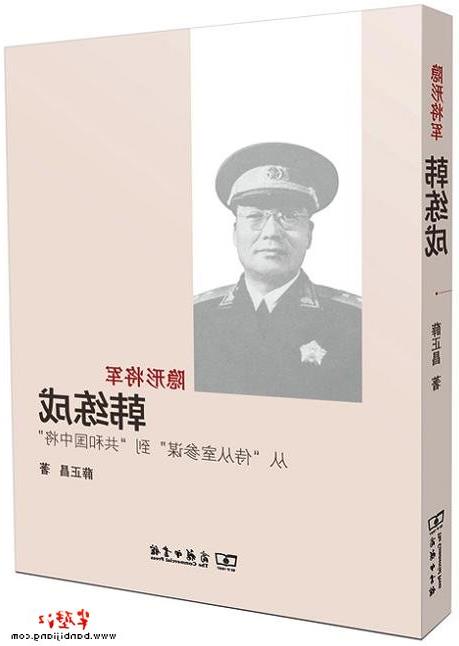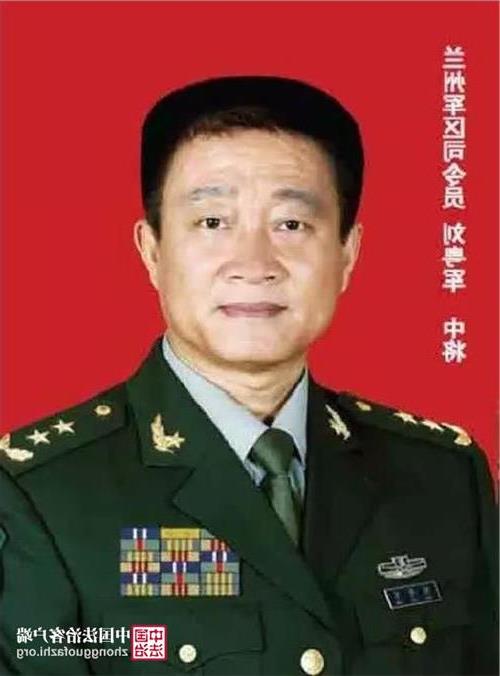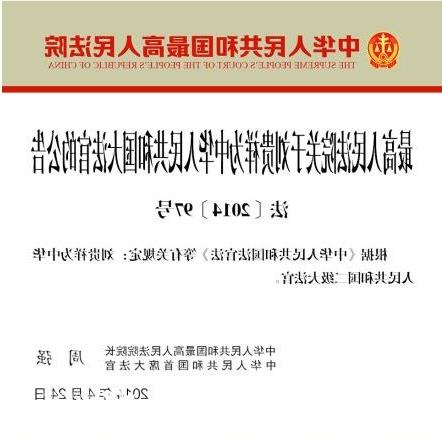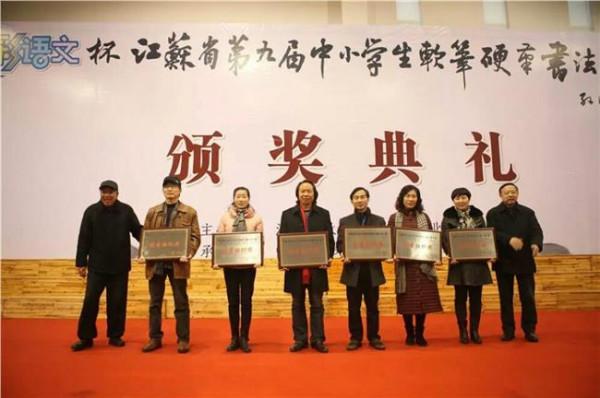刘正成张铁林 刘正成朱清时魏明伦张铁林曹宝麟对谈书法艺术
对话:刘正成、朱清时、魏明伦、张铁林、曹宝麟
主持: 李廷华 文化学者
李廷华:各位朋友,我是今天晚上对话的主持人李廷华,今天,我们以刘正成先生在北京举行他的个人书法展览为契机,邀请了几位朋友来作一个对话,我来介绍一下。
今天展览的主人刘正成先生,曾经担任中国书协的副秘书长、《中国书法》杂志社长兼主编,现在是《中国书法全集》的总主编,国际书法家协会的首席主席,他曾经在长期的书法组织活动中,举办过多项全国性和国际性的书法展览,这次是他从事书法艺术活动几十年来第一次在北京举行自己的展览,在举办展览的同时,邀请几位朋友对话。
朱清时先生,南方科技大学的创校校长,曾经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因为他在教学改革方面的探索性行动,现在已经成为国内甚至波及到国外舆论的一个焦点人物,这次的座谈以前,我有点担忧,我说朱校长可能无暇谈艺。今天见到朱校长,处于教育改革风口浪尖的人物抽暇参加这样的一个书法活动,他是怎么样一种文化心态?等一会儿可以请他谈。
魏明伦先生,大家都比较熟悉,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副主席,他的著名的戏剧作品《巴山秀才》,在大陆演遍之后最近被李少春先生的儿子李宝春,移植成京剧在台湾上演。今天魏明伦先生作为老朋友欣然远道从巴蜀而来,那么,两位巴蜀才子在京华相会,相信他们会给我们发表精彩的谈话。
张铁林先生,大家也都很熟悉。他的影视剧方面的身份就不用说了,他还是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的院长。我对张铁林先生个人有一个印象,我认为他是一个圆梦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由于环境和天分,他曾是一个蓬勃成长的美少年,他也曾经插过队,为了谋生,曾经在农村还干过抬死人这样的劳动。
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到了他的圆梦时期,他同时准备考美术学院和电影学院,结果他选择了电影学院。在影视方面成功之后呢,铁林先生又对书法、美术这些他从小钟情的艺术又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又开创这个暨南大学艺术学院,延揽了大批的有志、有才之士,在南国艺术教育领域开辟了一片沃土。他的文化经历,给我们会有哪些启示?我们等会也希望铁林先生能够畅所欲言。
曹宝麟先生,我要特别介绍他,在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之后,他是王力先生等人的研究中国语言史的首届研究生。这里有一个文化脉络,他可以说是赵元任的再传弟子,就是清华国学院流脉下来的。宝麟先生多年以来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可以为一篇文章考证十年,他的《抱瓮集》在中国书法学术界,是必读之书。首先是在台湾出版,现在又在文物出版社出版。
李廷华:五位嘉宾之中,既有改革风口浪尖上的热点人物,又有把冷板凳坐穿的人物,济济一堂,来进行中国书法和中国传统文化跨学科的对话。
我们先请这次活动的发起人刘正成先生发言。刚才忘了介绍一点,刘正成先生最初也是一个文学作者,可以说就是一个作家。最初问世的东西是历史小说,最初是四川文学的小说编辑,以后因为同时具有书法才能,当时中国书法家协会的老领导陆石先生就调他到中国书协工作。
20多年以后,正成先生第一次举办了他个人的书法展览。正成先生,你可以向各位朋友谈谈自己作为一个当时的文学青年、文学作者、以后的书法家、书法活动组织者,这多年来你的感受。
刘正成:当年,我在四川从事文学创作,但业余搞书法,书法是副业,文学创作是正业。到了北京以后,文学搞不了了,只有搞书法。我想,书法要求作者的文化程度是不是要低一点?除了这个书法活动是当代人在进行,这个书法作品与当代的文化有什么关系?应当明白,我们的书法艺术创作并不是仅仅复制着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它是表现当代人的艺术,它是当代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今天有记者问我,他说现在都用电脑,书法还能存在下来吗?我说只要我们中国人还使用汉字,那么这个艺术肯定存在。由于不写字,那写字的人不更显得突出吗?哈!作为纯艺术,还能够活跃在我们生活中间。二三十年以前,那时书法认识在我们现代文化来看还非常落后,认为仅仅是写字而已。
我们有责任把审美观念进行普及,我们写的是古代传承下来的书法,又是当代的文化艺术。如果你完完全全是临摹,你就是古代书法的复制品,如果说你把这个古代的书法赋予新的生命,就是活的一幅生命图画。
我记得哲学家叶秀山说过"传统就像一条河"。苏东坡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河里的水在不停流动,它不是凝固的,我们要成为河里的一滴水,顺着河流流下去。但这不是重复与复制,河流昨天流过的水和今天的水是不一样的,明天这个地方的水又变了,所以我们既要融入,又要变化与发展。
这次展览是我来到北京近30年后的当下状态,它是不是有不断的发展变化?我追求作品对此时此刻状态的表现,它是否能反映我的创作与审美的水平提高?这时候正好可以请老朋友们把把脉,我的作品能否真实、准确地体现出我的创作状态?在座各位分属不同学科,但又都是我的老朋友,大家很不容易坐到一块来,从我的书法展引申到文化问题。
那么,我们当代书法与文化要怎么发展,让它呈现什么样的文化品质?我想,这个跨学科的课题讨论,是能够产生相互的启示作用的。
朱清时:首先,我不敢当"教育家",也不敢当“改革家”。我当中科大校长10年,2008年退休。我退休已经1年以后,深圳要办南方科技大学,从全世界选校长,遴选委员会一致投票给我然后选上了。当初,我并不想去,就是猎头公司要见我,我都不见。
一直到深圳市领导组织个代表团来看我,然后一些老的遴选委员,老朋友告诉我,我们中国教育界想做一些改革,用了很多年都因为条件不具备没有做成,我们这代人退休了,但是还是有一些教育改革的梦想,他们叫我不要放弃这次机会。因为如果失去了这次机会,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教改可能还等上20、30年才会再来机会。
我到南方科大去想做一个最最基本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还原教育到它的原点上,就是我们教给下一代知识,给他技能地让他变成全能。我觉得最近几十年我们国家教育从给学生知识,让学生能力加强,逐渐被一些符号、学历代替了。
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校的学习实际上是为文凭在奋斗,争取到文凭的就够了,他就可以卖钱了,教师也没有积极性去提高教育质量。我希望我们的学生不要国家学历,但我们保证给学生一流的教育让他学到真本事,因此归纳出来我们要改革的事情就是丢掉铁文凭,捡起真本领!也希望能为我们浮躁的教育树一个示范,让大家思考一下教育是不是要改变本来的东西,而不要过分注重文凭。
各部门对这件事的看法也不一样,现在是推行十分困难。这个周末,刘正成的书法展我也得到一个机会,能够从这段时间以来一直在纠结的这些事情中间逃身出来,进入到另一种境界。像我们这样的年龄(我和正成兄都是66岁),我们都很明白人生要有张有驰,就是说,到需要的时候,能够把整个思想放空,能够把自己的身体松驰下来。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学习禅定,禅定的核心内容就是把思想放空,什么都不想,让你处于最自然的状态,你的身体就可以很快的恢复,你的思想就可以恢复活力。我学习书法跟我学习禅学一样。
我不是一个书法家,我是一个票友。怎么把字写好?最近这几年,我觉得想写好字,我就必须进入到学习禅定的这种状态,思想放空了,心就凝聚到一点上了,凝聚到一点上了,笔随手走,手随心走。这个时候这个字就写活了,字写活了,我自己的身体进入空灵的状态,这种状态对于一个长期纠结在事务中的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境界。
所以我很感谢正成兄这个书法展能够让我有机会到北京来,让我进入到书法的境界中,重新去体会一下这种空灵的状态。
我是学自然科学的,但是我一直相信书法艺术和自然科学是相通的,但是要理解这种相通不是外面的书报所介绍的很多人说的那种简单的类比,那是很牵强的,真正要理解艺术和自然科学是怎么相通的话,需要进入到佛学的一个新境界,这个境界在《楞严经》上叫做寻阅发现,就是跟寻你的阅历到什么程度,你就认识到什么程度。
我现在开始领悟到这个书法艺术实际上就是佛学讲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用几个字来说就是:“由戒入定,由定生慧。”当一个人真的有定力,思想定下来之后,你慧就出来了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就包括书法、绘画,包括人间所创造出的一切的东西。
我很愿意继续给正成兄和我在座的文艺界朋友,一起讨论,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些认识上都有所提高,我就说到这里,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魏明伦:今天是谈书法。对于书法,我完全是外行,我是书法盲,请我谈书法,就是问道于盲。我这个人是逆向思维,我突然对“问道于盲”这句成语产生了怀疑。问道于盲有什么不对?盲人、瞎子不等于不识路,既然他在那站着,他从天上掉下来了,说明他已经识路了。
问道于盲不一定不对的,问道于聋才不对,聋哑人听不见,说不出。你问错了人!问道于盲,说不定那个盲人恰好是一个高招,那个盲人比一般人更识路,我是逆向思维,正因为我是一个书法盲, “不识书法真面目,只缘身在书法中”,我完全在书法之外,也许我是“旁观者清”。
我认为书法过去是翰墨——翰林笔墨。现在却变成有墨无翰,或者说墨多而翰少,古代书法不是为书法而书法,都是有具体的生活内容,文章、诗歌、对联、奏折、文告、判词一直到书信都是先有生活内容,后有书法,不是为了书法而书法。而现在,书法已不是生活派生出来的艺术,只是玩弄图形。
书法是读图时代的产物。现在是读图时代,书法在当下已经脱离了它的人文的内涵,而转向了图像,就是玩图形的。它符合读图时代的需要。
书法符合快餐文娱的特征,一挥而就。它相对于其他门类,相对于我写戏剧,玩书法快多了。学的时候跟其他的门类都是一样的,都要十年寒窗,都要十年训练,但在实施的时候书法快,书法比其他任何门类都快。
书法的商品含金量太大,商品属性太强。书法与我们这个读图时代、快餐时代、商品时代一拍即合。由此而来也就墨多翰少,甚至于有墨无翰。也就是说它没有内容了,好像已经不是意识形态了,已经没有什么内容了,不仅是形式大于内容了,而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内容了,反正就是把各种字凑在一起。人们看也不是看内容,而是看那个图形。
像朱校长你抄心经这就是很少见的,因为心经是有内容的,是一种禅学、佛学。现在的书法不知道是“入世”还是“出世”,这个“市”不是“世界的世”而是“市场”的“市”,不是那个“入世”而是“市场”的“市”了,而是赤裸裸的进入市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墨多翰少,或者没有翰了,墨就是墨那就是墨了。这是我一个外行,站在书法之外,来看看书法而已。说得不对,你们批评,你们指点。
张铁林:我这个人,将来可以把我的成长经历,提供给有兴趣的人研究一下。我小的时候奶奶就说我“狗揽八泡屎,泡泡舔不净”,就是说兴趣太广泛,啥都不深入。小孩子兴趣多,人家说这孩子很可爱。随着年纪长了,依然是兴趣很广的话,你就是一个“万金油”,不能专一。
但是这里面却还另有涵义。我特别有感于朱校长的发言,他说要回归教育的原生态。其实我在创建暨南大学艺术学院的时候,就有一个基本的想法,我认为要把艺术的专业教育回归到接近原生态的理念,艺术的起源之时,耳朵听到的“音乐”,眼睛看到的“图画”,心有所感,嗓子眼里就飞出来歌声。
音乐和美术这些原本不可分割的原生态的集合体,在西方的教育体制观念下被分割了之后,出现了美术学院、音乐学院、这学院那学院都这样分开了。
实际上就剥离和切割了原生态自然人的原始天性对艺术的天然依附。我做艺术学院希望把比较有代表性的艺术学科重新摆放在一起,让学生能够有机会体验艺术精神的完整统一,回到那个原生态,尽量去接近和模仿艺术形态发生的原始状态。
再说的通俗一点,美术系同学在琴声中绘画,音乐系的同学也能有机会在书法和美术的气氛中歌唱,让美术和音乐以及动画的学生还有机会了解电影制作的现代科技综合语言形态,这是我在当初创建艺术学院初始时的基本想法。
所以我特别有感于刚才朱校长的发言。就是不要脱离原始、本源和原生态的精神链接,去研究无论是多么高深的学科,特别是教育。我个人的状态就是尽量保持在艺术实践的综合空间里面,我每做一件事情,都尽可能做到由表及里,融会贯通地去捕捉艺术道理的脉络,都是得益于我追求的综合知识结构。
我从来不把自己界定为某一个职业类型,我是所谓随遇而安的自然人。今天我是演员,明天我是编剧,改天是导演,来日是教师,后天写大字的时候,我又是一个书法票友,总之,艺术的精神和艺术的营养永远是相濡以沫,不可以分割开来。
按今天的对话环境说:第一我是一个晚辈,第二我是一个外行,我找到一个自然的位置,正因为是这样,我可以比较客观地观察一个现象。我今天参与了正成先生的书法展览,深有感触,千头万绪,我相信我跟多数人对今天展览的感触不一样,我观察了很多现象,我想尽可能简练地表白我的特殊感想。
就眼前而言,今天由刘正成先生展览而引发出今晚这个对话的形态是从来没有过的,是一个综合性的,是自然科学领域、书法学问领域、社会科学领域、以及我也沾一点边的影视文化,它是一个综合教科文的集合体。特别是书法,作为传统艺术精神在出世和入世之间自由行走,在各个文化学科之间自由穿梭,这就是正成先生这些年,特别在这几年所从事的社会实践中的一大特色。
我和正成先生由相识到相知的这些年,是正成先生精神不那么愉快的一段时间,但又同时是特别振奋的一段时间,我见证了刘正成先生在这个时期作品的精神升华,思想脉络发展的形态,正成先生在近十年中间的社会活动,是横贯古典和现代,纵贯东方和西方。
上高山理佛,踏潮汐去看海,非常非常广泛深入,非常非常综合贯通。
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下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书法学者所做的社会实践研究,它的社会活动的形态是极具中国传统精神特征的承上启下的学者代表,我认为他的创作状态也最契合,甚至最融合书法本源精神的发展脉络,我们说中国的书法是传统中国文学精神、人文精神和社会哲学精神的最有代表的符号,它集中国艺术、思想、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之大成,它博大而精深。
我们收藏人常说收杂项不难,难在书画,书画则难在书法,深不见底,莫名其妙,学问实在太大。
不消说在全国,我们在北京观摩过数不清的书法展览,也参与过“研讨会”不少,像今天这般展览盛况与参会人员社会身份的多彩纷呈,角色的形态各异,它的丰富性,高端性,广泛性都是空前的,令我们好奇和兴奋。而我们以前参加过所有的书法展览的研讨活动,都显得非常单调,苍白和程序化,就书说书,就书法论书法那能论出个啥来呢?
我常常在想,当今时代这么多书法人,相对古代而言,也还算是挺繁荣的吧,倒是赶上好年景了,写字能挣钱。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相当一批人靠写字为生,还可以靠写字买宝马的也不在少数,不然为什么众人趋之若鹜地写毛笔字啊?我们今天的书法展览忒多,书法家也忒多,成了当代社会附庸风雅的文化标签了,但是面貌都很相像,象克隆出来的多胞胎。
艺术最忌形而上地相互模仿,形成习气。当然,书法有特殊的学习的程序,这个是为了继承捍卫和发展古典精神的学习总结,但是书法成熟的最终表达,是要崇尚个性精神的,因为没有个性的书法,书法精神就不存在了,正成先生作品最感动我们的,就是个性鲜明突出,人文的精神突出。
接下来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刘正成先生的展览里面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原创诗、文,这又是体现书法精神的实践。
有很多朋友知道我收藏手札,我对手札的感情非常深,正是基于前面我对书法精神的认知。因为手札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既是人文的,又是艺术的,更重要的,它是真实的,不是客套的,它不是应景之作,为展览之用,它为了两斗米、一把盐、窃窃私语,推心置腹的往来心声,这些心声流落到纸上的东西是最全面的书法精神核心,是文人书法的最高境界,而这种精髓在正成先生的作品里明确地显示出来。
有识之士是可以看出来正成先生展览的这个价值的,我确信不疑。
所以我说我观察的角度,也许跟很多观众朋友不太一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基于这十几年我见证了正成先生的社会活动和观念变化的形迹,承上启下的学术责任感。我曾经多次聆听正成先生和西岛慎一先生通宵达旦的谈论中国书法史,他们谈得投机而系统,那么有兴致。
两个人语言不完全通,全部写在纸片上,我是既得利益者,最后纸片我是全部收藏了。我是见证了的,我是一宿一宿的在听他们谈话,当然我受益良多,在今天对话的场合,我感受很多,我是一个学生,我诚惶诚恐是如履薄冰,我在听着每一位先生讲话,我在大学我的学生中间也是学习,我常常跟学生学到我在外面学不到的东西,有机会参与今晚对话我觉得特别难得。
李廷华:铁林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但他这番话完全真诚。他让我们进入一种什么状态呢?人生这样的状态,他既是艺术的,又是发自心底的,他既让我们感觉轻松,又让我们深入。
张铁林:我补充一点,刚才我说的书法到了一定的程度一定要强调个性,我不妨举一个我这个行业的例子。大家注意到一线的演员,凡是所谓的明星,他们都有特征。你注意看,这些有名气的大演员,他的台词节奏和台词语法逻辑都有特征,不是约定俗成的,不是习惯性的程序化的说法,他们标点的停顿法是不同于大部分演员行活儿的,说话的特色影响到表演的特色。
然后是每个人的创作状态,一个好的演员,是需要强化特征,保持特征的,我们老说运动员心理素质要好,什么叫心理素质?就是控制身心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稳定和平衡的能力,这和我们的书法实践难道不是异曲同工吗?如朱校长所说,要借助禅定的练习,用中国最精华的训练方法来使得我们身体和精神状态得到充分的休息。
如此做到心平气和,才能悟大道理,才能写好毛笔字。现在大家太忙了,太急着挣钱了,没有休息的时间。我住口,再说我就喧宾夺主了。
李廷华:你是真诚的、有艺术性的发言演说。那我们这样座谈又进入一种很活泼的状态。宝麟先生还没有谈,我经常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可忘记书法的文化性,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书法的本体和专业性。今天宝麟先生的到场,我心中是这样评鉴的,在座者明伦和正成都是自学成才的,宝麟则是受到了完全的大学教育,北京大学的硕士,以前是学工业?(宝麟先生:对。
)那么就是说还是以前的家庭熏陶和少年的爱好决定了你以后的生活方向,我看到过你网上的一篇文章,从小生活在一个书香翰墨之家。
除却对米芾书法的精研,宝麟先生的旧体诗词,书法界可能也无出其右者。宝麟先生和正成先生一起编撰《中国书法全集》《蔡襄卷》、《米芾卷》和《北宋名家卷》都是他主编。
他把现在能够看到的每一件米帖考证得清清楚楚。我自己感觉乾嘉时期的学术在书法方面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里,学术界、书法学术界还有如此的人物,让我们感到亮眼,让我们心灵感到慰藉。
张铁林:你让曹先生说几句,你这样就是喧宾夺主了。
李廷华:我就是引这个话出来,现在请宝麟先生从他的书法世界里头,来谈谈他对书法文化的看法。
曹宝麟:原先听了三位大家一说以后,就觉得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刚才廷华引一下这也很有启发,因为我可以和我下午会上所说的那些有所关联。
我之所以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对话,这要感激正成兄。正是他所组织的一件件大手笔,我们才有一个比较专业的东西可以做,不然的话,我们恐怕到现在依然是碌碌无为。只有在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并且做好了,才觉得对得起这辈子也对得起历史。
从<>开始,现在再回过头看自己当时写的一些词条,还是比较幼稚浅薄的。而通过编写<>,不断得到学习磨炼,逐渐使自己变成某个领域的专家了。正成是帅才,象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他能够把这个千军万马都安排得非常的妥贴。
哪个人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他都物尽其用各尽其才。他知道我对宋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原先连南宋名家都安排我编写,后来实在因我接受的任务太多了,肯定难以分身,南宋这部分就派给方爱龙做了。
就我自己编的米芾、蔡襄以及北宋名家两卷来谈,我没请艺术顾问,都是独立完成的。我一直是比较信奉自学的一个人,尽管我也不是专业出身,但我想通过自学如果学风端正、方法对头的话,终究还是能学会的。包括这两位,魏明伦和刘正成先生,尽管他们的学历不高,但是最后都成为了专家,都成了某一方面的很有造诣的人物。
其实,只要你锲而不舍,总是会有成就的。我自己觉得<>是我的铭心之作,花了10多年时间,纠正了前人的不少错误,对一百多位名家之帖心系多年,应该也算是半辈子心血所寄了。所以我非常感激正成兄。莫逆之交是要凭良心的,这不是一种利益交换。
我在今天下午的会上发了一点感慨,也许这骨鲠在喉这么多年是不得不要一吐的事情,这次终于有机会吐出来了。刚才谈到教育问题,我想发表一些看法。书法到底定位在什么地方,也许一直都在讨论而且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书法作为一个专业,作为一个门类,很晚才有,按照现在的大学本科教法来看,本科其实在哪一个专业毕业都还是离成才很遥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尽自己的责任,引导他们走上正轨,这样以后也不会走入迷途。我想说书法既作为古典艺术,必须要在文史这方面补充自己的营养。我非常占赞成蒋维崧先生把书法归入中文系的观点,认为是非常有必要的。
李廷华:今天这个对话,铁林先生有一个评价,认为在书法界的活动里头,还没有这样几位人物坐到一起谈这些问题。我也有一个感触,正成是多年来第一次在北京给自己办书法展览,就利用这个机会邀请几位进行这样的对话。我还注意到,五位先生除了个人的专业以外,都表现出一种急公好义,就是一种文化担当和社会担当,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表现。
朱校长已经是功成名就,中国科技大学十年的校长,完全可以安度晚年,现在面临这样多的问题,是一个首先吃螃蟹的人。
明伦先生做全国政协委员二十多年,干了大量的打抱不平事情,他在政协会议的发言,曾经是多年被人们关注的热点。宝麟先生做的是冷学问,他平常的一些行事却十分有血气热情。那么我就归结到一个主题,我们的书法,我们的文化,到底在人的精神里头是建设什么的?包括我们的教育,包括现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到底要使我们的民族在我们的努力之中,在我们的行为表现当中往那个方向走。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文化的社会承担,再谈一谈。
我们现在的社会,思想发展脉络,没有离开80年代初期的探索。比如,明伦先生80年代初期所著剧本《巴山秀才》到现在还是不用改呀。《地狱变相图》表现的思想内涵,到现在也还有意义。正成兄是不是可以谈谈,你从当年的小说到书法再到现代文人的社会责任这个方面谈一谈你的观点。
刘正成:很奇怪,我30年前写的这些小说,冥冥之中,它在暗示、昭示、演示着我当下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我回答不了。以前写的小说我是旁观别人的,30年以后,我写小说中的故事,竟然变成我自己的事了,这有点奇怪了。
我想这个问题就是科学难以解释。之所以30年前写的生活和后来的生活相同,我们面临生活的问题,从古到今都是有着共同性的,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在那里。我这次的书法作品里面有一组叫“黄州吊苏”:我拄着竹竿漫步在黄州的长江边上,我就想这个水是从哪儿流来的。
喔!不是岷峨雪浪、锦江春色流过来的吗?这和苏东坡当年竹杖芒鞋踱步在这里时所想到的不是一样吗?后来杨慎又来了,他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不正是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翻唱吗?是的,生活在变,那些共同的永恒的主题,它是存在的,是不变的,而且是惊人的相似。
也许一千年前的苏东坡在谈到这个“逝者如斯”的问题时,又和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不谋而合!
爱因斯坦相对论在追寻一个“统一场”论,我们人的生活命运,无论古今,都是宿命?朱校长的论文《缘起性空:现代物理学与佛学》中讲过,现代物理学千辛万苦爬到一个山峰的时候,突然发现,佛学早已坐在这儿,等着你们来了。霍金的弦论说,世界是琴弦上的音符;佛学有藏识海,它说世界不过是大海中的波浪。这岂不是异曲同工?
儒学说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我们很难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物,谁是先谁是后,就像圆环一样。只有某一点确定下来,乃能知其孰为先,其他的就是后。这次我为自已的展览取了一个命题叫“江山寻绎”,被我女儿翻译成“在自然和历史中去寻找创作的灵感”,这就是在测试千古以来人心相通的准则。
我们五个人,从事各自的行业,一旦和中国书法文化联系起来的时候,大家就有共同的话题,这就是爱因斯坦相对论里面那一个“统一场”在起作用了。我觉得中国当代书法的发展也好,中国当代文学也好,中国当代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也好,或许都能找到共同语言,都需要各种学科认知的融合。
中国的学术在古代分科,无非“经、史、子、集”四部,或“礼、乐、射、御、书、术”六艺,探讨知识的方法特征是综合的。西方的学术是分析的,从达尔文以来,分科为数学、物理、化学等等,以至分得无以复加的细小。例如,以前医院分内科、外科,现在内科、外科之内已分了几十个科,知识被切割为各个小块。
但在今天,我们是否物极必反要走入一个回归综合的时代,只有综合的时代我们才能重新把握这个被复杂化的真理的时代。好多年前,我听朱校长讲过“蝴蝶效应”:一只蝴蝶在亚马逊河的上空轻轻的扑了一下翅膀。
它所引起的气流变化,最终在纽约上空演变成一场风暴,但是,从蝴蝶的翅膀的扇动到一场风暴的过程却无法用现今最大的计算机去计算,为什么?世界就是这样,具有不可知的特性。
不可知是我们共同的主题。我们从事书法也好,我们从事影视也好,或者从事科学研究也好,我们也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朱校长也好,明伦兄也好,铁林兄也好,我都极力把他们往书法圈里拉。为什么?我可以向他们学习,我们能找到共同的语言。
就是这一点,让我们坐到一块来了!中国的文化就是综合的,你让他分离是不可能的,是互相交叉的。所以我感觉文学小说或者书法或者其他的门类,都有一个永恒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人生对理性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