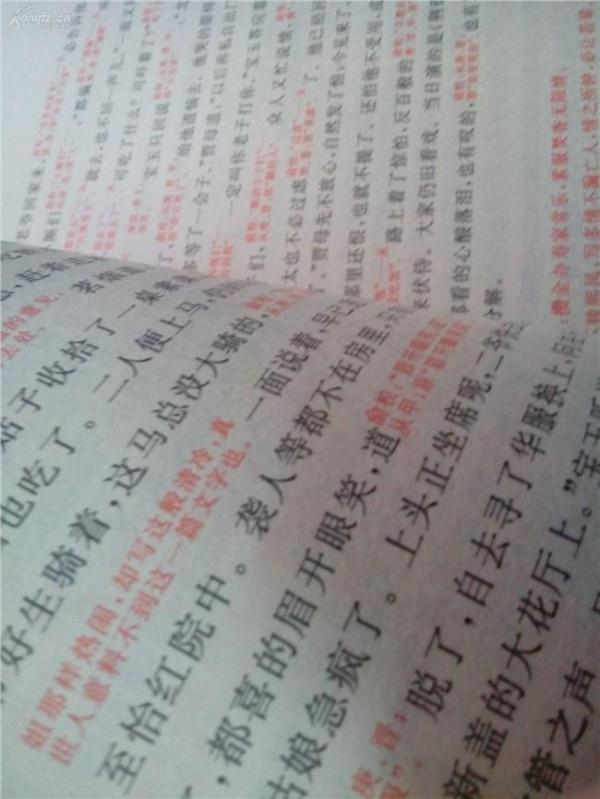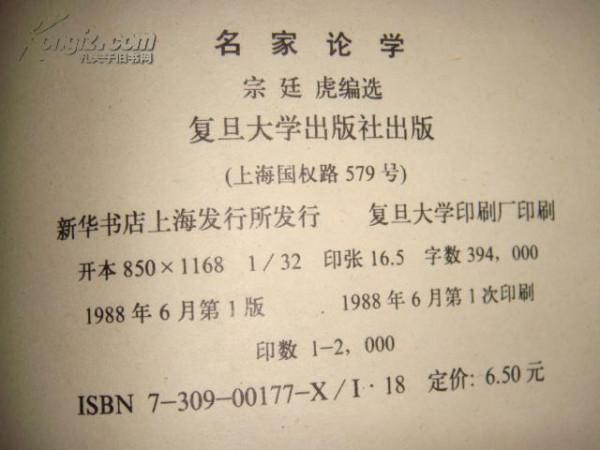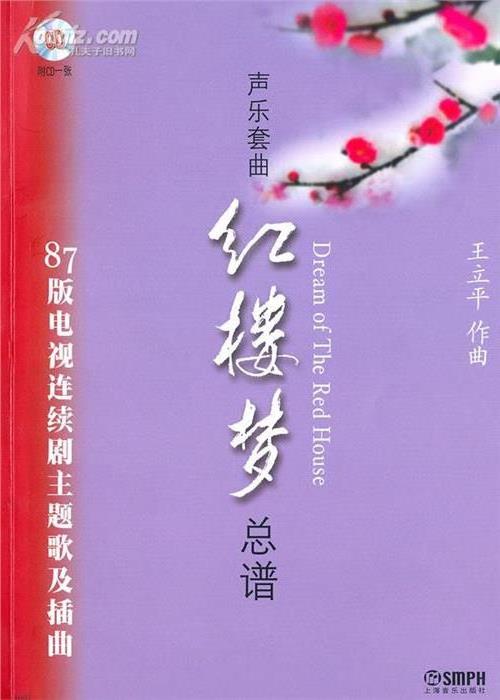俞平萧马 《红楼梦》是命中“萧何” 俞平伯成败皆于此
俞平伯(1900-1990),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学者。名铭衡,字平伯。原籍浙江德清县,生于苏州,系俞樾之曾孙。1919年12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上海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执教。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研究员。
在诗词、曲赋、戏曲、小说等诸多方面有丰厚论著。尤其是作为享誉中外的红学泰斗,其《〈红楼梦〉辨》(后修订为《〈红楼梦〉研究》)和《〈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等红学论著,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另著有 《唐宋词选释》、《论诗词曲杂著》,新诗集《冬夜》、《西还》、《忆》等,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杂拌儿之二》、《古槐梦遇》、《燕郊集》等。
他出身名门,早年以新诗人、散文家享誉文坛。他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研中国古典文学,执教于著名学府,他在诗经研究和唐宋诗词研究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就,但最引人瞩目的是他的《红楼梦》研究,一生共发表红学著作近四十万言,为《红楼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是俞平伯。
天生就是一粒读书种子
我跟朋友说,去曲园吧,去看看俞平伯的祖屋。
我们经过了怡园,又经过了听枫园,还问了若干次路,走走停停。
站在俞樾的画像前面,我饶有兴味地端详着他那柄拐杖。
当年,八十一岁的俞曲园左手牵着曾孙僧宝,站在阶前合影的时候,右手里就握着它。我在想,还是幼童的僧宝,会不会也有我一样的好奇心,想去摸一摸、耍一耍这老太爷须臾不离手的宝贝呢!
僧宝的大名就叫俞平伯。
对于这个一脉单传的重孙,俞曲园在含饴弄孙之外,当然是有着另外的期待的。当时曲园里的情形,俞平伯在多年以后想起,写下这样的句子:“九秩衰翁灯影坐,口摹苫帖教重孙。 ”
曲园大大小小的匾额上,每一个题字者的声名都如雷贯耳。曾国藩、李鸿章、顾廷龙……当年,才华横溢的俞樾因为一句“花落春仍在”得到曾国藩的垂青,他点了俞樾为部试的第一名。后来俞樾却遭到弹劾而断送了仕途,成为落难才子。他于是接受同年李鸿章的邀请,来到苏州担任紫阳书院的讲习。踏上苏州土地的那一刻,俞樾是风尘仆仆的。这风尘仆仆将会开启苏州一段流光溢彩的文化史,这让苏州有点始料未及。
“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这两句话,桃李天下、著作等身的俞曲园受得起。“三千士”里有陆润庠、章太炎和吴昌硕,也有俞平伯的父亲——探花郎俞陛云,自然也要包括一脉单传的俞平伯。
芥子纳须弥,曲园从建成的一刻起,就开始了一段绵长的父传子,子传孙的接力;五亩地不算大,却承载了著书立说、诗书传家的精义,这里有种宿命在。
因此,俞平伯天生就是要做一粒读书种子的。可是小孩子到底玩性大呀,曲园的童年时光想必就夹杂着些不自在。
直到六岁的表姐许宝驯来到了苏州。接下来的日子才是俞平伯的天真童年:“花好闲园‘苏州府署园名’胜曲园,青梅竹马嬉游在”(俞平伯《重圆花烛歌》)。许宝驯就是以后和他嬿婉同心六十年的结发人,这是后话了。
别有一种独特的风格
适逢一个王纲解纽的时代,俞平伯作为曲园的正宗嫡传,有了选择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青年俞平伯有两次留洋的经历。第一次是跟许宝驯婚后三年,自费赴英。他1920年1月从上海乘船出发,到了4月初,他突然匆匆归来。关于俞平伯留洋半途而废的原因,有着种种猜测。一说是因为俞平伯穿不惯洋服、皮鞋,另一说是因为他抛舍不开妻子。外孙韦柰曾经向外祖母求证过,她笑着驳斥道,“那是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哪里会是为我呢? ”
第二次的留洋机会是岳父替他争取得来的,由浙江省教育厅以视学名义派往美国考察教育。这次留美近四个多月光景,俞平伯归来时西装革履,手持stick(文明棍),一副翩翩洋少的气派。
对于这次留洋,想要探底里将当日的真相看破有点难。叶兆言说,俞平伯是他见过的老人中,最有少爷脾气的一位。而少爷脾气说穿了就是孩子气。用这点来解释,就说得通了。俞平伯的两次留洋并未取得洋文凭,除了经济问题,与他的脾气性格不无关系。
但有无洋文凭并不削弱他参与到新诗与白话文实践中去的热情。他的第一首新诗里,有这样的句子:双鹅拍拍水中游,众人缓缓桥上走,都道春来了,真是好气候。
这与他喜爱的父亲的两句诗“只缘曾系乌篷艇,野水无情亦耐看”,中间只是隔了几十年的光阴,两代人的笔墨也上演了一出翻天覆地的好戏。
说起来,俞平伯身上有着诸多新旧的缠夹。他有着过硬的旧学功底,在现代白话散文中也能自成一家;既师从旧派人物黄侃,又是新文化领袖胡适和周作人的学生。周作人说他,别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这风格是属于中国文学的——那样的旧又那样的新。
仅是读过《红楼梦》而已
不管他本人作何感想,俞平伯的确是因为《红楼梦》而获得了更多世俗的关注。《红楼梦》就是俞平伯命中的“萧何”,成败皆在于此。可他自己从来不肯承认自己是“红学家”,说:“我仅是读过《红楼梦》而已,且当年提及‘红学’,只是一种笑谈,哪想后来竟认真起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俞平伯在《〈红楼梦〉辨》的基础上,加了两篇新文章,出版了《〈红楼梦〉研究》。 1954年因此而遭受了大批判,这让俞平伯夫妇一度很慌很紧张。批判归批判,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并没有止步。 1958年他出版了和王惜时共同校注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之后又写了《甲戍本〈红楼梦〉序》。 1963年,是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他那篇著名的《关于十二钗的描写》就发表在《文学评论》杂志上。
“文革”中,红卫兵抄家,关于《红楼梦》的所有资料、笔记,被一扫而空。“老实讲,我还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一直想搞的《〈红楼梦〉一百问》,还有过去所谈的也有许多不妥之处,应予纠正。但手头没有资料了,还搞什么! ”俞平伯有点万事皆休的愤慨。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他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庆祝会。俞平伯的发言总题是“旧时月色”。对于《红楼梦》研究,他诚恳地提出了三点意见,能否引起当时红学界的重视,这对他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此时,夫人许宝驯已病故,没能看到这桩纠结多年的公案尘埃落定。
1986年,俞平伯出访香港演说《红楼梦》。在老人心中,还存留着二十年代途经香港赴英留学的记忆。再次去,他说,要配副眼镜,好好睇下香港。“睇”完之后,他随手写下了老杜的诗句: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
故园一直在心里晃荡着
俗语说百炼成钢,观其一生,俞平伯是在一波波的惊涛骇浪里练就了宠辱不惊的定力,什么样的日子都散淡地去应对。
1969年,年届七旬的俞氏夫妇赴河南干校。住在农民家的一间简陋茅屋里,写就了许多清新安逸的好诗句:
茅檐极低小,一载住农家。侧影西塘水,贪看日易斜。(《无题》)
1976年唐山大地震震撼了北京,天天闹避震。俞氏夫妇却坚守在二层楼的寓所里,岿然不动。只有两个晚上,在“紧急通知”之下,他们住在了防震棚里。事后俞平伯在日记里写:……卧见碧天,巧云往来,空气清新,只稍凉减寐耳。点蚊香,一夕恬然无忧。
活到这份里,人生已露近情随性的端倪。不是说,顺乎天性,就是身在天堂吗,俞平伯是实践得比较彻底的一位。无论冬夏,总是打着赤脚,几套中式布衣裤换着穿,衣服上,有烟灰烧出来的洞洞星罗棋布。他嗜烟,但不重牌子,能冒烟的就行;嗜肉,不喜蔬菜;想吃就吃,困了倒头就睡……宛如大水养鱼,自然率性。终年九十,也算是高寿了。
俞平伯不善言辞,怕与人周旋,看似怪癖,内里却有深情。夫人许宝驯病逝,丧事办得极简单。俞平伯表现得异常冷静,只是坚持将骨灰安放在自己的卧室内。常常在夜里一个人自言自语,甚至是狂吼。他把自己的抑郁心酸都写在了日记里:高龄久病,事在定中。一旦撒手,变出意外。余惊慌失措,欲哭无泪,形同木立。次晨火葬,一切皆空。六十四年夫妻,付之南柯一梦。
如今,他与夫人合葬于北京西山脚下,碑文是他生前亲笔拟好的:德清俞平伯杭州许宝驯合葬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