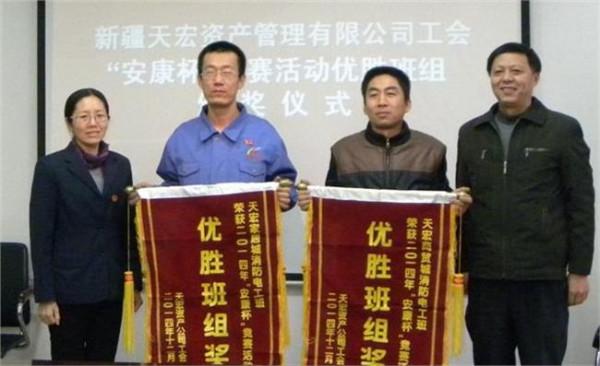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消息——唐师曾访谈录
董岩:您曾说用妄想来治疗自己的抑郁症。
唐师曾:早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读书时,我就喜欢上了记者这个行当。未名湖畔有著名记者斯诺的墓,每次下课途经那里,我都会献上一花一草,以示怀念。那时我对参加世界革命的里德、斯诺、卡帕顶礼膜拜。斯诺不仅追赶热点新闻,而且热衷一切有价值的进步事业,这更令爱管闲事的我向往。
为鼓励后人热爱生活尊敬历史,斯诺还立下遗言把自己遗骨埋在北大,持续充任民主科学的种子。由此我才知道记者不仅可以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可以留下一种精神。
董岩:同行曾评价说:“唐老鸭”是写的比拍的好,说的比写的好,干的比说的好。在成为“唐老鸭”之前,您过着怎么的生活?
1991年1月15日,结合国安理睬给伊拉克最后期限。为了能留在巴格达,“唐老鸭”居然谢绝办理出境手续,以至1月14日中国使馆郑大使率最后一批中国职员撤退时,他差点在巴格达机场被扣下。当伊拉克袭击了以色列,所有的人都在往回撤的时候,在安曼待命的“唐老鸭”越级上书北京总社,强烈要求去以色列。于是,他成为新华社用“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第一人。
董岩:你以为本人的胜利重要来自什么呢?
唐师曾:穆青说,摄影是新华社的翅膀。是他破格引进了我。1986年进入新华社,到海湾战争前,我一直负责报道北京地域的新闻。做新华社记者,没有报纸,也没有电台,没有电视,他的新闻作品被别人用,必须第一个到场。
第一个到场,必须要有硬件和软件,硬件就是一些机器。我1986年、1987年有一个BP机。天天上报的稿件特别多,我买呼机的时候,店主说为什么要选一个好号,我说看今天的《北京日报》《国民日报》《光亮日报》,我就是这位作者,所以我必需要一个好号,以便让大家记住我,以便和我接洽。
所以126给了我一个5566。1987年我开始用挪动电话,是爱立信的,个头很大,谈话的时候必须按着,听话的时候松开。当时我就能获取别人不能取得的信息。这是因为我有一定技术设备的上风。
阔别了战场和硝烟的“唐老鸭”,好像安静了许多。但懂得他的人都知道,老鸭是永远停不下来的。他开始了一个人的远行。他曾这样形容自己的生活——“在C-130‘鼎力神’肚子里,边旅行边敲字。人在天上飞,手段上就是时间,脖子上就是空间,怀里抱着的就是自己的生命。”
唐师曾:我坚信这一点。我认为劳动分为几种:牛马劳动、体能劳动、技能劳动和德能劳动。要靠智慧赡养自己。因为体能注定会损失,技能也会落伍,但智慧却能提高。我不敢说我是一个灯塔去领导别人,只能说我是个萤火虫,至少可以发一点点光。
唐师曾:不懊悔,我认为值。我16年没提升,由于有病拿不到全额工资,但一点儿不后悔。性命一闪而过,能从事自己爱好的职业,亲历了那么多大事件,很荣幸。况且记者这个职业还培育了许多技巧:开车、语言、写作、摄影……有这么多播种,你还说亏吗?
董岩:在那里,您晋见过卡扎菲,曾徜徉黑云压城的伊拉克街头,闯过以军封闭进入解严的加沙,也曾跟随穆巴拉克横穿西奈……中东成全了您的冒险精神和叛逆精神。记者是一个危险的职业。在去中东之前,您就曾两次和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去秦岭拍摄野生大熊猫,一脚踏空,从山腰上滚下来;一次是赴山西雁北,路上汽油渗漏,差点车毁人亡。在中东采访时,您惧怕流弹吗?
唐师曾:这个评估太轻了。记者只是其一,他仍是思维家、文学家、翻译家,是翻译《尤利西斯》的人。
唐师曾:摄影记者不该给被摄体描眉画眼。心中的“至美”首先是自然,天然第一。摄影记者应该发现“至美”,再挑选适当的时间、空间记录“至美”。是“记录”而不是夸张一点的“宣扬”、“工程”。摄影记者应该切中时弊地发现问题,倡议“被摄者”适应自然规律,同时参照时下的审美价值。任何违背做作的努力都本钱昂扬,难以长久。从狭义的角度说,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记者,《史记》也是“语像”。
唐师曾,1961年生于北京,江苏无锡人。本科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核心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现任新华社主任记者,装甲兵学院研讨员,美国柯达联网职业摄影师。在完成新华社图片文字发稿义务之余,在《世界博览》等报刊发表文章数十万字。屡次冒生命危险亲临一线采访,为新华社拍摄了上万张名贵照片。著有《重返巴格达》《我的诺曼底》《一个人的远行》等。
唐师曾:车是厂家借给我的切诺基,油钱都是自己出的,胶卷是柯达的。新华社不许拉资助,另外我也不擅长拉援助。这次行程耗时4个月,创造了新的纪录——第一个从中国走陆路到印度的亚洲人,但这段旅程也吃了不少苦头。在珠峰邻近,睡在海拔5000米的小土屋,棉被凉得跟冰一样,我猜忌自己是不是睡死过去。到印度以后没钱了,只好睡在车里,凌晨醒来发现好几个流落汉都睡在车下面。去印度的路上,动摇了我“一个人远行”的信念。
董岩:您对现在的生活满足吗?
唐师曾:知名要趁早。那时年轻,精力茂盛。世界上著名的摄影记者都是二三十岁著名的。新闻是我生命的全部,我始终没把记者当成上班的事,而是当成生命的全部,当成生命的状态。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
唐师曾:我们那会儿至少要控制多少项基础功。使劲练字,进步速记程度;照相机是手动的,疾速抓取,也是一门大手艺。过去曝光,靠教训、光照度、亮度来掌握,现在不需要了。过去相机是模仿的,现在是数字的,基本不须要胶片。
观点完整变了。1991年海湾战役,我在中东首次接触IBM。美国佬笑话阿拉伯人个个都是“IBM”,Inshala(真主保佑),Bukra(来日再说),Mafeishi(什么都不),或maleshi(什么无所谓)。1997年,我开端应用电脑写字,此前始终用钢杆的“派克45”,特别硬朗。图穷之际,还能够当鱼肠剑刺秦。
唐师曾:不可能。因为我现在拍的电影均是一些富有挑衅性甚至是很危险的题材,置身于这样的工作环境,我的豪情和发明愿望不仅不会消减,反而会得到强化。但我确切等待着像罗伯特?卡帕那样,在临死的一瞬间还能最后一次按下快门。而您所说的“那一天”估量也将与我毕生无缘——您说,这岂非不是一件很幸福、很惬意的事吗?(作者系专栏作家、新闻学博士、中央电视台社教中央策划)
唐师曾:我吃完药,特别乖,然而没有思想和激情了。我一直认为我没病,我认为一个人能给自己看病的是自己。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医生。因为生理和心理的界定很含混。
董岩:这一点您做到了,而且很杰出。我们知道,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您认为新闻摄影的原则是什么呢?
编纂:知秋
唐师曾:1994年我参加了555世界汽车拉力赛。1995年参加中国迷信探险协会“神农架寻找野人”。1996年单独驾车围绕美国。1997年因受辐射患“再生阻碍性贫血”,住院做骨穿等医治。1998年在病床上实现《我钻进了金字塔》,张中行作序。
1999年出访海湾,谋划《从金字塔到万里长城》吉普车采访活动。2000年海湾战斗10周年,自费前往伊拉克,出版《重返巴格达》,季羡林作序。2000年12月到2001年2月参加“首批人文学者南极考核”。2001年,入选“全国十大新锐青年”。2001年11月至12月,加入马来半岛吉普车穿梭热带雨林运动……
董岩:您的头衔很多,光环也很多,该怎么称谓您?
董岩:中东是一块神秘、庞杂的土地,也是一个剑拔弩张的炸药桶。
董岩:在北京新闻界,人称您“唐老鸭”,这个外号有什么来历?
唐师曾:那是我生命中最华彩的一段时间,当时我还不到30岁。我三十而立的成人大PARTY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高楼顶层防空兵器丛中举办的。那天有好几枚“飞毛腿”划过夜空向我鸣炮庆祝,我活这么大从没看过那么大的焰火……它带给我的高兴,弘远于苦楚。
历史为他供给了一个全新的舞台。半年多的时间里,“唐老鸭”辗转于中东诸国,向新华社传回百余张战舆图片,其中大部门刊登在海内外各大报刊上。
董岩:经历过生生死死、采访过世界风云人物,在相称长的一段时间里,您的名字和世界关注的热门地区、新闻事件、焦点人物牢牢联系在一起……您的人生,够得上传奇了。
我是看着他的《我钻进了金字塔》成长的。战争、历险、风云人物、沙漠景色以及豪杰一样顶天立地的“唐老鸭”,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战地记者、陆军上校、作家、探险家……这些字眼曾不止一次在我的脑海里翻腾。但它们仿佛和面前的这个人绝不沾边。传说中的“唐老鸭”,毕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带着这样的疑难,开始了和他的对话。
唐师曾:我感到最称职的、最看重的还是记者,别的所得都属于记者的从属产品。固然我说过自己是个“低档次”的记者,自由性强、纪律性差,但我有一个优良记者所应具备的独立工作、独立思考的品德,这品质出于本性,更多的是出于后天的历练。
岁月能给人带来的馈赠,这馈赠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有价值的,并且如何失掉这些价值。总结起来说,当记者,我喜欢,我善于,我以此为生。我原创,我自主,我不可替换。我特别喜欢《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有这么多收成,你说还亏吗
董岩:2003年,您只身驾驶吉普车从北京动身,开始重走玄奘取经路。
唐师曾:考察一个新闻摄影记者优劣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在最合适的时间达到最适合的地点。
唐师曾:我拍的都是新闻照片,而且大多是不可反复的,是现场新闻事件照片。因为我是通信社摄影记者,为新闻而生。我的照片都有两个意思,第一是新闻价值;第二是文献价值。所以我的照片可以卖两次,第一次是新闻照片,第二次是文献照片。
所有的照片都有文献价值,但我所说的文献价值除了它名义的文献价值之外还有深层的文明内涵。我个人认为我的每一张照片都很可贵,每一张底片消耗的也不仅是金钱,还有时光、精神、机遇、还有生命……海湾战争……都是花多少钱都不可能重复的。
有人批驳我的照片是虚的,这很有情理,我应当检查。首先,有关当局严禁拍照,人家不让拍,我哆里发抖照一张扭头就跑,但究竟有一虚影。其次是我的摄影技巧不外硬,还有我的心理素质差,在危险场所心跳过速。
第三就是我的视力有问题,右眼在大学踢球受过伤,而且双眼都是高度近视。我的照片不可能和那些漂亮照片比拟,所以我从不参加任何摄影竞赛,因为我晓得那都是俏丽的大比赛,我不可能有戏。我也不习惯。
上个世纪的90年代,是唐师曾事业的巅峰。1991年2月8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唐师曾的一张照片,这在活着的新华社记者中是少有的。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更让亿万观众知道了在世界关注的中东,有一个不怕死的中国记者,他是世界的眼睛。新华社对这个老是风风火火、以自己精彩的工作为“新华”博得极大名誉的年青人同样多一分偏爱和关照。郭超人社长亲身同意为他配置了一部移动电话。在新华社的历史上,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唐师曾:有两点比较重要,一个是知识。学校教的知识,适用的局部不够,我们可以回忆,尤其上大学的时候,好多课,考完试就没有用了。我老认为,教导是这样的,中学有一门课必须学好,就是中文。大学最重要的一门课就是英语,教你学世界通行的语言,最好是英语。
这两点,我中学、大学都学得不好,当时不明确,学了很多没有用的课。但也选了一些当时别人认为没有用的课,选了我作为战地记者无比有用的课,就是军事知识。我读了些十分经典的军事书籍,不是报纸、杂志抄了很多遍、已经被稀释的知识。
此外,我当了好几年的记者,交了不拘一格的朋友,积累了社会经验。我发现经验比知识还重要,这种经验是锤炼之后深刻骨髓的,不是简单的培训就能得来的。
唐师曾:他是一个精力独立的人。我一直认为萧乾是天底下为数未几的勇敢男人。战争是表示勇敢、承当义务的最佳机会。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欧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他亲历了两次轰炸伦敦,随美军挺进莱茵河,是攻克柏林后首批进城采访的战地记者。我这里讲的勇敢存在两层含意:一是明知有危险而临危不惧;二是心坎自在不受金钱权利等物欲的驱使。
唐师曾:这要感激两点:一是上对了北大,二是找对了工作。北大不仅给了我人文科学常识,更主要的是培养了一种自由、科学的精神。再有就是新华社的实际和积聚,如果没有那5年跑新闻的练习,就是后来去了中东也是白去。另外,我还赶上了改造开放的好时候,遇上了一个巨大的时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才促成了一个所谓成功的“唐老鸭”。
唐师曾:没有那段阅历,就没有现在的我。1991年海湾战争,我第一次去中东。在耶路撒冷,一位以色列姑娘带我散步神的土地。她告知我说,你正站在大卫·本、古里安、摩西·达扬……许过愿的哭墙下,我闻言手足无措。
她说,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要汇聚这里,在神的土地上许诺,再把写上心愿的纸条塞进哭墙的墙缝,神一定兑现。我诚惶诚恐,问她上帝使用什么语言,她说古代是希伯来语,后来是伊地语,现在确定是英语。我本能地写了“为共产主义而斗争!
”她看后笑了,说,这是一个党派的政治目标,不属许愿,“你必须写自己个人的宿愿”。在犹太姑娘的启示下,我写了“当好记者,娶好姑娘,生好儿子。Tobeagoodphotojournalist, tomarrycharminggirls, tomakesupermen!”因为语法太差,后两个都写成了复数。
董岩:一个记者能拍的新闻,能出的风头,能得到的风光,在您那里几乎都完成了。
董岩:您曾说,只要您是优秀的,想干什么都能干成。
董岩:在那里,您采访了许多世界风波人物。
董岩:据我所知,当年萧乾学新闻也是受了斯诺的影响。
董岩:您曾先后五次去中东采访。您认为,新闻记者战地采访时应具备哪些素养?
记者:会有这样一天:您开始腻烦摄影,并终极扔掉手中的相机吗?
董岩:据说您已经出了8本书了。
唐师曾:以前生机自己的书能畅销,现在不那么急躁了,更重视品质,不求多,但必定要有品位。在《一个人的远行》里,发现了语像文本方法。下一本书《我说》就要出版了。愿望铲平老鸭喉舌,共建民众语像。
在“唐老鸭”的第六本书《我的诺曼底》里,封面上,他戴着墨镜,斜挎一个相机,在有名的历史留念地表情肃然地站破着;封底是一段“唐老鸭”的规语:“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涯,中华就是——旁边的精髓!你我就是。灰尘掉入眼便成眼屎,赏给蚌壳就变成珍珠。世界覆灭了每个人,就在被灭绝的处所,却呈现了强人。”
2003年11月寒冬到来之前,唐师曾和大吉普“和平鸭号”蹒跚翻过喜马拉雅山回到中国。“唐僧取经”还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四位保驾,“唐师曾取经”全靠大吉普和四个米其林轮胎。
唐师曾:应该学我做人的立场,而不应学我的详细职业。比如我当真,我对每一件工作都尽量认真。不屈服于好处。你看我去做一个电视节目,似乎随意说说,但我在幕后付出了几倍的劳动。
唐师曾:怕。在新华社摄影部我是第一个买钢盔的。以后去的记者都是到我去买钢盔的地方买,因为我对军品店比他们都熟。在那里,我与死神约会频频,仅数次撞车的经历就让我魂飞魄散。第一次是在耶路撒冷,我租了一辆出租车赶往伊拉克“飞毛腿”导弹爆炸现场,途中与一辆大卡车相撞,出租车右门被撞瘪。
然后就是塞浦路斯的那次大难不死。当时我乘坐一辆据说是世界上最抗撞的沃尔沃轿车,在一拐弯处,时速95英里的沃尔沃猛地撞在一辆红色福特的屁股上。
当时我正瞌睡,忽悠一下就从后座上飞了起来,撞断了前座的靠垫。还有一次是乘坐的大奔跑撞向一群山羊,弄得大奔抛锚,羊尸一片……有一段时间,我只要一坐进汽车就六神无主,患了“乘车胆怯症”。
在友人眼里,身高一米八三的“唐老鸭”实在是一个特殊抵触的联合体——思惟深入,有时却像长不大的孩子;古貌古心,有时却又不近人情。我问有什么欲望,他老诚实实地答复说,老鸭飞不动了,只能当陈设了。盼望健康,老了有饭吃。
丘吉尔说:“咱们都是虫,可我是只萤火虫!”丽人迟暮、好汉末路,本是天然法则。只管老鸭还像从前一样仍旧有一颗大胆的心和执著的信心,但我仍难掩失踪。看着他高大的身影,突然有些莫名的悲伤跟难过。想起了多年前老鸭与记者的这样一段对话——
唐师曾: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两个点,时间和空间。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腕表,空间就是相机,而后就是活在中间的我,我开着车,戴着表,拿着相机照相,然后把它们综合在一起放到我的IBM里,整合了我所遇见的时空。加工成一本书,一捆捆放在那儿就成了过去,我再开始新的一切。人生太短,来不迭干小事。
唐师曾:我一个人狼狈万状重蹈唐僧覆辙,回到北京才发明我所酷爱的工作、家庭同时崩盘……老唐的近视眼装下过全部世界,怎么就容不了这半粒沙子?海湾战争落下的“再生障碍性贫血”加上“重度抑郁”使我不修边幅,就像火山暴发失去家园的大猩猩。
精神抑郁让我情感剧烈,任幼强编辑不得不把我送进北大医院。当时中心电视台小崔和海啸正在做片子传奇《隧道战》,让我说一段词。发现我状况错误,进而担忧我这个海湾战争的漏网之鱼迫害社会,连夜把我押往边境云南。
昆明云大病院一直沿用德国的综合疗法,强劲的洋药之后还有阴柔的心理治疗。受过德国人栽培的徐医生是小崔挚友,他说大凡生活紧张、工作玩命又知己犹存的好人,很容易构成各种疾病。陪我住院的小崔也说抑郁症患者都是天才,像打坏自己脑壳的海明威和川端康成……如果小崔没骗我,我这个“重度抑郁”就一定是“分量级蠢才”。
董岩:您黄金时期的豪举令人瞠目——1990年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持续探险4个月。1990年径自潜入伊拉克,最后撤离巴格达,是第一个使用以色列电头发稿的中国记者。辗转交战双方,出版《我从战场归来》,萧乾作序。1991年到1993年任新华社驻中东记者,采访加利、卡扎菲、穆巴拉克、阿拉法特、沙米尔、拉宾、佩雷斯、巴拉克、沙龙、曼德拉等。
唐师曾:以前是记者,现在是半个作家,有独立、自由思想的作家。
唐师曾:每说到我的大吉普我都忍不注泪珠潸然,她是我在中东唯一起床共枕、历经生死的伴侣,我叫她长腿沙漠跳鼠。买她的头一个月,我就开了1.3万公里,从开罗跨过苏伊士运河、横穿西奈、穿越加沙地带一直开到耶路撒冷。
直到以色列南方军区动用M113坦克车和AH—60“黑鹰”直升机才在阿什克隆终止我和我“爱妻”的蜜月旅行,我和我的长腿跳鼠的蜜月之旅由此上了法新社、路透社、《约旦时报》《以色列新闻报》1992年6月22日的头条。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教养表现为可以享受最好的、蒙受最差的。吉普,就是拥有这种贵族气质的生命。我已经无奈回想多少次我和我的大吉普陷在沙漠中,被可怕分子围追切断、被士兵扣留、被难民包抄……为了自我维护,我的前风挡上贴了我与卡扎菲、阿拉法特、拉宾、曼德拉、加利的合影,我说的最纯熟的一句阿语是:“安拉最伟大”。记者的魅力在于勇敢、老实、不装孙子
董岩:在良多人眼里,您也是一个英勇的战地记者。
董岩:在新闻院校,有不少学生盼望能像您一样成绩一番事业,对他们您有什么忠告呢?
唐师曾:人的运气就像撒马拉转塔,有着宿命的滋味。我对生命的懂得也是这样,每个人的生逝世都是命中注定的。按医生的说明,我活着已经是奇观了,可我还要不知疲惫地工作。尽管医生不停地给我吃药,逼迫我睡觉,可我决不会为安定而就义工作。
我是为新闻而生的,为此永远朝着自己心中的目的尽力,中国话叫“狐死首丘”。活一天就要做一天新闻。我们都是虫,可我是只萤火虫男人以世界为家,女人以家为世界。望着二伯留下的农田,我想,官再大也有退的一天,钱再多也有死的一日。幸福是很难用时间是非划分的,一小时真正的幸福可能赛过乏味无聊的100年。——唐师曾
唐师曾:我不喜欢这个称说,这是记者应该做的。其实危险性最大的是战争摄影师。美国人马修?布雷迪,是人类第一个全面报道战争过程的摄影记者。我最信服的人是卡帕。他在匈牙利诞生,德国柏林上大学,法国巴黎营生,在日本上班,在越南被炸死,葬在纽约……卡帕是真正的世界国民,几乎经历了那个时期的所有战争,比如西班牙内战、诺曼底登陆。
他是靠诺曼底登陆的照片有名的,别人站在船上拍,卡帕跳下去自己拍。他的镜头都是简单的、平视的,不是仰望或者俯视的,这一辈子他只给自己打工。
他喜欢饮酒、美食,环游了世界,还会写小说,他的人生是真正的传奇。卡帕有一句名言——如果照片拍得不够好,阐明你离得不够近。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只有相机能力真实地记录历史
唐师曾:过去在乱哄哄的采访现场,我的镜头常被人挡住,经常急赤白脸地冲人乱叫嚷,状似被人掐住了颈项的鸭子,直到人家让出一条通道为止。时间长了,就得了这么个绰号。
董岩:听人说,“唐老鸭”是被穆青从大巷上拣回来的。
董岩:但当初科技发展了,竞争前提和环境产生了变更。
唐师曾:跟世界靠近了。我们是远东的人。中东,那么盘根错节,那么稀释历史的土地。在那里工作,给了我濒临世界的可能。我在北大学的是国际政治,教学曾说,我们应该是极其敏感的人,一根针掉下来,都能感触到。别人震动一下,我们应该震撼一百下。当然记者也同样。在中东,要造就超越别人许多的敏感。
唐师曾:可能有影响。那本书是广西师大编的,好几十个作者,他们写的眼中的我,好多人跟我很熟,有的是来报社采访我的记者,应该是准确的。另外说我的问题,我自己承认,我一直是问题比拟多,比方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能考上北大,却入不了团,我们班上所有的人都是团员,我是独一的例外。
因为我一直是一个问题比较多的问题青年。此外一系列冒险包含战争的影响,性情不敢说,对精神有影响。一方面是傲慢,畸形思维的人,毫不会终日大放厥词,老爱要么A,要么B的抉择,而且把我的人生变成了A、B的取舍,把自己变成时常逾越不该跨的竹篱的黑马。
通过战争,我清楚一个道理,人的毕生,假如依照70岁算,70×365天,即是25550天。前二十年上学,后二十年退休,中间二十年是找工作,入党入团寻求提高、买屋子、追女孩、供养父母、滋生后辈……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所以我把时间看得很可贵,督促自己常常干一些是有趣而事后值得回味的事。我方才说的踊跃方面。长年冒险生活给我的生活造成的消极方面是多疑、暴躁,喜欢打架,喜欢砸货色,家里能砸东西的全砸了一遍。
董岩:朋友曾不止一次地调侃说,吉普、相机才是“唐老鸭”的真正伴侣。
董岩:采访时,您曾把口袋里所有的钱和食物送给需要辅助的人,也曾把身上背的生命之水全体送给了赞助过您的骆驼队。在很多人眼里,“唐老鸭”是真挚、热情、仁慈的。
董岩:为了新闻采访,先是摔伤了腿,造成肌肉萎缩,后来又因辐射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落下了一身病,简直搭上了命。想想自己,亏不亏?
董岩:最大的收获和感悟是什么?
董岩:我知道,在新华社您曾坚持均匀每天发表一张新闻照片达数年之久。但同时也为这份光彩与梦想付出了繁重的代价。
董岩:有些东西不会有大的改观,好比权衡摄影记者的尺度。
唐师曾:因为长期适度操劳,连续挣扎,老有一种达观情感,很缓和,很火暴,轻易往坏处想,同时也导致了身材的虚弱。我不到30岁就双手发抖,拍出的照片越来越虚。当年中东总分社的老引导周泽新看到我手臂颤抖,曾经问我是不是有帕金森氏症……可是当时我手轻脚健,除了否认自己1998年在秦岭追熊猫右踝骨韧带撕裂,一条腿粗一条腿细之外,壮实得胜过金刚。
后来生病了,不能像以前那样冲锋、工作了,成了别人的累赘。谁乐意40多岁的时候离婚呢?现在反过来想,把工作当成生活,当玉成部,迟早会闹弊病的。我不到30岁就闻名了,是好事,也不是好事。
唐师曾:我认为,世界上的人分成四类人,一类是爷爷级的,比如丘吉尔、沙龙,是制订规则的;第二类是爸爸辈的,巴顿、艾森豪威尔,他们履行规则;第三类是儿子辈的,他们遵照规矩,北京大学总裁培训;第四类是孙子辈的,他们损坏规则。在中东,我见识到了各式各样的政治家。
唐师曾:记者不是作家,而是一个行者。记者要性分外露,态度赫然,有觉醒,善于沟通,有襟怀,是一个行走的人。当然离不开车。好多年前,在秦岭南坡的盘山路上,我与一位正在北大念博士的女孩跋涉而行。这丫头突发奇想地问:“有朝一日发洋财,你盘算买什么?”我不假考虑地回答:“买辆吉普!”从那天起,领有一辆吉普的幻想就一直折磨着我。即使到现在,我还在固执地保持,只有吉普才是真正的汽车。
唐师曾:我认为摄影自身有两个特点,一是真实性,二是霎时性,这两件事都必需依附时间空间。摄影首先应认真实,应该处在一个实在的位置。无意中诱骗过读者的摄影记者应该懊悔;恶意诈骗过读者的摄影记者应该引咎辞职;应用工作之便歹意制作假照片,并参加摄影大赛牟利的暴徒应该判刑。
卡帕说,只有相机才干真实地记载历史。这句话一直是我的座右铭。纪实摄影不请求拍得如何美丽,而应具备批评事实主义思想。把主流社会不在意的真实展现出来,提供应不同部位、不同阶层的读者领悟,增进社会发展先进。
董岩:二战时代的战地记者曾把吉普车说得无所不能:“它像狗一样虔诚、像骡子一样强健、像羚羊一样机警。”
董岩:有人曾批评您拍的照片有的是虚的,您怎么看自己的作品?
董岩:作为记者、作家、探险家,您如何评价自己?
董岩:萧乾是中国第一个战地记者。
唐师曾:不满意。20年前我瘦高修长,一年四季穿简略的红衣服,即便3天不吃饭,只有睡上半个小时,骑上自行车依然行走如飞。而今我已是40多岁的老男人,即使捂得再严实仍会不停地感冒,‘走路抗风穿衣费布’,还没有放下碗筷就已鼾声如雷,成了别人的负担。
也因为健康的起因,不能像以前那样拼命工作了。容易疲劳,极端情绪化。一个人如果三十岁的时候没干自己喜欢的事,当前就很少有机会。所以三十岁以前,我是积极的、自动的,三十岁以后是被动的。有时喜欢一个人呆着,或者和朋友聊聊天,或者跟小孩子一起玩。
唐师曾:记者的魅力在于勇敢、诚实、不装孙子。好记者就要像卡帕那样,四海为家,有一颗博爱之心,胆子比我大,能如实、客观地记载那件事,不惜生命。被地雷炸翻还按一下快门,没有任何人能禁止。新闻是我生命的全部
董岩:那么这个准则又给摄影记者提出了哪些详细要求?
董岩:我记得有一本书叫《问题青年唐师曾》。大凡有造诣的人个别都很有个性,包括问题青年。是不是战争对您的性格发生了影响?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兼并科威特。当时“唐老鸭”正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探险。“中东要打仗了”。四年大学、四年教书的国际政治训练,让他立即做出这个断定。他全部的神经都跟着这个预见高兴起来。在鸭绒睡袋里,他打着手电起草给新华社领导的电报稿,恳求赴中东采访。“唐老鸭”最终获准。1990年12月22日,“唐老鸭”打扮齐整,他单枪匹马,带着300美元,飞往大战期近的伊拉克。
董岩:记得您曾写过一本书《我在美国当农民》。为什么想到去美国当农民?
阳光残暴的午后,在北京前海西街的一个院落里,膀大腰圆,被北京消息界戏称为“唐老鸭”的唐师曾正耐烦地和小侄子一起装置波音787的飞机模型。在采访他之前,我设想了很多可能的场景,但绝没有想到是这样温情的一幅画面。
唐师曾:对。当时斯诺是新闻系的传授,萧乾是英语系学生,自从与斯诺接触后,他便从英语系转到新闻系,由此开始了新闻生涯。他是斯诺亲手带出的中国门徒,是一个中西合璧土生洋长的世界级记者。在萧乾的影响下,我还没出校门就空想自由飞翔,好像越渺茫越合乎我流浪的心。
以后分到政法大学教书,却二心以为有鸿鹄将至。大概在1986年,我的共事不知从哪里弄到萧乾的地址,带了我找上门去。当时我诚惶诚恐,只记得萧乾养了乌龟之类的小动物。
尔后我连考几家报纸,最终进了新华社。鉴于萧乾写文章沦为右派的教训,我起誓永不写字,铁了心只当摄影记者。1987年我在新华社首创BP机、手提电话跑新闻的方式,几乎把持北京地区所有突发事件的报道,名声大噪。
《中国青年报》用半个版面先容我和我的“闪击”实践,得到我师萧乾的欢呼。1991年,我停止海湾战争采访回国,行前顺便到巴格达曼苏尔食品店买了一听巴格达咖啡,献给我师萧乾,以报知遇之恩。回到北京,头一件事就是跑到萧乾家展示我的战场心得。
唐师曾:我是被迫去,强迫回来的。我骨子里崇敬农夫,但当不了农夫,我认为那是特别高等的职业。在美国的农场里,我知道了当农民的利益。《我在美国当农民》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那是我成熟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