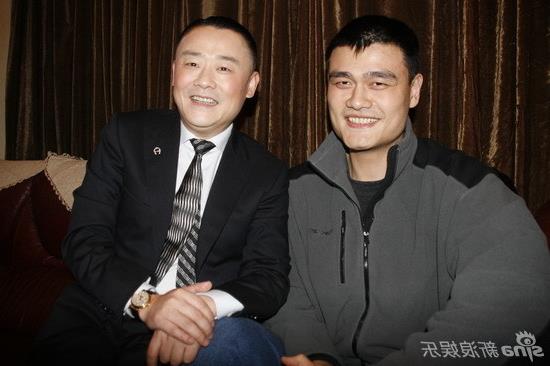叶公超老婆 叶公超:惜为官场误半生老憨新浪博客
教授生涯的终结 叶公超,原名崇智,字公超,后以字行,原籍广东番禺,1904年10月20日生于江西九江。其父叶道绳曾任九江知府。叶公超兄弟二人,早年丧母,父续弦后生叶崇德、叶崇?二女,后父去世,由其叔叶恭绰抚养公超兄弟和姊妹。
又因恭绰无子,视公超为子。 1917年,叶公超就读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缅因州贝兹大学和马萨诸塞州爱默思特大学。
后赴英国留学,毕业于剑桥大学文学系。在英国,叶公超与现代诗人艾略特亦师亦友,叶成为第一个向国内介绍艾略特的学者。1926年秋,叶公超归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师,主讲西洋文学,年仅二十二岁。
此时蒋梦麟是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蒋比叶大十八岁,是叶当然的前辈,叶终生都以先生称呼蒋梦麟。1927年春,叶转赴上海,出任暨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5月与胡适在上海相识,并与徐志摩等人创办新月书店,翌年创办《新月》月刊,徐志摩任主编,叶与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余上沅等人参与编务并发表作品。
1929年秋转赴北平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30年6月与贵州修文籍的燕京大学毕业生袁永熹女士结婚。
1936年,叶公超受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邀请,辞清华转入北大外文系任教授兼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叶随校先至长沙再转昆明,出任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
从1926年自海外学成归国任教,直至抗战迁往昆明,叶氏的教学与创作堪称一路顺风,并有了相当的声名,如果没有意外,当沿着此路继续走下去,直至在儒林中奠定相当的学术地位。但是,包括叶公超本人都没有想到,历史于不经意间改变了他的命运。
1940年6月18日,叶公超应叔父叶恭绰电召前往香港议事。这位叶恭绰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孙中山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等“三朝”高官大员。
对抚养自己长大视自己若亲子的叔父,叶公超得电,不敢怠慢,急向主持校务的梅贻琦请假赴港。叔侄见面,叶恭绰在密室向叶公超交代了一件事,他叮嘱叶公超,此次回沪,除处理财产纠纷,最重要的是保护毛公鼎,并谓:“已经有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想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有答应。
现在我把毛公鼎交付给你,日后不得变卖,不得典质,尤其不得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叶公超听罢,知其事关重大,且毛公鼎关乎民族大义,乃肃然起立,答应一一遵办。
毛公鼎是西周青铜器中的极品,重量近三十五公斤,铸有铭文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字,是传世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
清末,毛公鼎落入满洲正白旗人、金石学家、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之手。1916年前后,英国人、日本人都觊觎这一稀世珍宝,国人得知,纷纷阻止,端方子女亦竭尽全力保护。几经周折,毛公鼎身价陡增,尤其学术界都以国宝重器礼遇。
当时在北洋政府颜惠庆内阁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探知毛公鼎的事后,东凑西借,终于得手毛公鼎。自此,毛公鼎由叶恭绰收藏于天津,后移上海法租界劳里育路街乐园三号住宅。1931年,叶公超在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时,曾为毛公鼎精拓一纸,示于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孙海波、唐兰、董作宾等人观摩、研究。
叶公超悄无声息地潜回上海老家。此时,叶恭绰遗留上海的小妾正预谋出手毛公鼎,以获得财产离开叶家。
叶公超便与他的婶娘开始为叔父的财产过起招来。小妾一咬牙走出叶家深宅,径直进入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声称家中来了一位间谍,请大日本皇军快快前去抓获。日军听罢立即采取行动。
未久,一队大兵从汽车上跳将下来,端着大枪哇里哇啦叫着冲入法租界内乐园三号叶府。面对杀气腾腾的日军,不明底细的叶公超大惊,想阻止已无可能,日本宪兵在叶府搜出一些字画和两支自卫手枪,即以间谍罪将叶公超逮捕关入大牢。
当此之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上海租界还是“孤岛”,日本人尚不敢对租界内的一切人事太过分。但有一点出乎叶家预料,这位小妾到日本宪兵司令部密报叶公超是国民政府派来的间谍的同时,还出于报复之心把叶家秘藏的国之重器毛公鼎一同供出,只是小妾不知叶家七箱宝物具体的秘藏地点,这为叶公超咬牙顶住和毛公鼎最终未沦于敌手留下了空间。
日军将叶公超逮捕后,除了让其交代身份,更重要的是审询毛公鼎的秘藏地点,只要得到毛公鼎,无论是转手倒卖或献给日本国家,审讯者自有功名利禄可图。
在这一思路指引下,日军开始对叶公超展开轮番审讯。身陷囹圄的四十九天之中,叶先后七次受审讯,两次受鞭刑、水刑,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间谍,更不吐露毛公鼎秘藏地点。
为了尽快脱身,叶公超暗中传出一纸条,秘嘱家人请铸工假造一个毛公鼎式样的古铜器交出。时在上海的叶公超之兄叶崇勋除了找制假的文物贩子日夜打造铜器,还通过赵叔雅、陈公博、汪精卫等人与日本宪兵司令部交涉,花重金具结作保,被折磨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叶公超总算于10月下旬出狱。
叶公超出狱后,找来几位当地有名望的士绅与律师,对叔父的财产进行了分割。
而后,他亲自携带毛公鼎秘密乘船逃往香港。一路有惊无险,把手中的国之重器交给其叔,在港久等消息而不见的叶恭绰,此时悬着的心才落下。 当叶公超到港时,已是11月中旬,西南联大新学期早已开学,校方已指派柳无忌代理外文系主任。
经过上海之行和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劫难,叶公超感到身心俱疲,决定暂不回昆明,在香港休息一段时间,或到来年开学时再回昆明任教。
未久,叶氏在港岛遇到了老熟人董显光,二人一见如故,越聊越投机。董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力邀叶参加其主管的国际宣传处工作,叶因懒于回昆明,便答应下来。想不到这顺水推舟的一转身,结束了叶公超十四年的大学教授生涯。
大学教授叶公超 叶公超随蒋介石王朝浮海南渡,他留在大陆的足迹与事功渐被岁月的流沙风尘湮没,留在幸存者记忆中的也只是雪泥鸿爪。
加之叶公超弃学从政的偶然性与发迹、败落的突发性和神秘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叶氏成了宦海中谜一样的、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两栖类传奇物种。随着时间推移,即便他当年亲自执鞭教导过的弟子门生,对其印象也逐渐模糊,残存于脑际的只是几个残缺的碎片。
清华外文系1933届学生许振德说,他进清华时,“大一外文系英文课由叶公超先生讲授,课本为英女作家名小说《傲慢与偏见》。叶先生时方而立之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隆冬天寒则着棉袍二,进教室授课前,先脱其一。
先生授课讲述大意,从不逐字讲解,但课文中遇有生字之稀见而重要者,则反复阐述。当时先生未婚,只身住北院,某岁圣诞夕曾偕好友钱锺书往谒”。
燕京大学校花赵萝蕤,在清华外文研究所读研究生时曾为叶公超的学生,抗战前赵氏翻译完诗人艾略特的著名诗篇《荒原》后,出版前请叶公超作序,叶满口应诺并有些讨好地问:“要不要提你几句?”赵氏称自己当时很高傲,答:“那就不必了。
” 后来赵萝蕤在《我与艾略特》一文中说:“这篇精湛的序远远超出了我当时的水平,使译本生色许多,而当时的叶老师还是个才华出众的青年教授。
” 然而,优秀青年教授叶老师的出众才华与主动献上的殷勤,被一代校花熟视无睹或者装傻充愣地挥之而去。这导致了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催生了叶公超与赵萝蕤燕大时期高一班的学姊袁永熹的结合,而叶、袁婚姻的悲剧也因此而铸就。
当此之时,同样未婚的校花赵萝蕤,对未婚青年才子叶公超的殷勤视而不见,有自己的心理背景和理由。
许多年后,赵萝蕤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如果说叶老师在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十分自在的,也许是他那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决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也许他的非凡才华使他有时锋芒毕露,不过绝没有咄咄逼人‘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味道。
人们还是喜欢听他那天南地北的神聊。我这位老师的‘修养’是不凡的。” 正因为叶老师的“少爷”风度,令拘谨怕羞的赵萝蕤于不自在中缺少了一种信任感和更进一步的爱,从而没有随这位才华横溢的叶老师去研究当代外国文学,甚至只是“偶然到他那坐落在北院的家里”做了一回客,这一切令叶公超十分郁闷甚至有点恼怒。
于是,身穿长衫,神情显得有点落拓,眉宇间不时作忧郁哀愁状,周身散发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和古典文学气味的一代才子陈梦家,成了赵萝蕤芳心所属之人??人生姻缘也是如此诡秘、玄奥和不可思议。
后来赵萝蕤和陈梦家结婚时,叶公超送出了自己的礼物:一个可做灯具的朱红色大瓷瓶,一套带着硬壳的精装本哈代诗剧《统治者》,以及一个单人沙发床。
西南联大的学生对叶公超则如此描述:叶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绅士的派头,仿佛很神气,如果跟他接触多了,便会发现他是一个真诚、极有人情味儿的人,一个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
他并没有什么架子,相反跟年轻同事相处得挺好,乐于助人,而且十分重视人才,爱护人才。他英语语音纯正、动听,遣词造句幽默、秀逸,学生们一个个对叶先生的学问心悦诚服,无限景仰。
” 与亲历者的回忆有异的是,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 不少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锺书的言论,尽管后来杨绛撰文否认,但同为西南联大学生的许渊冲后来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
” 到底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认为:“作为学者,这话可能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翻,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
” 叶公超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 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 叶公超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
” 对于叶公超的懒,许渊冲以自己的身心感受“痛说革命家史”,谓:“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 1938年到1939年,杨振宁和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一年级,都上过叶公超的英文课。
在杨振宁的眼中,叶的表现相当糟糕,杨说:“联大绝对是一流的大学。我们两人后来的工作都要感谢联大给我们的教育。但叶教授的英文课却很糟糕。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捉弄我们。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东西,许恐怕也和我差不多。
”此为杨振宁为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作的一篇英文序言中的话,尽管事隔几十年,当年只有十六岁的杨振宁,对这位叶老师的拙劣表现和不近人情仍耿耿于怀,亦可见当年的叶公超对这位后来获得诺奖的学生心灵的伤害是多么深刻。
对于叶公超弃学从政、一头扎于宦海扬风扎猛的得失,他的学生王辛笛一度痛心疾首,认为如果他后半生专心教书治学,一定会在学问上做出一番业绩来。
而同为清华外文系叶氏门生的季羡林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叶公超并不适合教书治学,他还语中带刺谓:“我觉得,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 叶公超似乎没有真正的朋友。事实上,在叶氏一生所结交的朋友中,与他掏心窝子交流的恐怕连一个也找不出??蒋梦麟最多算半个。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也是其晚年悲剧的主要原因。
从政之路神秘终结 踏上官宦之路的叶公超,尽展风流,玩起计谋与策略来,比教学更得心应手。在国民党宣传部驻英办事处处长任上,他于新加坡、印度、重庆、英国、美国之间来回穿梭,工作成就颇得上司赞赏。
抗战胜利后,叶公超进入外交部出任参事,未久晋升为欧洲司司长、常务次长。1949年6月12日,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全面崩溃,叶公超“临危受命”,任代理“外交部部长”主持部务。
1949年10月1日,即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叶公超被国民党当局正式任命为“外交部部长”。自此,叶氏深陷宦海,随波逐流,直至晃荡到台湾孤岛终了一生。
叶公超之妹叶崇德回忆说,1949年3月的一天傍晚,崇德的母亲,也就是公超的后妈赵寿玉正在上海家中做晚饭,忽然叶公超轻轻推门进来,只见他“对老母摇摇手,并立即将厨房门关上,搀扶着老人走入客厅,正巧我也下班回到家,他在客厅招招手,示意我快把客厅门也关上,他立即告诉母亲,他是回来接老人一同去台湾的。
他说:‘老头子(指蒋介石)不准我留下来,必须立即随行,经请求要带老母同走,只答应在家停留十分钟,届时不出去则性命不保。
’如老人愿随行,一样东西都不能带,抵台后再为她添置,并说现在汽车就停在亚培尔路口,车上还有二人在等,要母亲立即决定。老人略加思索,决定不随他行,老人说:‘我已年迈,跟你去了是你的包袱,何况留大妹一人在沪,我也不放心。
’并嘱他抵台后,说话、交友都要谨慎小心。他一口答应:‘请妈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的教训。’转身对我说:‘大妹,你要好好照料母亲。
’说完即匆匆走出后门,消失在黑暗中。不料这次话别,竟成了我们最后一面。”叶公超随溃败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赴台后,在一个不算太短的时间段内,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直到“外蒙入会案”出现,才翻船落水,一头栽入泥坑而无法脱身,并在泥猴一样翻滚腾跃而总是跳不出蒋氏父子手掌心的尴尬、郁愤中,度过了百感交集的余生。
1958年8月,叶公超调任台湾当局“驻美大使”。1961年,联合国成员国召开会议,讨论包括外蒙古等诸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
当此之时,以社会主义阵营老大自居的苏联透过美国对台北施加强大压力,阻止其对“外蒙入会案”使用否决权(时台北当局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代表,握有否决权)。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遂要求紧跟自己屁股后面的台北当局,对外蒙放弃使用否决权。 面对苏联的要挟和美国的施压,台北当局表示了极大愤慨和抗议,制定了“不顾一切,否决到底”的行动方针。
时间在台北、美国、苏联等三方相互牵制又各不相让的尖锐冲突中一天天熬过,直至10月初,联合国安理会日期已定,情势紧迫,严阵对峙的僵局仍无松解的迹象。
蒋介石不断拍发密电致常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和“驻美大使”叶公超,指示方针大计,最后对蒋、叶两位臣差在列强之间的斡旋与处置能力十分不满,乃在一电中训斥道:“弟平时一再请兄等在外发言务必慎重,以免引起揣测而损及立场,为敌所乘而影响交涉。
今外蒙事谣诼纷纭,将何以收拾……仍盼秉政府既定方针,据理力洽为是。” 在极度紧张沉闷的气氛中,“驻美大使”叶公超于10月14日奉召返台,此时距联合国安理会复会日期10月23日不到十天。
因事出突然,叶以为是回台述职,或为“外蒙入会案”当面听旨,几天后必返美,因而只带了一只旅行箱,连办公室都没有收拾,便匆匆乘机抵达台北,暂住博爱宾馆。
叶公超在宾馆梳洗打扮一番,等待“总统”蒋介石召见,结果三天过去,一点召见的迹象也没有,而过去主动前来攀亲接故的官僚政客也不见了,自己被晾在宾馆里成为一块没人理睬的洋咸菜。
既然上头没有召见的意思,耐不住孤寂冷清的叶氏便决定探亲访友,并于10月20日早上来到了胡适家。主客见面自是亲切,寒暄几句,叶说自己离美匆忙,竟把一根结实耐用的皮腰带忘于寝室。
江冬秀听罢笑着说:“找条麻绳给你吧!”胡适说:“那怎么行,一个堂堂的驻美大使腰系麻绳出入厅堂,成何体统?”于是到卧室找了一条黑色的皮带送给叶,虽短了一些,但勉强可用。叶公超又抱怨台北天气闷热,自己衣服带得太少了。
胡适又让人找了两件夏威夷衫送给叶。一番忙碌过后,胡适招待叶吃早点。饭后,四川大学原校长、时任台湾当局“教育部长”的黄季陆来访,几个人一起聊起天来,此时叶还不知道自己已不能返美了。 叶公超告别胡适一家返回博爱宾馆的第二天,得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已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强烈反对中共参加联合国或联合国所属的任何机构,强调“蒋总统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合法地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美国一直认为中华民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且一直合力支持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内的地位与所有权利”。
肯尼迪的声明经台湾岛内媒体报道,一般人尚未充分认识到这项声明与“外蒙入会案”有何直接关系,但从稍后“外交部”郑重其事地发表谈话,对肯尼迪总统声明表示“欢迎”等一系列动作来看,“外蒙入会案”已经出现了新的转折。
而这时,叶公超还不知道自己遭到了老蒋的暗算。
但很快,他便接到了一个召谕,大意是“总统”不召见了,叶也不必再回任所了,就在宾馆好吃好喝地蹲着吧。 叶公超听罢,如同晴天霹雳,想问几句为什么,传谕者早已离去。
叶公超先是蹲在地板上发愣,接着是仰躺在沙发上发呆,继之绕室彷徨,足足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直到困乏不堪,才一头倒在床上昏睡起来。未过几天,叶的“驻美大使”被正式免去,同时当局令他搬出博爱宾馆,到松江路一个小巷的院内居住。叶公超的外交生涯与从政之路算是折戟沉沙,就此梦断。
如此江山烟客逝 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按预定时间召开,对立交锋了五个多月的“外蒙入会案”,在蒋介石同意并指使台北方面放弃使用否决权的让步下顺利结束,美、苏双方皆大欢喜,台湾当局也风波不惊,渐入沉寂。
由于叶公超奉召返台后,不到十天当局就突然决定放弃否决外蒙入会,台岛和海外许多人士认为:叶公超一直不赞成对“外蒙入会案”持否决权,并与蒋公的战略方针有冲突,是他返台说服蒋介石“悬崖勒马”,最终放弃了否决权,因而他是保护台湾免于“玉石俱焚”的一大功臣。
想不到突又传出叶氏被罢黜的消息。这一变故,让世人陷入一个迷魂阵中,苦思冥想不得其解。
丢掉“驻美大使”帽子的叶公超,自搬入松江路一个院子居住之后,当局又派人送来一顶“行政院政务委员”的纸糊帽子让其戴在头上。
自此,台北当局与叶氏之间,便开始了狸猫戏老鼠的游戏。叶的家室皆在美国,当局对其来了个“斩足”行动,明令叶不能迈出台湾半步,更不要想出国探望妻子儿女之事,只能在台湾本岛内部转悠。 原来的朋友相好一听说叶被蒋公下令免职,皆认为背后必有隐情,乃像躲瘟疫一样躲避他,再也不敢上门或在路上相遇后打招呼了。
尚有自知之明的叶氏除了与几位相当密切的旧友??这几位不会因与他接触而有所损失的人物如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人来往,实在感到憋不住了,便以“政务委员”的头衔向当局要部车子,于黄昏时分到台北郊外与海边转上几圈,借以疏解心中的郁闷之气。
如此往复数日,叶公超感到胸中的闷气消了不少,如是者数日。
有一天,叶驱车转悠时突然感觉不对,四周好像多了点什么,脑子忽地想起“跟踪”一词,再往周围一看,果然如此,显然有便衣跟踪自己。叶公超大怒,当天晚上就打电话给蒋经国,发了一阵牢骚后痛斥当局派特务跟踪。
蒋经国表面上对叶极为客气,似亲兄弟一般,但内心深处从没有把叶当成自己圈中的人物。蒋经国听罢,表示可能是主持这方面事务的彭孟缉误会所致,一定要与他说个明白,何必如此无礼云云。
结果隔了几天叶氏再度外出,仍有特务和秘密警察盯着,叶遂明白是蒋家父子耍的布袋戏,自己实际上已钻入人家张开的布袋中被软禁了,遂不再抗议,任凭特务们跟踪下去。对于这种非人非鬼的生活,叶公超恼怒于心,但又无处发作。
一次,叶的老友,曾与蒋经国一度关系密切,后又分裂的“中统”重要特工之一蔡孟坚前来拜会,叶说:“你虽然被经国摘了纱帽,但社会舆论很同情你。你好在与老先生有深远历史,否则,你如我一样,不准步出国门,让你出国乱跑。
”蔡说:“你已有一政务委员高职,足以安慰,时时彩技巧。”叶说:“我此时是有‘务’而无‘政’的空名义。”蔡不解此意,叶公超不无愤怒地解释:“身边有‘特务’,‘政事’不准问。
”还补充说,“行政院会议时,只有我一人‘小便’,有人随同‘保护’。” 尽管有特务跟踪,生活还要过下去,叶公超开始蹲在居室习字绘画,过起了“怒写竹,喜写兰”的文人雅士生活。
几十年前的好友、时任教于台湾师大的梁实秋认为叶不宜长时间憋在屋子里,需到外面透透气,遂不避各方射来的警觉紧张的目光,力邀叶到校任教,讲授现代英美诗等课程。叶自是乐意前往,遂重执教鞭当起了教书先生,只要是叶氏上课,台下皆坐满听众,到底是听课还是观人,叶并不计较,只是私下向梁实秋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云云。
然而不久,当局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一个学期勉强结束,叶公超被迫收拾场子走人。
除了特务跟踪给自己带来的郁闷与孤愤,被困台湾不准去美国和亲人团聚,亦是叶公超晚年最大的痛苦之一。他说:“我会被困死在这个岛上。” 1977年,费正清由美国造访台湾,此时蒋介石已撒手归天,其子蒋经国掌控大局。
费氏回忆说:“在台北最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再次会见前任外交部部长叶公超,他依旧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仍然牢牢地坐在政务委员的位置上,他喜欢孤独,然而却奉命去处理预算问题。
他外出时,秘密警察跟踪他;当他住院时,蒋经国却莅临探望??一种对最高级天才的奇怪的愚弄。” 1981年临近中秋节的一个晚上,叶公超在邻居陈子和的画室里叹了口气说:“我是有家归不得。
”过一会儿又说:“我要给我在美国的女儿画一幅竹。”在场的人都为他这种孤独思女的心绪所感染。到了这年的11月,叶公超一病不起,行将进入另一个世界。弥留之际,他不断念叨:“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女儿,都要来看我啦!
”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在孤寂凄凉中因心脏病于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终年七十七岁。一生历尽繁华、看惯了热闹的他,在撒手人寰之际,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殡葬时也显得格外冷清,夫人袁永熹没有赴台告别,只以未亡人身份撰献了一副挽联。 狂傲本奇才,唯贤哲多能,如此江山烟客逝; ,时时彩平台评测网; 贱辰劳玉趾,忆清谈移晷,最难风雨故人来。
叶、袁结婚四十多年,总是聚少离多。1940年袁永熹携子女赴美定居,在美终了一生。 叶在美国时,只有在外交场合需要非出面不可的时候,袁氏才以夫人身份出场应付一时,两人对家庭生活越来越淡漠,感情亦越来越疏远,最后竟形同路人,令后之观者扼腕一叹。
由“外蒙入会案”而衍生出来的神秘的“叶公超去职案”随着叶的去世更加扑朔迷离,叶公超因此被蒋家父子“斩足”禁锢了整整二十个年头,终致叶在凄惨的晚景中赍志以殁,更加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