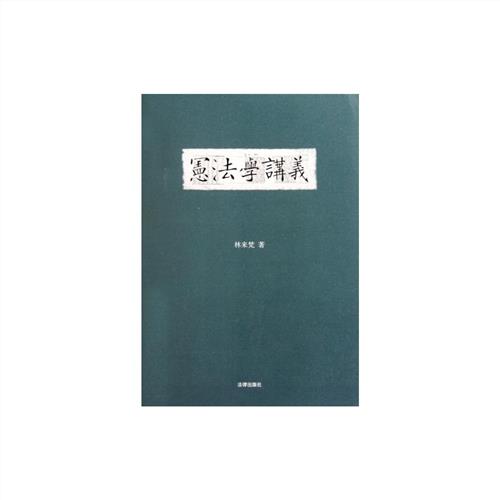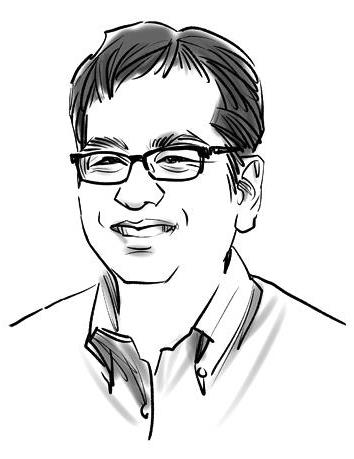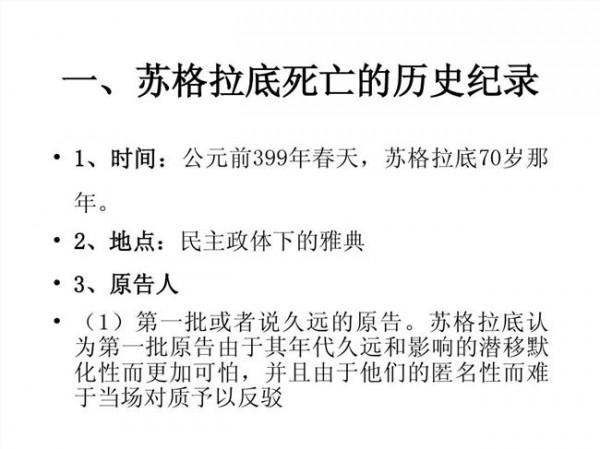宪法学林来梵 林来梵:宪法学的方法与谋略
张千帆老师: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我们很有幸请到了浙江大学林来梵教授给我们作报告。林教授,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不用太多介绍了。林教授生在福建,后来又在杭州任教,所以是标准的南方人。但他有北方人的豪爽和个头,所以很多人看到来梵教授,听说他是南方人都大吃一惊。他有颇为传奇的求学经历,早年到日本求学,后来是在立命馆大学,这个大学可能中国人不太熟悉,但在日本法学是很有名的。立命是“安身立命”的立命,等于从那儿拿到博士学位就可以立命了。回来以后出版了一本我们大家都知道,叫《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很多学习宪法的人可能都读过。那么,我就不多介绍了。林教授给我们讲座的题目是《宪法学的方法与谋略》,我个人最感兴趣的是林教授要给我们的宪法学一个什么样的谋略。
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评议人:中央民族大学的熊文钊教授,社科院法学所的高全喜教授。下面我们就欢迎林来梵教授给我们做学术报告。
林来梵教授:今天我这是第二次刮了胡子进了北大,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在中国,据说很多读书人其实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来北大读书。我记得自己在1979年的时候——那时我还16岁,在南方的一个村庄考大学,那个村庄的名字叫南社。
当时,我的一个老师告诉我说,你有可能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我那时还是乡下小孩,就问他:最好的大学是那一所呢?他说就是北大,全称是“北京大学”。但最终结果是我并没有考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自己在中学时还比较得意的作文写作居然在高考时写离题了,而且是很严重的离题,总分40分基本上都没有了。
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就进一步离题,到日本求学我觉得也是一种离题。在日本96年博士课程毕业时,我记得我还想圆自己的北大梦,于是就给肖蔚云老师写信,希望能够入读北大的博士后。
当时博士后的招生好像刚刚兴起,我非常荣幸的接到了肖老师的答复,说是可以的——我现在还珍藏着这些信。于是96年夏季我就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北大,结果肖老师在香港开会,因为他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刚好去了香港。
于是我就到香港找他,但是还是没有找到。恰好当时香港的一个大学正在招聘,我就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去试了一下,结果被聘上了,而我的北大梦终究没有圆成。
今天我就带着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来到这里,和大家交流自己一下自己研究的一个心得。关于这个心得,我这几天刚刚想到一个题目,初步定为《宪法学的方法和谋略》,并临时组织了一下其中的要点,完全是一个不成熟的思考结果。闲话暂且不表,接下来就进入正题(打开PPT开始演示)。
这个正题主要讲四个内容:一是方法的意义;二是宪法学的方法;第三个内容是方法与谋略;第四个,则是简单的反观一下我们中国,即简单的回过头来看我们中国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讲方法的意义。我个人对方法论比较感兴趣,因为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部门法学科的学者,有三种东西特别重要,尤其是在宪法学研究当中特别重要。哪三种呢?首先一个是拥有可靠的方法论;第二个是能够在历史的脉络中把握问题,比如我们研究宪法,就要把握立宪主义这样一个历史课题。但这样一个历史课题在西方有一个历史脉络,在中国,它的发展和形成也有一个历史脉络。那么,如何在这样的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把握各种具体的问题,我觉得就非常重要。第三个也很重要,那就是作为部门法学者,应该形成自己法教义学意义上的学说体系。在这三个东西中,我对其中的方法问题已经开始着力在思考,虽然目前研究不深,但是也有了一些看法。
我觉得,从总的来说,方法的作用、意义是非常大的。那么,它的作用、意义在哪里呢?我觉得至少在这几方面:比如说我们视角的把握,问题的设定或形成,或者问题的解决方法,甚至我们的理论构成、功效的控制——至少在这几个方面,部门法也好,法哲学也好,方法论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在这里我们大家都能想起我非常喜欢的德国一个著名的法哲学家——拉德布鲁赫。他有一个名言经常被引用,大致是说:某一个学科如果沉溺于方法论,那么这个学科就可能是“有病的科学”。
这句话大家也许都比较熟悉,用拉德布鲁赫这句话来看我们当下的中国宪法学,我却冒昧的以为,中国宪法学也可以说是一个“有病的学科”,至少可以说中国宪法学还在“感冒”。为什么这么说,大家都知道,因为原因都很清楚。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宪法学在方法论上甚至还没有觉醒。拉德布鲁赫的说法事实上一直回荡在我们的耳边,我们用他的这句话来反思我们中国的宪法学,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哈贝马斯曾经说过,哲学必须为自己的失效负责。我觉得,我们中国宪法学也必须为自己的失效负责。而要跳出这样一个怪圈,我们就必须重视方法问题,把方法论问题的思考贯彻到宪法学研究的起点当中。这是今天要讲的第一点。
下面我们来讲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宪法学的方法。在这点上,我准备讲两个问题,一个是各国通行的方法,一个是我国当下的状况,即方法应用的状况。
首先讲各国通行的方法。关于各国宪法学通行的方法,有多种多样整理的方法。我从自己的角度初步整理了一下,认为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从传统来看。传统的方法应该是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方法,或者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法学意义上的宪法学。
因为这个法教义学和“法学”基本上是等同的。同学们可能都看过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他就把法教义学和“狭义的法学”基本上等同看待。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是现代出现的几种方法,我认为它们基本上都属于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宪法学,其中又有几种具体的主要的门类或流派:第一种是狭义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宪法学;第二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宪法学,但大家要注意,这里所说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宪法学”和作为政治话语的宪法学有所不同,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德国施米特的宪法学,它才是典型意义上的政治学意义上的宪法学;第三种则是在美国等国家沛然兴起的、在当下中国也有所影响的经济学意义上的宪法学;第四种虽然不是非常严格的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宪法学,但在我国也可能会被拉入这样一个范畴,那就是哲学意义上的宪法学,有人把它叫做宪法哲学;第五则包括其他多种,比如宪法人类学,宪法心理学等多种宪法学的门类。
应该说,各个国家的宪法学所运用的方法,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综观各国状况,以上这些方法大致就是它们通行的方法。
其次,我们来看第二点我国当下的方法状况,这又可以分为两点来讲。第一点讲我国迄今为止的主流的方法。我觉得在我国当下的宪法学的方法状况当中,存在一种迄今为止的主流,但对这个主流方法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最近我才想出一些妥当的表述方法。
我认为它具有两面性,这两个方面是具有一定的关联性的,而且彼此之间还具有一定的递进关系:一方面是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之下,将宪法现象倾向性地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甚至是一种政治现象,并对其进行把握,由此自然进入了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宪法学范畴之中;另一方面,它又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致力于对现实中的实定宪法进行解说性的阐明,以完成正当化的政治话语、或者说哈贝马思所讲的“言语行为的功能”。
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宪法学的主流。那么,简单说,我国宪法学迄今为止的主流可如何定位呢?我认为它是一种“解说性的宪法学”。在这里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解说性的宪法学”和“解释性的宪法学”是有根本不同的。
“解说”虽然也是一种阐明,一种对含义的阐明,比如说对条文涵义、立法原意的阐明,但是它的最主要的功能则止于正当化,只是止于对条文设定、立法原意以及制度构成的缘由进行正当化的一种说明。而“解释性的宪法学”的门类则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宪法解释学,既传统上的“宪法解释学”,当然,这个“宪法解释学”在当今世界各国也已经有所发展了,如果只用宪法解释学来涵盖宪法学,甚至用宪法解释学来涵盖法教义学意义上的宪法学也已经是不可能了,因此我此前提出了“规范宪法学”这样一个更大的概念,来涵盖现代应有的方法。
但对于法教义学意义上的宪法学,总的还是可以说,其迄今为止的核心方法,还是解说性的宪法学。
在晚近,我国宪法学界就出现了一种潮流,这种潮流也反应在这样一个情况上面。那就是首先出现了一种“脱政治话语”这样一种潮流,即希望我们宪法学研究能够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而不是形成一种政治话语,或直接被编入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之中。
而在这种“脱政治话语”的研究中,最后还进一步产生了一个“脱事实论”的研究。我们知道,在德国,传统法学的研究被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事实论的研究,一个是规范论的研究。事实论的研究最主要是研究“是什么”,这主要是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宪法学所关心的主题,它研究某一种宪法现象的状况如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宪法现象;而规范论的研究则主要是研究“应该怎么样”这样一类问题。
在传统的大陆法国家的历史中,规范论的研究实际上一直是占主流地位的。
我们知道,事实论的研究实际上是在近代科学主义沛然兴起之后,特别是在法学领域中法社会学兴起之后,才形成研究热点的,它最主要是把法当成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而不是把法当成非常复杂的、用德国话来讲乃是“人类客观的精神现象”来研究的。
这一点,中国的许多学者和学生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把法看成一种社会现象、政治现象,而不会把法看成是一种人类的精神现象。
为什么我们中国会这样呢?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了我们,所以把法看成是一种社会现象;第二个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深厚的法治传统,因此不会把法看成是客观的精神现象,把法看成是客观的精神现象来把握的这种精神在中国是很难产生的。
一旦谁产生了这种观念,反而可能被看作是幼稚的,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发疯的。因此在我们中国就很难产生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或者说法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很难奠定基础,在宪法学领域尤其如此。
而我们中国近数年来的宪法学研究所出现的一种新的潮流或动向,就是摆脱事实论的研究,至少是尽量在事实论研究的同时,适度的返回“规范主义”,把宪法不仅仅看成是社会现象或政治现象,而且主要是看成一种规范现象来进行研究。这是我国当下的状况。
好,以上两点简单的讲完了。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讲第三点:方法与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