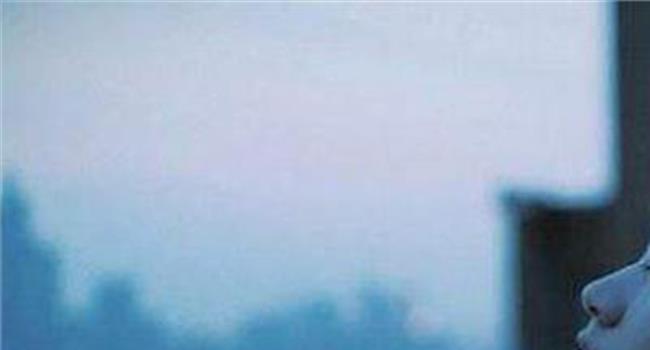萧功秦是不是狗 萧功秦:新左派是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与墨子刻教授的谈话
新左派是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五十年代的计划主义者并没有失败的教训,他们是好心做错了事。而新左派却没有这样的借口,平均主义造成的灾难我们早已经领教了,继续把左作为中国药方,难道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作者按: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先生是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思想史研究,他是我所认识的少数对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思潮研究有透辟见解的美国学者之一,墨子刻先生的思想属于保守主义,但他又与那些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家不同,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热情关注, 对中国问题的同情理解,完全不同于那些指手划脚的美国保守派议员。
他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界动态了解之清晰,使我自己作为中国人也自愧不如,每当他谈及他最近谈到的一些中国学者的最新著作,甚至有些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子的论文与著作,常常使我非常感动。
每次他来中国,我都要设法与他相见,向这位我钦佩的先辈请教。每次见面我们都相谈甚欢。这是二000年深秋我与他在上海相见数小时的谈话回忆。
今天早上天气真是好极了。秋日明媚的阳光洒在大地上,我九点钟准时赶到华东师大专家楼门口,正好遇见老墨在散步,于是我与他一起在丽娃河畔漫步。他首先说,这儿的风景比斯坦福好。这儿的人看上去很轻松,笑得那么自然舒展,有些城市的市民脸老是紧绷绷的,可见上海都市的人们生活得还不错,这儿一切看来是令他们满意的。
我说,是不是所有的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天生有一种浪漫心态?他们总是由衷地夸奖别的国家与别的文化的优点,人们这样做的往往是无意识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批评本国的立足点或参照物。其实中国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问题,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久居之后你会发现很多问题。
他似乎并不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我也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争论下去,我有许多问题要向这位充满智慧的长辈学者请教。以下是他谈到的一些问题与观点。
一个社会的进步需要精英阶级我问老墨对精英主义理论怎么看,我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政治文化中就渗透着反精英主义的价值倾向,在中国,很少有人正面为精英主义作辩解。我很想知道精英主义理论的内在逻辑。老墨的回答是,由于某些人对社会有比别人更大的贡献,社会给予他的稀缺资源,如荣誉权力地位金钱,要比别人多,例如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所获得的荣誉就比一个没有这种重大发明的科学家要多。
这样,拥有这类稀缺资源的人们就取得了影响社会的地位,如果把社会层级用金字塔来比喻,这样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们就处于金字塔的上端,这就是精英。
每个社会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与文化社会领域都有这样一些精英。在一个公平的健全的社会里,精英的形成应该是一个自然的竞争过程。
如果没有鼓励人们成为精英的社会机制,这样的社会将是没有发展动力的社会。民粹主义者反对精英这一客观事实存在,实际上这不是鼓励社会进步,而是导致社会停顿,因为这是要人为地拉平了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的在知识、智慧、能力与竞争力的差距。
当然,一个社会要尽可能公平地给予所有公民以同等的教育机会,使每个人在争取成为精英的竞争中机会上要均等。虽然要绝对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美国在为公民提供平等竞争机会这方面做得并不好。
关于变革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腐败
我问老墨,如何看待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腐败问题,老墨的看法相当独特,他说,其实,就中国而言,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有些国家的腐败比中国要严重得多。当官的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搞到好处,要完全避免这一点是不太可能的。
人性总是有弱点的。他相信从总体而言,真正坏的官员还是少数。最重要的是,社会是不是比过去繁荣进步。 对这一点我也表示同意,在我看来,在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下,资源配置的权力总是掌握在官员手中,只要经济开放,官员搞钱的机会肯定比他在经济封闭的时候要多。
官员比其他人的机会也更多。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过程初期,社会对个人的监督能力的完善总是滞后一些的,在这个时间差里,官员腐败就有了可能。
这一切是不完美的。不完美是事物的属性。我们只有承认这一客观事实,才能进一步考虑应该如何办,当然,认识到现代化过程中的腐败难以完全避免,并不意味着是要纵容腐败。更不是要为腐败辩护。制定法律,强化监督,严惩腐败完全是必要的。
中国文化中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传统
我问及,墨先生前天在华东师大哲学系座谈时说过,中国文化中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传统,儒家思想不是保守主义而是复古主义,这一观点颇为新鲜。能否进一步说明一下理由是什么。
老墨认为,从亚里士多德到当代的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西方的保守主义是环绕着这样一种对传统的观念而持续下来的,这种传统观念是以希腊文化的历史观作为前提的,这种历史观认为,历史始终是一个神魔混杂的过程,古代既不象儒家文化中所主张的那样,有一个由政教合一的圣人所统率的美好无比的“三代”,未来也不可能有什么所谓的大同境界。
根据这种历史观,一个具体的社会的传统也同样是神魔混杂的,一个社会中始终有着很多与人类理想相矛盾的成份。
例如,总是有着既得利益者,有着假公济私的官僚政客,有着财产富分配上的不公正,等等。然而,如果人们聪明一点,他们会通过努力使比较坏的社会变成一个比较好一些的社会。他们会形成一些能减少种种恶事的风俗、习惯与政经制度,这样一来,人类的生活一方面并不完美,另一方面也还是很有价值的,这个世界还是很值得留恋,是有趣味的。
世界既不完美也还值得活下去,人们还有希望使世界变得比它原来的样子更好一些。
既然人们对生活的要求既不太高,又不满足,这就不会走极端,就能心平气活地考虑这个世界的种种问题,如果人们认同这样一个前提,那么,无论是要保守传统,还是要改革传统,都是对方可以理解与体谅的。
更具体地说,改革传统,是因为传统并不完美,保守传统,是因为传统值得我们留恋。它既不坏到哪里,也不好到哪里,这样,知识分子与国民就会形成一种保守主义与改革主义之间的持续的对话。这就是西方意义上的保守主义。
西方的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革,但反对以人的理性去设计建构一个新社会,反对以这种想当然的“新社会”模式来取代现实社会,其原因就以这种历史观为基础的。 老墨进而认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就不是这样,中国人的“三代”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人们总是不自觉地以“三代”这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古代理想社会来对照现实世界的不完美。
中国知识分子深受这种思想方法的影响。例如,人们会认为,既然政府是不完美的,以理想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怎么可以与不完美的政府合作?一个政府无论取得什么样的进步,公开支持政府的人士,就会被视为“御用文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有“抗议精神”,新儒家徐复观在这方面的态度就很具有代表性,用徐复观的话来说,“假如一个知识分子要公开地谈政治,他就必须批判,不能赞美。
”这样,事实求是地谈论当代政治与政策的得失就并不重要,批判则成了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大事。于是,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与政府反对这种抗议而进行的政治压制,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就会变成政治上的家常便饭。这样的社会是不容易团结进步的。英美政治文化有很多方面是有问题的,然而,却能够比中国更能避免这种恶性循环。我不能不说,中国朋友应该学学我们。
其实,四十年以前,胡适就在台湾对知识分子提出这方面的批评意见。可以他们听不进。人们一直崇尚的是殷海光式的抗议精神。我还是希望大陆的知识分子比台湾的知识分子更能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从“抗议精神”转向“平心静气地谈论政策得失”。
老墨还进一步认为,五四虽然对传统文化予以严厉的批评,但并没有批评儒家传统的这个方面,即以完美的“三代”的道德理性来评价现实。五四知识分子就是如此,他们一方面抹杀了儒家思想中有价值的方面,另一方面却与新儒家一样,对中国文化对传统的态度(即三代模式)缺乏真正反思。儒家思想酝酿出来的传统,就是每一代知识分子始终不能摆脱“三代价值”。
不同的只是不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自己的心目中的“三代”,五十至七十年代,左的的教义成为新“三代”,改革以后,西方民主又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三代”,一个民族自身的集体经验从来没有在知识分子中受到真正的重视。而知识分子要实现这种转变,实在是需要有这种对传统的批评反思的。
造成中国缺乏保守主义的原因是什么?
我问,为什么中国文化中缺乏西方意义上的那种以集体经验为本位的保守主义?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老墨想了好一会,终于提出了他的见解,他的意思很复杂,大意是这样的:
由于西方文化对人性的看法是悲观的,他们很容易对人所从事的政治活动有很悲观的看法。既然人性是恶的,单纯以道德教义来涵养个人是没有什么指望的,于是,西方人可能求助于集体经验,求助于经验中形成的更好的制度与法律来解决问题。
相反,中国对人性是则是乐观的,人性本善,因此道德就可以解决问题。在儒家看来,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道德教育就足以通过把人潜在的善的本能从隐藏状态中发扬出来,以为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在中国人看来,中国政治应该实行最高的道德,儒家认为,既然官员与百姓都是性善的,中国的问题只要道德化,只要人人按道德方式办事,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总而言之,西方与中国这方面的不同是跟各自的人性观和历史观有关。人性观与历史观这两者也是彼此相互依赖的。复三代之古的政治观是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假如人性不善,三代当然也不可能有。
孔子述而不作,这就是意味着,他乐观地认为,中国已经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过去时代,一切只要按过去的模式做,什么问题也就解决了,在他看来,因为我们有一个神圣的经典,一切都可以从那里找到现成答案。在儒家看来,一个要培养政治智慧的学者与政治家,是不必研究三代以后的政治历史的,亚里士多德则不同。
可以在老墨所谈的观点的基础上,作这样的发挥,中国文化中的普遍的性善论,导致道德主义是解决中国政治的原则途径,道德说教成为儒家最经常要做的事,甚至是唯一重要的事,那么,对于现实生活中那些不符合人们的道德标准的人与事,那就被定位为恶人恶事,对于一个被认为是恶的社会,例如五四知识分子所理解的传统社会,那么办法也就很简单,只要用人的理性所认定的道德社会的标准,在心目中重建一个新社会,并以这个头脑中的“新社会”取代旧社会,问题也就解决了。
孔子的道德王国在过去,即三代,而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王国则在未来。这两者趣向不同,但思维方式上完全一致,都是崇尚一个实际上人类经验世界中并不存在东西,并以这个道德理性的原则来重塑现实社会,前者的榜样在过去,因此趋向于复古,后者的榜样在未来,因此趋向于激进地反对传统。
两者的共同点是都不承认现实中的社会是人类集体经验的产物,不承认这种历史产物是一方水土上生活的人们适应自身环境挑战中才形成的。因此,我们只有改良它而不应简单地摧毁它。
新左派是不负责任的理想主义
老墨对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新左派思潮很不以为然,他谈到一位颇有影响的新左派学者时说,这位学者用抽象的大概念,如“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工具”之类的大话、用那种笼统的、一般性的说法,来掩盖具体的实际问题。
纸上谈兵是最要不得的。什么是看现代性的标准?现代性对中国人有什么不好?看一件东西好不好,是看他给中国人带来了好处没有,改革以前的中国原来是一个什么社会?原来的社会是现代性太多了还是太少了?如果原来中国的现代性太少了,主张中国要现代性多一些有什么不好?不要光看现代性的来源,不要因为它来源于西方,所以就说现代性不好,其不聪明就如同当年希特勒因为物理学家是犹太人搞的,所以不要物理学,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德国没有了原子弹。
我说我在读新左派的文章时,总想不通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容易忘记自己的苦难经验,只过了没有几年,就会有人称自己是“红小兵”,要继承的文化大革命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看他们的文章是一种精神折磨,有一种痛苦感。
(后来我在一份报纸上看到此位“红小兵”的大幅相片,隐约感觉到那笑脸上似乎有某种“后主义”的玩世不恭的神情,才觉得,在中国是不是左的言论也是可以用来作秀的?但愿我的这种想法是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偏见。)在我看来,那些主张中国不应该强调现代性的论点的文章(例如汪晖先生的文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