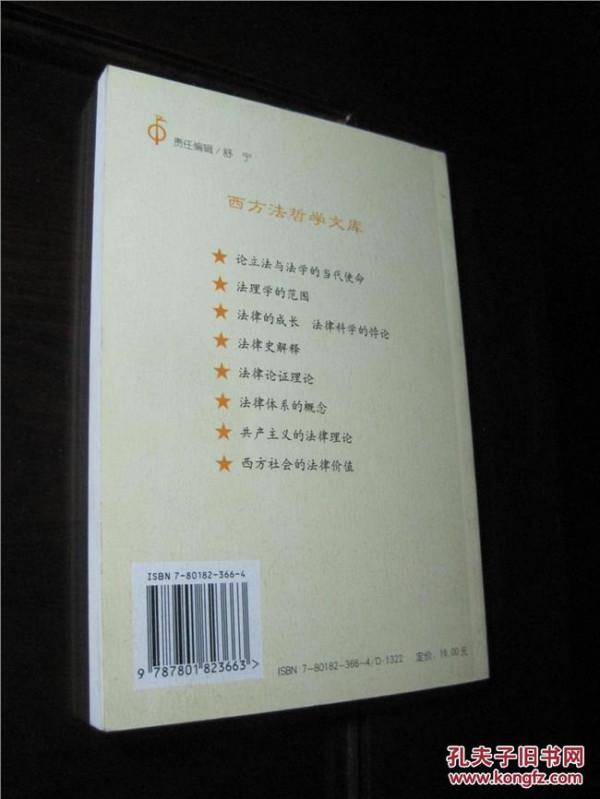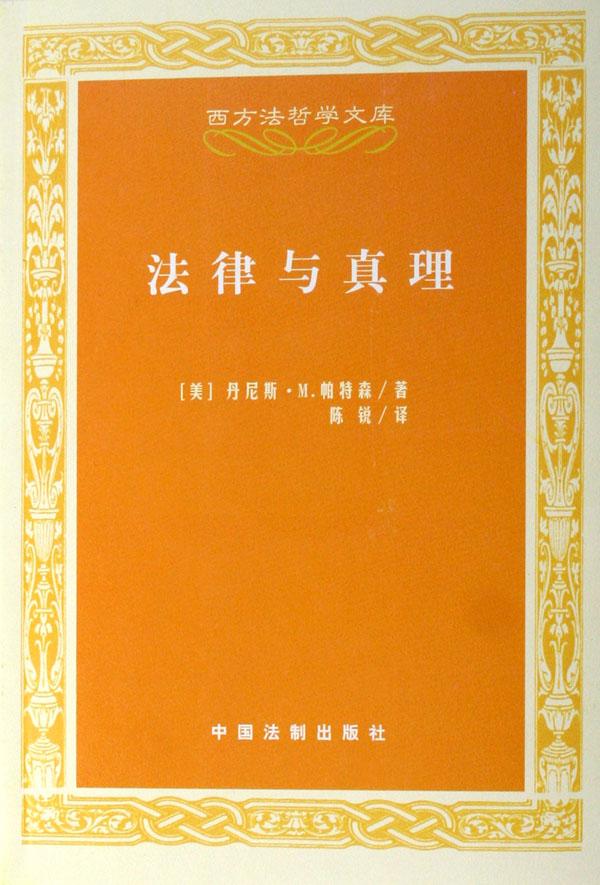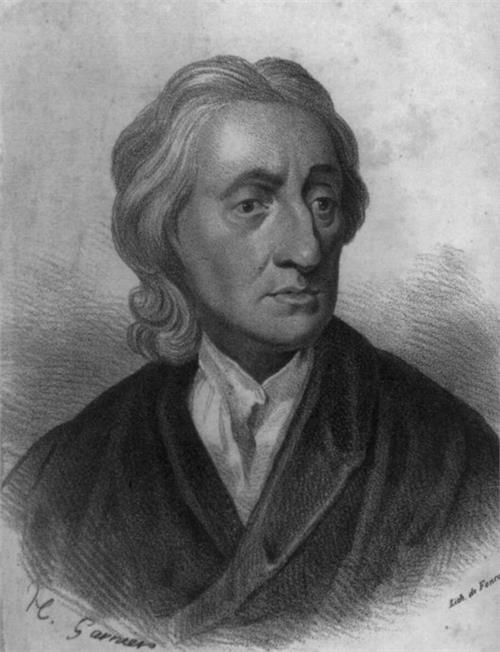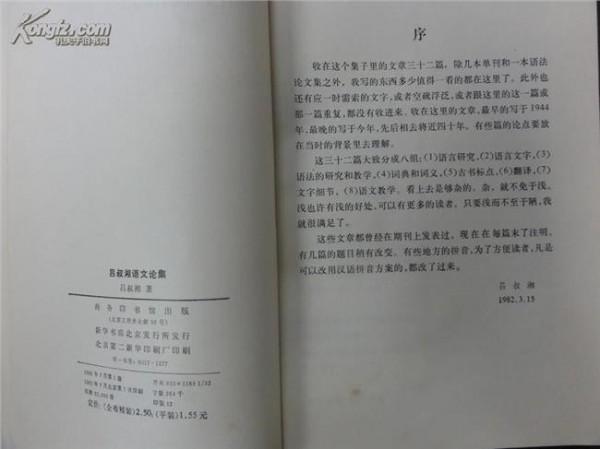哲学高全喜 高全喜:关于法律与权威的几点法哲学思考
法律与权威的关系是一个老而新的话题,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今天我们在此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制定的法律已经很多了,法律的强制力也不可谓不充分,但我们的法律真的具有权威吗?人民是否真的是出于信赖而服从法律吗?我们的法律权威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权威,它们的正当性如何?等等,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关注。
我的发言主要是从法哲学的角度,对法律与权威的关系作一个初步的勾勒,涉及三种理论的叙说。
法律不同于道德礼仪或宗教信条,属于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权力的行为规范,塑造的是社会秩序,或者说是社会秩序的规范形态或控制形态,因此,法律从产生之日起,就具有世俗权威的特性,没有权威的法律不是法律。但是,究竟什么是法律,什么是权威,法律与权威的关系是怎样的,在中西法律思想史中却从来没有定于一尊的理论,古往今来,各家各派,形成了诸多理论和学说。
尽管如此,如果从大的方面看,从形态类别上看,关于法律与权威的关系,在西方思想史中,概括起来还是可以分成三个类别,即政治理论、哲学理论和法学理论,也就是说,由于法律与权威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的综合性问题,而不是单纯的一个法律问题。
因此,理论家们基于不同的立足点,从政治、哲学和法学这三个领域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关于法律与权威的问题阈,虽然它们相互之间的很多问题是重叠的,但侧重点却是不同的,甚至是抵牾的。
下面先看政治理论。由于法律与权威的交集关涉社会权力,或者更准确地说关涉政治权力,因此,从政治权力和社会秩序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便构成了政治理论的要点。法律的制定以及公民对于法律的服从,从政治看,就是依据权力(power),权力是政治的本质,法律的权威也就是政治权力的权威,power等同于权威。
基于权力之下的法律,其基本的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安全和人身自由等。历史地看,这个政治权力主要的是来自国家,国家权力构成了法律权威的最后支撑,所以,法律与权威的政治理论又可以说是一种国家理论,我们知道,奥斯丁、哈特等人的法律实证主义便是以这个政治理论为前提的,国家权力论或国家主权论是这派理论的政治前提,主权者是实证法的政治渊源。
当然,政治理论还不止这一家,社会契约论也是近代以来的一种有关国家构成的主流理论,法律的权威也可以从这类签约类的国家学说中推导出来,代表性的人物如霍布斯、洛克、卢梭等,这为他们的法律理论提供了另外一种有关国家的权威性的来源。
不过,这种国家学说实际上已经开始超越了对于power的实证主义考察,具有了探究其背后的正当性问题——国家正义的意义,这样就进入了哲学范畴,或者说成为一种政治哲学。
关于法律与权威的哲学理论,最为突出的是各种自然法的理论。自然法对于国家权力的本性给于另一种正义论的论述,在此,power被justice置换,政治论的国家权力或国家主权的权威性受到挑战,即为什么政治权力是有效的,国家主权是绝对的,它们要面对rights问题的质疑,因此,自然权利论、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论、社会正义论等出来了。
我们看到,政治秩序、社会安全、人身特权等传统的政治法制问题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消解,至少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在相当一段时间(十七、十八世纪)是激进主义的,可惜的是当近代自由主义刚刚开始转向保守,即转向古典自由主义或保守的自由主义,左派激进主义,即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就裹挟着满腔的热血和正义的戾气开始新一轮的批判与革命的狂潮,法律权威的辩护在哲学理论的滔滔言辞中只能偏于一隅,为保守主义的思想所惨淡持守。
在哲学理论上,英国的休谟、博克,法国的波叙哀、迈斯特,德国的黑格尔、洪堡等人,他们关于秩序、等级、权威、法制、自由与传统的论述构成了不同于激进革命的另外一种理论景观,这类思想家们的遗产也值得我们关注。
下面我重点谈一下法律与权威的法学理论。从本性上说,法学理论是保守的,法律秩序是社会政治秩序中的最重要的内容,法学对于法律与权威的考察显然不同于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的视角,它既不需要像哲学理论那样穷究法律(国家法制)的终极性正义本源,也不像政治理论那样镂析权力体系和政治秩序的运作、功能与绩效,而是偏重于法律规则本身,即法律的本性、规范、程序与裁决,所谓法律的统治是矣。
当然,法治有一个法律的权威问题,而且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但这个法学理论的权威不是权力,也不是正义,而是authority。
法律为什么要求人民服从,人民有守法的义务,不是因为法律是出于垄断性的暴力的制定,也不是因为自然法意义上的正义,而是法律具有权威,即它们包含着authority,权威是一种合法的权威,或正义的权威,它的约束力来自人民的自愿服从,但又不是自然法则,而是基于强制力的权威,甚至这个强制力来自国家。
也许从政治学上看,power与authority是等同的,权力与权威没有太大的区别,都与政治或国家的强制力有关,但是从法学理论上看,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关键性的,法治的本性就是要在国家政治权力的腰眼上插入法律这个楔子,用法律的统治这个轭约束权力的暴虐,所谓权威指的就是被法律约束的权力,或者说政治权力得到合法化的使用。
说起来,如何制约政治权力,这是一个古老的技艺,法律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追溯源头,权威(authority)一词是一个罗马法概念,早在罗马共和国,法律的权威就与限制权力联系在一起,至于英国普通法的宪政主义,有关大法官科克与詹姆斯国王就统治权与司法权的争论等,这些都说明了法治的独特性意义。
从法学理论的视角来看,法律与权威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法律塑造或构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只有合法的权力才是正义的权力,即权威,不合法的权力则没有正义,属于赤裸裸的暴力;另一方面法律又限制或约束政治权力的恣意妄为,即政治权力不能是不受约束的,没有规则的,没有限度的,因此,法律权威从法学的角度看就是constitution。
宪政从原初的意义上说是权力的结构构建,即通过法制秩序来构建法律的权威,因此,罗马法的权威在于权力制衡的政体,英国法的权威也在英国的混合政体。
近代以来,从源流上看,法律与权威的法学理论有两个谱系,一个是强调立法权的实证法学派的法律权威理论,这个为新老分析法学所发扬,另一个是强调司法权的普通法心智的法律权威理论,这个为英美的法官造法理论所坚守,前者维护国家权威,后者维护私法权威,但就authority来说,两者又有共通之处,即任何政治权力都必须得到法律的支持与庇护,政治秩序的维护、社会安全的保卫、人身权利的保障,财产权、自由权、言论权的确立与救济,等等,都只能通过权威性的法律制度来实施。
法律是有约束力的,法律不是道德,在它的背后有国家强制力,但是法律又是一种普遍规范,一种形式程序,其权威性在于正义,当然,这个正义不是哲学理论中探究的终极性正义,而是法律正义,即落实为救济的权利,国家权力只有得到法律的约束并旨在维护人民的权利,才获得权威性,得到人民的服从。
至于如何使得国家的政治权力在法律的权威方面得到落实,这是一个制度技艺问题,对此,罗马宪政和罗马法,英国宪政与英国普通法,乃至德国的法治国,美国的复合联邦政体和司法制度,等等,都提供了良好的法治教益。
拉德布鲁赫在《法哲学》一书中曾经指出,关于法律的约束力的政治理论、哲学理论和法学理论只具有相对的价值,三者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化解的,因此,他认为法律的约束力并不是因为它极其容易使自己获得被遵守的效力,而是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维持安全。
把法律权威的根据付诸于社会共同体的安全,这可能是拉德布鲁赫的无奈之举。在我看来,在可能是低限标准,应该看到,法律权威依然有着自己的高线诉求,即把法学理论与保守自由主义结合起来。
法学理论提供的是一种形式正义,法律所维护不仅是安全,而且还有自由,当然这个自由是法治下的自由,这个自由只能寄托于法律的权威。基于个人权利论以及自然权利说的近现代自由主义曾经有一个激进主义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理论特色是反对权威的,包括神学权威、政治权威和法律权威,但是成熟的自由主义或革命之后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其保守主义的本性使得法律权威这个问题凸显出来。
法治与人权、民主是有一定张力的,法律的统治需要一种权威理论,权威从终极性上说来自人民授权,来自民主政治,来自人权保障,但它们要塑造秩序,实现自由,必须经过法律的过滤,必须建立法律权威,人民必须守法,恪守服从法律的义务,因此,authority这个中介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