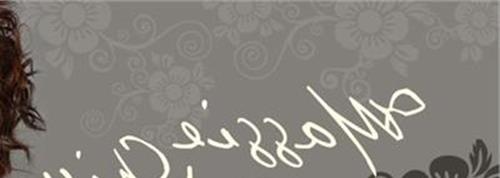王岐山被曝在家做饭待客 多次提美剧《纸牌屋》
1979年底,***作为实习研究员,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研究室工作。 时任民国史室副主任的朱信泉曾对媒体描述,***是“一个热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轻人……学了四年历史,基本功不错。”
据《京华时报》报道,当时***被分到了编纂《民国人物传》的小组。期间,他先是参与修订《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与作者贺觉非一起花了近半年时间将书稿敲定。之后,***接着参与到《民国人物传》的编纂中。“如果这么发展下去,他肯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研究员。”朱信泉曾如此评价。
1978年8月,***的岳父***出任商业部部长、党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任中央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就在这一段时期,王开始将一部分注意力从历史研究转移到改革和经济问题上。
当时,中国长期积累的各类国民经济问题开始显现。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感到迷茫,也存在分歧。1979年,全国提出建设10个“大庆”、30个“大化肥”,以及若干个“大钢厂”,“***”中打了鸡血一样的时局隐隐可见。
这些急躁的政策,引起了社科院研究生黄江南的注意。当时在社科院的学生中,流行着一种小型沙龙,十来个年轻人聚在一起,讨论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就有社科院研究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黄江南、朱嘉明,以及后来的社会学家李银河。
“(在“***”结束之前)从7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小圈子。”李银河告诉本刊记者,当时气氛非常禁锢,“国家乱成那个样子,大家在圈子里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当时圈子里最热门的书,有乔治奥威尔的《1984》、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在黄江南的记忆中,那时的讨论轻松愉快。“大家连玩带讨论问题,甚至还放个录音机在亭子里,大家一块跳舞。”
“***”结束之后,这些小圈子迅速活跃起来。提起当时的年轻人,李银河形容为:“简直就是群情激昂,在压抑了10年之后,有解放的感觉,觉得中国有希望了。就是这样一种欢欣鼓舞的气氛。”
此后,黄江南结识了《农民日报》的记者翁永曦,翁将他的一帮朋友也带进了这个圈子。这些年轻人约定时间举行了三次讨论会。未曾想,由于口口相传,讨论会的影响力日趋扩大。第一次只有三五十人,第二次上百人,第三次则达到近千人之众。许多人慕名而来,彼此相互不认识。黄江南形容这样的相逢和聚会为“英雄不问出处,只较武功。”
在讨论会上,黄江南对国民经济结构失调的分析勾起了李银河的兴趣:“我们当时认为,80年代初,中国可能要出现一次结构性的经济危机。这个很重要,但是咱们小老百姓议论也没用,要让领导同志知道。” 于是,她把***介绍给黄江南。
***与黄江南等人聊了一次就理解了他们的想法,黄江南对王称赞不已:“岐山这个人,他不学经济真是可惜了。他异常聪明,对经济知识的吸收和理解非常快,第一次听就懂”。***很快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交中央。
于是,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再加上***,一行四人在北京车公庄附近的市委党校租了一个房间,在里头关了几天,写出了报告。在这篇题为《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的报告中,四个年轻人“预测了1980年经济将要出现的衰退,分析了衰退产生的原因,并给出了应对危机的对策。”
为了这份报告,黄江南遍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经济数据,并得出结论:“58年、60年不是自然灾害”,而是“社会主义周期性的短缺危机”。如果不立即采取调整政策,那么过去的危机将有可能重现。
在报告中,***主要负责分析危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他是学历史的嘛,任何一个政策,都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黄江南说。
报告完成之后,***首先向***做了汇报。此后,姚又当面听取了几位年轻人的阐述,深感此事重要,于是将报告转给了***。***批示:“一个学工业的,一个学农业的,写了一份很好的报告。”
这份报告最终转到了时任***总理的***处,赵在中南海一个会议室接见了他们。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在见面之初,这样对他们说。实际上,这次对话发生于1979年底,当时翁永曦32岁,***31岁,黄江南29岁,年龄最小的朱嘉明28岁。
这次接见被后来人称为第一次“老青对话”,参与对话的,除了***和三位年轻人外(朱嘉明此时在安徽参加改革会议,不在北京),还有***负责经济工作的高层官员,包括***、薛暮桥、马洪等人。
黄江南做了主报告发言。“我们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很狂的。”多年之后,黄江南对《中国新时代》杂志的一次访谈中谈及此事,笑道:“我们当时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运行的规律。”
这些年轻人尝试着告诉国家的掌舵者们:社会主义是有经济危机的。当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认知。以至于时任统计局局长的薛暮桥,当场批判他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因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特有的”。
“他当时做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发言的宗旨就是说,你们年轻人,理论都没学好,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有经济危机”。在黄江南的回忆中,薛暮桥的发言最终被***打断了,“你甭说了,我们不是听你说,我们听年轻人说。”
黄江南认为:“过去的领导层里并没有反对市场经济的。***也好,***也好,发展市场经济是共识。只不过是进程的快慢问题,所谓稳健一点或激进一点。从骨子里面,没有一个人反对市场经济,也没有一个人要坚持计划经济。我们说的保守派还是改革派,其实应该说是稳健派和激进派。真正的不改革派是没有的,我从来没见过***说要反对改革。”
***那时就提出“困难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二十多年后,***在北京应对“非典”危机时,也是如此行事的。“要告诉大家,我们有困难,来了困难大家才不会怨恨。”
这次对话后不久,《人民日报》在1980年的元旦社论中,提到了“国民经济潜在危机”的警告,“这是中国第一次承认社会主义存在经济危机,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黄江南如是评价。 在那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年代,这次与中南海的直接对话,对当时的年轻人而言,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激励。
他们意识到,自己可以参与国家的变革。“应该说我们的意见当时中央听进去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国策上从大发展转为大调整。从发展政策变成危机对策。”
从此之后,四个年轻人就经常凑在一块讨论研究、写报告。从生态、农业,到经济体制改革,无所不谈。“因为中央领导都比较认可,凡是我们送的报告,他们都比较重视。所以这个报告就成了一个系列,就叫‘四签名’。后来也不知道谁就给改成‘四君子’了。”
“四君子”名气越来越大之后,各部部长不时会带着一些司长请他们去做报告、提建议。
1980年夏天,黄江南和***来到广州,时任广东***的任仲夷请他们为广东的经济改革出主意。于是二人着手开始调研工作,花了大量时间与省政府各个部门进行座谈,并走访各县、市及农村。
“广东每个厅局的一把手带上各个处长,都来给我们汇报。我们当时给他们发提纲,就是问卷,让他们先做功课。做完功课他们来对着我们讲,我们就提问,一个个***。”
紧张的调研之后,两人开始着手起草报告。当时的广东正值盛夏,“我和岐山热得呀,那会儿也没有空调,就光着膀子趴在瓷砖地上,瓷砖地凉快点嘛。在小凳子上写,小凳子放在电扇底下,我们俩就趴那写。”
报告完成之后,任仲夷召集所有负责经济的***、副***和厅局级干部至省委招待所开会,由黄江南和***对报告进行说明介绍。
“我们提出要重点依靠香港这个窗口,引进管理和技术,发展外贸型的经济结构。七山一水二分田嘛,广东省农业要以发展出口型产品的农作物作为方向。”
后来广东省的发展进程,与这份报告基本吻合。但在这次会议上,***和黄江南还是受到了尖锐的质疑。“我们说广东粮食不用自给啊,不用以粮为纲啦,进口也行,内调也行。广东地少嘛,要改成为出口服务的,要提高它的价值。”
在民国时期,由于战乱和交通阻绝,广东省曾发生过惨烈的饥荒。饿殍遍地的景象给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广东省领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当时就有领导提出“以粮为纲绝对不能动”。会上,还有一些老干部对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投机倒把现象深恶痛绝。“有痛哭流涕的,老同志的意识形态不能接受。”
对此,***和黄江南提出了“改革污泥期”的概念。“改革首先要走出第一步,一开始肯定会有一些泥沙俱下的时候。莲花只有顶破那层污泥出来了,才能开出秀丽的花朵。要是想从一开始就干干净净的话,那改革就没法搞。这个成本我们要允许,不能因为有这些我们就不动了,就不改了。不干净我们也要改。”
在1984年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主要停留在农村,涉及城市的改革相对较少。
“***”结束之后,一些知识青年对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在成功举办了几次讨论会之后,为了更好地研究改革问题,年轻人们筹划着成立一个机构。“大家一合计,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黄江南回忆。
当时农发组的成员以学生为主,其中包括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以及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作为一个由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机构,农发组还得到了两位中共高层人士的支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一位支持者是邓力群,另一位则是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两人亲自参加了农发组的成立大会,虽然所谓“大会”也不过只有三四十个回城知青。
经过邓力群与国家计委的沟通,农发组被挂靠在社科院农经所,经费则由农委发放。
1981年,农发组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开始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改变了中国,文件中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自此合法化,人民公社在政策层面被瓦解了。
此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和***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套班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原有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则被撤销了。
农研室由于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又被习惯地称为“九号院”。
1982年,由于杜润生的赏识,***被借调到农研室。他在九号院一呆就是7年。
九号院里曾流传着一个调侃“四君子”的顺口溜:“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的腿。”黄江南对这一调侃并不以为然。在他的记忆中,每当需要打印文件,或者送报告,***就主动跑腿。“他经常说‘这事我去’。只不过是不摆架子,小事他也干。不能因为这个就说这是‘腿’。这都是外面人调侃的说法。”
“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是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翁永曦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回忆,这辆引人注目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在当时给了***很大的帮助。
***在农研室的工作主要是安排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赵树凯当时在农研室任办公室秘书,在他的印象中,***“广泛交往”并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先是担任联络室成果处处长,很快又被提拔为该室的副主任。
《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记载了张少杰的回忆,农研室设立联络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保持与农发组的沟通,安排农发组的年轻人进行一些农村调研。“农研室有什么项目,我们就接过来,然后拉上一帮同学一起做。
我们那时没事就跑到***的办公室,问他最近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就会告诉我们,比如最近农村有这么一些事,你找几个人跑一趟怎么样?杜老最近要抓一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你们去调查一下吧,如此等等。” 在农研室的这些年里,***的办公室是年轻人聚会、讨论的重要场所。除了农研室的工作外,当时***还积极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运动。当时广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就有***的身影。
“当时刚刚开放,国外很多科学前沿,大家并不知道。”黄江南告诉记者,《走向未来》丛书的诞生就是为了“把全世界人文科学的前沿,用简单明了的方式,介绍给国内的青年。” 这套丛书致力于普及西方先进理念,其编委和原创书目的作者,大多是当时国内优秀的知识分子。
丛书上市之后,各地纷纷抢购,不断再版。“这套丛书已经是现代中国人精神史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朱晓阳这样评价,“这是那个时期中国自由思想界的象征和中坚,其地位有些如《新青年》之于五四时代的人。”
1986年,农村发展所成立,***出任所长。他依旧嗜书如命,喜欢给朋友们开书单。他当时推荐的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从明治时期日本打开国门、致力维新说起,一直叙述至二战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日本,并创造经济奇迹的整个过程。
据当时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所述,“读《激荡的百年史》,就是要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应该避免。改革有了成就后,还会有危险,会遇到崩溃、战争,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前瞻性的问题。”
“他是在引导大家。”王振耀说,“他跟我们一块儿学,听我们每个人发言。他一般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和大家针锋相对,而是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并不拘泥于改革与保守的标签,“而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
在王振耀看来,在***手下工作非常舒服:“发展所里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一篇署他的名字,他参与讨论、起草,但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现在有些领导写文章愿意署名,领导一署名,底下人怎么署?领导署在最前面,那些写得多的人署在他后面?***有他的领导方式,他不署名,反而大家好署名。他很自觉,(各方面问题)他都给你考虑到了。可能外面人看来,***很凶,很狠,但我们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很舒服。”
***以自己独特的工作风格和组织协调能力,带领着发展所的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思考。并把他们的主意向杜润生汇报,落实到农村的改革中。“他知道你思想的价值。”王振耀感慨道。“他从那时候就不愿意说一些套话,一直到他当***以后,还是讲话不打稿。”
***处事的特别之处,还可从另一件小事中窥一二。有一次,***和黄江南一起到河南省某县,县里的领导招待他们。河南省有“灌酒”的风气,餐桌上,该县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
“要一般人就说起来起来,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这种方式胁迫,他就不屑一顾。他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黄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颇感惊奇。“***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
如此场面让黄江南倍觉尴尬,因此他主动提出替***饮下此杯。***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不买账,你愿意跪就跪着,我理都不理,我不但不喝,我也不劝你起来。”黄江南说,“他经常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处理方法,我想一百个人里都不会有一个人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