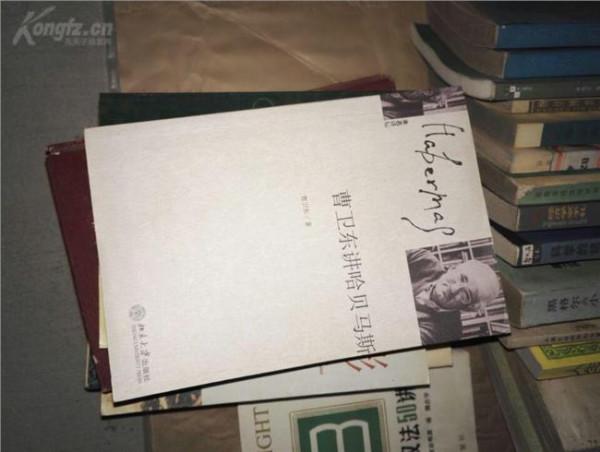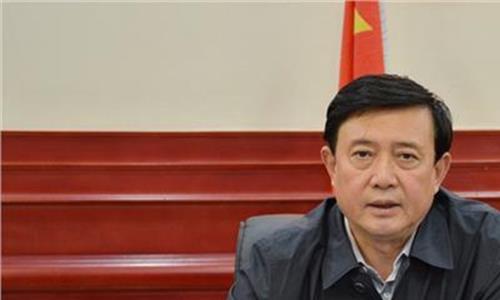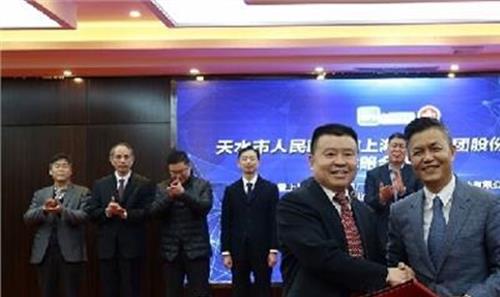曹卫东哈贝马斯 曹卫东:哈贝马斯在汉语世界的历史效果
到了20世纪80、90年代之交,哈贝马斯研究在汉语世界形成了第一个高潮。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对哈贝马斯作了较为系统的译介:《交往与社会进化》、《交往行为理论》等重要著作被收录其中。
丛书还推 出了中国学者对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思想的研究专著[6]。其他一些学术刊物,如《国外社会科学》和《哲学译丛》也纷纷展开对哈贝马斯的翻译和介绍。也有学者开始 尝试从伦理学的角度对哈贝马斯进行探讨,如薛华的《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7] 综观这一时期对哈贝马斯的介绍和研究,我们不难看出,主要还是局限于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出发,强调哈贝马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尚未形成对哈 贝马斯思想的全面认识和总体把握。
换言之,此时的中国学者对哈贝马斯研究的着眼点还在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最新发展,他们眼中的哈贝马斯只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的法兰克福学派一员,其理论也只是被简单地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一种新 近发展而已。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汉语世界对哈贝马斯研究的热潮出现回落,研究水平也没有什么新的起色。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政治氛围的改善,汉语学界重新燃起了对哈贝马斯的强烈兴趣。
大批学者在不同刊物上发表文章介绍和讨论哈贝马斯的不同思想概念。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哈贝马斯的著作开始大面积地翻译出版:1999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推出了三部主要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和《认识与兴趣》。
2001年4-5月,哈贝马斯应邀访问中国,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做了系列演讲,激起了“哈贝马斯热”,并使汉语学界注意到了哈贝马斯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维度:话语政治概念。
为了顺应这股热潮,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推出了“哈贝马斯文集”(包括《合法 化危机》、《包容他者》、《后民族结构》、《交往行为理论》等)。其他出版社也不甘示弱,陆续推出了哈贝马斯的部分代表著作,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理论与实践》;译林出版社出版了《后形而上学思想》、《现代性的 哲学话语》等。
引人注目的还有一批哈贝马斯的对话录,如《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作为未来的过去??与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对话》、《理解的界限? ?利奥塔与哈贝马斯的精神对话》等。
为了进一步推动哈贝马斯著作在汉语世界的传播和接受,一些外国学者撰写的传记著作和研究著作也被引进了过来,如德国学者霍尔斯特的《哈贝马斯传》;英国学者奥斯维特的《哈贝马斯传》、日本学者中冈成文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和美国学者欧 文?豪的《哈贝马斯》等;[8]与此同时,许多中国学者也出版了风格不同的传记类或专题类的研究著作,如余灵灵的《哈贝马斯传》[9]、曹卫东的《交往理性与诗学话语》[10]、章国锋的《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解读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11]、郑召利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12]和龚群的《道德乌托邦的重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13]等。
把汉语学界的两次哈贝马斯热潮进行比较,很容易就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首先,接受动机有了显著的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汉语学界不再把哈贝马斯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之内,相关研究也不再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的角 度出发,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哈贝马斯自身理论的独创性和丰富性。
其次,对哈贝马斯著作的翻译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被介绍过来的哈贝马斯著作主要是转译自英文,译文质量也难如人意,错误可以说是比较多的;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翻译过来的哈贝马斯著作基本都是直接译自德文,加上一些专业研究者投身到翻译哈贝马斯的事业当中,这就使得翻译质量有了较好的保障。
最后,对哈贝马斯的研 究水平也有了不小的提高。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哈贝马斯研究基本还停留在介绍和评述水平上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关研究已经大大拓宽了视角,深化了学理,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通过粗略回顾汉语学界对哈贝马斯的接受过程,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具有一种其他著作所无法比拟的表征作用,因为这既是第一部有了较为可靠译本的哈贝马斯著作,也是第一部在汉语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并被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 的哈贝马斯著作。
众所周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哈贝马斯的教授资格论文,出版于1961年,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便在欧美学界,在198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英文译本以前,也同样如此。但自1989年该书再版起,即在原书德文版出版近30年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注目,引发了一场关于“公” 和“私”的大讨论。
》[17]等。 然而,也就在这个时期,如何翻译“@①ffentlichkeit”一词在汉语学界还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形成了小小的学术论争。有学者认为,“@①ffentlichkeit”应翻译成“公共领域”,也有学者认为,“@①ffentlichkeit”应翻译为“公共论域”,还有的认为应当翻译成“公共空间”,或干脆译为“论域”。
作为该书的主要译者之一,经过认真思考,笔者本人决定取“公共领域”而舍弃其他。
为了论证自己的译法,笔者曾撰文指 出,哈贝马斯是在思想和社会两个层面上使用这个词的。思想层面上的“@①ffentlichkeit”可以翻译成“公共性”,而社会层面上的“@①ffentlichkeit”则应当翻译为“公共领域”: 虽说哈贝马斯在该书中主要是在思想层面上做意识形态批判,但鉴于他是从(资产阶级 )社会变迁角度入手,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①ffentlichkeit”加以提炼和抽象,因此,我个人主张,书名还是译成《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好,而不能叫做《公共性的结构转型》。
[18] 随着“公共领域”概念被汉语学界的广泛认可和接受,汉语学界涌现了一大批利用“ 公共领域”概念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涉及传媒、历史、法律、社会、政治乃至教育等众多领域,许多硕士生和博士生也纷纷以“公共领域”作为论文选题和研究对象,取得 了不错的研究成果,在历史研究和传媒研究领域更是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和独特的研究视角。
二 “公共领域”概念在哈贝马斯那里,是指在17世纪后期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开始出现的所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产生于私人领域和贵族的代表性公共领域的明确界分。按照哈贝马斯自己的说法,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商品流通和信息交换 是“公共领域”产生的前提,“私有化的经济活动必须以依靠公众指导和监督而不断扩大的商品交换为准绳”[19]。
其外在的显著特征,则是私人在阅读日报等传播媒介时形成了一个开放并富有弹性的交往网络,然后通过私人社团或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 会、宗教社团这类机构,自发聚集在一起。
剧院、咖啡馆、沙龙等公共空间为他们的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 这些早期的公共领域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并且在话题方面……聚焦点由艺术和文艺转到了政治。
这种联系和交往网络最终成了处在市场经济和行政国家“之间”或“ 之外”、但与两者“相关”的某种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
[20]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已经萌芽,而且随着政治危机意识和民族危机意识的加剧,传统的书院、知识分子结成的社团和新兴的报纸都成了人们发表自己对时局看法的重要场所,并且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初步具有了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的一些特征。
因 而,美国汉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学者,如罗威廉和兰金等,运用“公共领域”概念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如罗威廉对汉口的个案研究,兰金对中国近代士绅阶层地位的研究。
他们认为,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具有走向现代化的潜质 和活力,已经初步形成了“公共领域”的基本形态。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汉学界就“公共领域”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
发难者以魏斐德和黄宗智为代表,他们二人都认为,“公共领域”概念很难直接应用到中国身上。黄宗智在其《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 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21]一文中首先梳理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的不同类型,进而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的历史特定性太强,难以真正适用于中国。
但是,当他进一步深入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本身时,他发现这一概念具有二重性:“ (公共领域)占据着两种不同的区域”??一方面根据国家、公共领域、社会的三分法, “公共领域”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张力的区域”;另一方面,根据国家与社会的二 元对立,“公共领域”仅仅成了(市民)社会在反对专制国家的民主进程中的一种扩展。
哈贝马斯关注的重点显然在于后一种“公共领域”,在黄宗智看来,如果将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概念应用于中国,则难免会发生错误与混淆,因为中国社会压根就没有形成与国家的实质对立。
不过,哈贝马斯本人也很少关注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随两者变化而变化的公共领域这一较为复杂的观念,由此,黄宗智指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概念蕴涵着适用于中国的内涵。为了确切地把握这一居间区域而又避免在使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 ”概念时出现误用与混淆,黄宗智建议代之以“第三领域”概念。
在中国,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个第三领域,它居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受到二者合力的影响,但具有“超出国家与社会之影响的自身特性和自身逻辑”。
“第三领域”概念的运用,实际上相当于将“ 公共领域”从市民社会的束缚中剥离了出来,赋予了其独立存在的可能性。通过这一概念,就不会再纠缠于论证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具有了西方式的市民社会的特征,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客观事实,即在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早就有了一股异质力量的兴起,并 遵循着自己的成长规律在不断发展向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