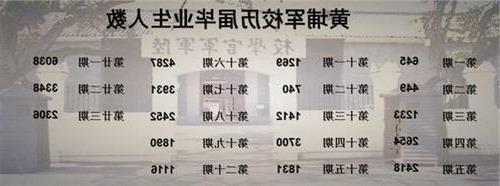唐师曾父亲 唐师曾:父亲疏化阵天线节转
严格地说,我没有叫过他们,没有象别的女孩子一样嘹亮地、全心全意地、带着全部的爱与信赖大声地喊过“爸爸”——对生父可能喊过,但他离开的时候我还不满三岁,从小小的、细嫩的喉咙里呼出的“爸爸”二字,对他说来或许很惬意,但对我说来可能完全是无意义的喃喃儿语。所以,严格地说,我从没有叫过他们。
元帅,我原是遵奉着当时流行的风习,喊过他“叶爸爸”的。但大约在我10岁的时候,他听烦了:“爸爸就是爸爸,什么叶不叶的。”从此,我也就随着他的亲生孩子一般喊爸爸了。当然,总是在不得不叫的时候,才吞着声音含含糊糊地喊一声。
而当我已成年,知道再喊他“爸爸”,不但意味着某种优势,且在优势之余又有了点沾光的嫌疑的时候,我基本就不再喊,而以“委员长”或“副”代之。到了他已经去世一周年,我写悼念文章时,则只呼以“叶伯伯”,虽然我一次也没有这样叫过他。
对我的继父,我是很隔膜的。做小姑娘的时候,曾被他领着玩过,并不知那时他和母亲的关系。待他正式与母亲结为一家,我已是高中女学生。我一直自己去爱他、尊重他,疏化阵天线但直到他离世,我们,他的亲生的与非亲生的孩子们,甚至包括我的母亲,对他都并不了解——直到我开始写作,开始细细揣摩他们这一代人,这些抱着纯真的理想,于30年代投身“”的中国知识人。
但他对我的了解显然要早得多——当然是出于只有他那类人才具有的极单纯的判断。他离世前对母亲说:“小庆⑴有一颗金子的心……。”那时我正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采访,这是在我已经无法回应他的时候,妈妈才告诉我的。
我的公爹是我在里的时候离世的。他一反中内知识多年养就的克制,在医院对他报了病危之后,提出一定要见我一面。这在任何时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那时是秦城的“未决犯”。但他以一名濒死的人的,固执地一再请求。这次,居然胜利了——他几乎输了一生,却赢了这最后的一次。怎么回事?要知道,他的职位并不高,也不具种种吓人的“海外关系”,更没有托门子。或许,一种的人类同情心终于战胜了?
在医院部的和方的监押下,我来到他弥留的床边。我握着他那已经瘦得变得差不多透明的手,不再儿媳与公爹间礼数的距离,把它贴到我满是泪水的脸上。我仍旧喊不出“爸爸”二字,只依着我的孩子的辈份叫他:
我的公爹没有理会我的泪水,我觉得他甚至没有看我,但他开口说话了,微弱、断续却非常清晰,清晰到使得拥在他那间病室的每一个人:奶奶、我的丈夫、医生、、医院部门的人、的人、秦城跟来的人,都听见了——
那时的恐怖与压抑一点也没有减轻。他开口说话了,他拼出最后的一点力气把我叫来就为跟我说这最后的一句话。我感到一种父爱的热潮向我涌来,感受到一个幼弱的女孩子所能得到的全部的爱:可依凭、可信赖、可以毫无地沉浸其中的庄严的父爱。
我的从无做官愿望的这一特质可能就来自他——如果爱憎与判断力也能遗传的话。他是在1919年因和陈独秀通信,而后进了这名总办的渔阳里俄语专修馆,并于1921年派往苏联,成为莫斯科东方大学第一期的“党的”。但是,直到20年之后接受了那么艰巨与的任务⑵,并且面临早已预料的时,他在也没有任何职务。
他是一个聪明过人的人。据零星得到的材料,他中学读的是学校,有很好的英文底子。疏化阵天线从苏联回来之后,俄文已十分流利。在黄埔军校听过他作翻译的人讲了这样一个“可惊”的事实:他一个人在台上,先将鲍罗廷的俄文译成国语,又将国语译成广东官话,然后再照样译过去。
据李菊生⑶说,当他自己在马来西亚做时,父亲是当地地下的负责人,想来他是懂马来文的了。据妈妈说,在重庆时,一批海南同志来找他,他与他们一直咕哝着她一个字也听不懂的一种话——想来是海南方言了。
最特别的是他与我的外祖父的交往。老先生是清末翰林,的保光绪派,出于联姻名门之固癖而把我的母亲嫁到湖南曾家。无奈母亲那时思想太新,自己逃婚到日本,数年后又携这样一名自己“”上的女婿归省,外祖父的怒气可想而知。但事情后来竟朝着人们预料的发展,这保皇老人不但接纳了他,居然还有一首七律写到他们翁婿间的关系:
亲友们吟咏玩味之余,一直以为这是马列主义的伟力:我的父亲以主义征服了的岳丈。直到去年,当父亲的传记作者召集家族座谈会广泛征集信息时,我才知道,原来他还懂藏文。外公之所以对他认可,是因为他能直接阅读藏经——老人只认藏,其他所有汉传佛教高僧在他眼里都是野。
在重庆遇到妈妈的时候,他已经40岁,朋友之间有“王老五”之称。他们闪电般地结合,,也就是说,党需要他以名人女婿的身份到北平去住家应酬,搜集情报,恐怕是第一目的。那时候的人,大概将看得很轻。翻看他们留下来的只言片语,我的感觉,在接受这个安排定了的命运的时候,他好象是乐呵呵的。1941年元旦,他们在著名的曾家岩50号行婚礼。在那方辗转保存下来的喜幛上,有一首“新郎自题”,向他美满婚姻的牵线人致谢:
喜宴结束了,他们结为夫妻。到了年底,带着婴儿(我)北上赴死。在他们的情感生活里,老实讲,妈妈是很委屈的。父亲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没有心思顾到妻儿。这一切,当然,同为CP的母亲都以“”的名义谅解了。在他们已经落到日本人手里,已经不可免地面临他们最后的时刻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
那时,他和妈妈分别关在同一个筒子最头上的和最后一间。牢饭,发霉的杂米和臭了的菜叶,对孕妇也一样。一次,递过碗来,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又指指那饭。妈妈接过去,急急扒了几口,发现碗底下埋着两块肥肉。
最后一次,压在饭下边的,不是肉了,而是一张字条。虽然都在狱中,他似乎比妈妈先一步知道日寇的结局,同时也预感到了自己的。他写到了理想,写到了胜利,他还写到了——这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己和家庭,向党提出属于他个人的要求:“请转告组织,把我们的孩子送到苏联学习。”
20年后,当我已经大学毕业,妈妈在偶然之间提起这一节的时候,我不禁黯然神伤。我的无畏献身的父亲,在这里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把他的理想看得太了。他到苏联的时候,那里正是“饿乡”,他显然不是想让他的孩子去享庸福。他把那方土地看成他美丽理想的寄托。然而,他不知道,如果想在一个有党支部、有常委、有局扩大会议这种种鸟事的地方实现平等、、无剥削、无倾轧,要经过多少污泥浊水、殊死⑷。
他也许以自己的心去掂量一名烈士临终的托付;但他忘了,烈士之被活人想起来,只在那活人觉得需要张扬他的,以使更多的人为他们正享用的事业献身的时候。当然人也许不这么势利,也会有人,包括相当志得意满的人偶尔也念念旧情,但他不应忽略的是,必须立足于不作如是想,才不至受到——当然,在他的愿望被冷冷的时候⑹,人已经死了,已无所谓不;而且,他的孩子虽然未能如他所愿去苏联,也都受到了高等教育;再有,无论从真正的学识人品,还是社会的承认,他的三个没什么幸福童年可言的孩子,除了靠自己一点一滴扎实努力之外没别的出,最后也都不逊于那些有资格去苏联受教育的同龄人。
这,想来,可以稍稍慰他于九泉之下了。
因为从事的工作属超级机密的缘故吧,虽然我们姐弟作为烈士子女由“组织”扶养到十八。














![唐绍仪之女 [唐绍仪简介]唐绍仪的后代近况如何 顾维钧曾是他的女婿](https://pic.bilezu.com/upload/6/b8/6b8d45f45203a95f19d4eda72d03ea47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