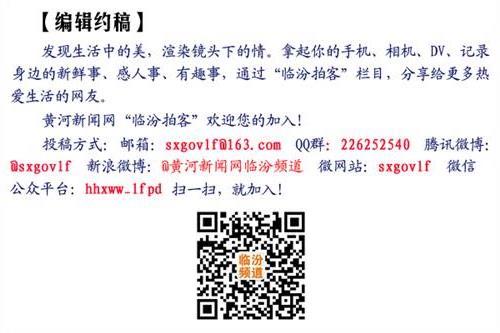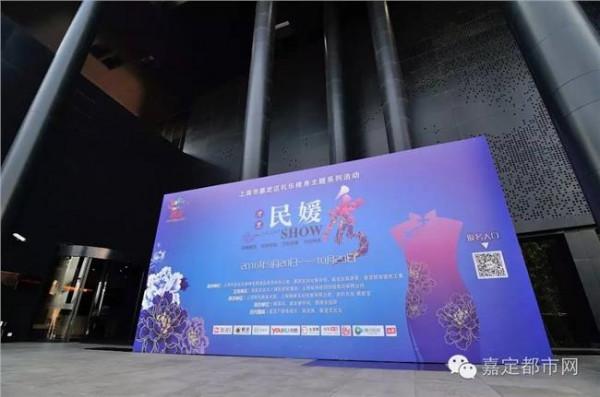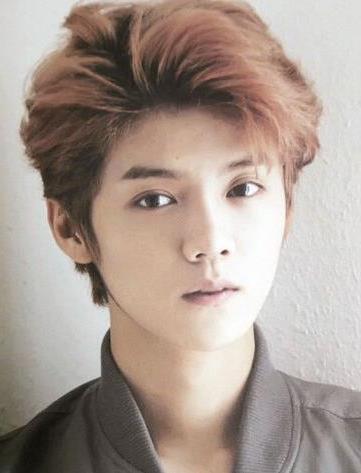春节年年有今年特冷清 回忆老济南上世纪的春节情景

每年,当一家人围坐在年夜饭的餐桌前,常常会回忆起往年的年货,它是过年的味道里最重要的一部分。说起年货,或许有的人会想起一锅热气腾腾的豆沙包;有的人会想起攥着副食本排队买带鱼的情景;有的人会想起摆满鸡鸭鱼肉虾的年夜饭餐桌。有的人甚至还会想起穿着白边布鞋和军绿衣裤的那一年,买了彩电的那一年,揣上手机的那一年,搬进新居的那一年和换了汽车的那一年。

年货是中国人过春节的重要符号。置办年货,蕴含着中国人辞旧迎新的心愿。在置办年货过程中,在期盼着新年的喜庆心态中,新的一年也就悄然而至了。一年一年,往复如此。

迈进腊月门儿,过年的话题就开始热闹起来了。一件件年货,一份份平安,一桌桌美食,不同的年代,相同的团圆。

年年过春节,岁岁办年货。无论哪个时代,年货都是让春节过得喜庆热闹的必需品。年货是中国人复杂感情的融合与交织,略显琐碎的仪式里传递着脉脉温情。时光飞逝,伴随着时代变迁,从一个豆沙包到鸡鸭鱼肉样样俱全,年货也在悄然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眼下已经迈进了腊月的门槛,人们对于年货的记忆也开始纷至沓来。

孙志云老人出生于1935年,过了这个年坎儿就是81岁高龄。“现在的你到高楼林立的官扎营片区看看,一定很难想象80年前这个片区是啥样子。”孙志云老人说,官扎营片区位于火车站以北,天桥以西,当年是济南的“贫民区”,他就在这里出生和长大。从地理位置上看,官扎营位于市区北部,靠近漕运繁忙的小清河码头和贸易往来不绝的泺口市场,所以很多下苦力劳作挣钱养家的贫苦市民都住在这里,还有逃荒的,打工的,聚集在官扎营过着食物难以果腹的苦日子。

“那时候的生活太贫寒了,贫苦到我自己都不愿再想起。”孙志云老人回忆说,不过人上了年纪,眼前发生的事情常常回头就忘,儿时的苦难生活却是记忆犹新。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爷爷是在铁路上“跑火车”的工人。上世纪30年代末,日本人统治济南时,火车站被日本人占领,很多不愿给日本人工作的工人们纷纷“闹工潮”,爷爷也在这个潮流中放弃了工作。为了养活家人,爷爷就在天桥卖甜沫儿为生。直到现在,漫长的七十年过去了,孙志云还记得下半夜两三点钟,爷爷点着昏暗的小油灯磨豆子的场景。就靠着卖甜沫儿,爷爷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在一年到头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里,过年就成了吃点肉末、穿件新衣服的唯一盼头。孙志云老人说,那时候过年都盼着吃豆沙包,现在的孩子都不觉得豆沙包有啥稀罕的,在苦难的日子里过年吃个豆沙包却是一年中很奢侈的事情了。爷爷奶奶会把红小豆蒸熟,再加了糖搅拌,逐渐成糊状的豆沙泥就在筷子一圈圈的转动下越来越黏。后来日子好了,孙志云老人又买豆沙包来吃,却怎么也吃不出儿时的味道。“手工搅拌的和机器搅拌的味道怎么能一样呢。”也许是如今花样繁多的食物刁钻了人们的味蕾吧。
贫困人家的孩子最羡慕的就是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家能买个猪头了;或者是能切上一两斤肉包个水饺,别提多香了。想要买件新衣服的小孩子会把家里积累的垃圾卖一卖,像牙膏皮、骨头渣,都有人收,卖掉之后或许能换一双新鞋子。鞭炮也是过年时男孩子不可少的玩物,“只能一个个放,放上几个过过瘾罢了。”孙志云说,就是这样还舍不得买呢。
回想起这些浸透着战乱、饥饿和苦难的童年生活,孙志云老人感慨现在的日子是“换了人间”。

时隔五十年,今年63岁的老人高军还记得母亲当年为了备年货熬夜买猪大油的情景。每到离过年还有十几天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开始“忙年”,其中颇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准备过年用的油。那时候,凭着单位发的“油票”领来的油不够用,就要通过其他的方式获取食用油——比如买了肥猪肉自己炼油。排队买猪大油的人太多,为了能够多买上点肥肉,天还刚蒙蒙亮,母亲就起床顶着鱼肚白刚刚泛起的黎明,挎着篮子赶往万紫巷。这一路上,能遇到几个顺路的老姐妹,“去买猪油啊。”彼此打个招呼便一起匆忙往万紫巷赶,到了副食品专卖店才发现自己去得并不算早,已经有人早早地排在那里。往往排上两三个小时,才能买到一小块肥猪肉。

买上肥猪肉后拿回家,母亲就会把肥猪肉放到锅里,直接熬炼出猪油存放起来,以备过年的时候炖菜吃。猪油和植物油不一样,冷了就会凝固,做菜的时候用勺子盛起来的是一块黄白色的固体,放到锅里受热后逐渐融化,发出“嗞啦嗞啦”的声响。猪大油熬炼到最后还有油渣,母亲会把油渣剁碎了封存起来,包白菜水饺的时候添进去一些调馅儿,这样水饺吃起来格外香。

高军说,每年到了母亲天不亮去排队买猪大油的时候,就知道年快来了。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粮食减产,连日常的生活衣食保障都没有的情况下,也就没有了“忙年”的概念。靠天吃饭的那几年,甚至吃上了地瓜秧子或者树叶,能吃上几顿地瓜面的大包子就算是年下最好的食物。“地瓜面非常硬,包大包子很难黏住。要是白面的话轻轻一捏就黏在一起,地瓜面又黑又硬,特别费力气。”高军说,要是黏不好,出锅的时候大包子就“开了花”。即便如此,那时候能吃上这个已经算好的了。

韭菜水饺可算得上是数得着的“奢侈”食物。那时没有塑料大棚,菜非常稀罕,在济南,只有北园附近的菜农们用草席子盖着能种点韭菜,就算是手中有点余钱,买点韭菜还得找个熟人呢。三年自然灾害过去后,日子渐渐有了点起色。

让孩子们最高兴的是,年前的鱼票、鸡蛋票会比平时多一些,兴奋的孩子们会跟着大人去副食店领食物,回家的路上还能买几张年画贴一贴。“《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少剑波都是年画中常见的人物。”高军说,女孩子能买上几根红头绳,平时舍不得戴,过年前时常会拿出来看一看,非得等到过年时才早早起来扎在头上。

日子虽然仍然不富裕,不过家家户户能准备点油,买几张年画,在地窨子存点青菜当做年货。等到过年时,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个白菜油渣水饺,伴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贴上几张年画,就算是过年了。

在今年33岁的许平平记忆中,年货是炸得焦黄的萝卜肉丸子,是咬一口全是瘦肉的猪肉香肠,还有提前备好的鸡鸭鱼肉……总之,除了买上几挂红火火的鞭炮之外,几乎全是散发着香味的美食。

年货是需要特别拿出一天时间来专门去采购的。许平平小时候,家家户户日子已经越过越好,老百姓手中有了余钱,准备年货时就格外慷慨。每到过年前些天,她家所住的小镇上的集市就格外热闹,平时不怎么出摊儿的商贩们也早早在大街两旁摆满了过年的商品。有铺地而放的春联,有大大小小的中国结,有各种各样的烟花炮竹,有琳琅满目的糖果糕点等等。菜市场最是热闹非凡,小贩们不停地吆喝着菜名,买菜的不停地讨价还价。走在街上置办年货的男女老少们也都是喜气洋洋的。

那时候,许平平跟着母亲推着自行车,在拥挤的街道上挤来挤去,看到家里缺少的年货,便挤上前去口若悬河地讲价,然后再大把大把地把年货往家里送,有时一天赶集都要赶上两三趟。鱼、鸡、蔬菜、瓜子花生、糖果……满满地系在自行车把上,沉重的年货压得自行车把都不好扶正。最重要的是买上一挂猪头,回到家里父亲再把猪头分切开来,留着春节吃。总之,不把春节期间需要的年货买齐,“年集”是赶不完的。

年货的食材买齐了,家里的老人就开始着手加工。许平平说,过了小年,奶奶会连续好几天蒸馒头、炸藕合、做腊肠、包饺子,这也是孩子们最盼望的时候。奶奶会起个大早,把买来的东西洗净切碎,然后烧开油锅,一盆盆炸透,看着勾芡过后的小白块在油锅里翻腾,由白变黄,由生及熟,空气中弥漫着油的芳香,许平平和幼小的妹妹看得好不兴奋。浓浓诱人的飘在厨房的香味总是吸引着她,于是偷偷地把刚刚炸好还冒着热气的丸子放到嘴里,烫得她嘴巴里发出“嘶哈嘶哈”的声音,丸子在舌头上打好几个滚儿才咽下去。俗话说“正月不动刀”,在春节过去的许多天里,家里都不用再上街买吃食,靠着年货可以吃上十天半个月。如今,奶奶已经离世,再也吃不到奶奶在厨房忙活大半天端出的美食了,想起童年的年货,许平平脑海多半充斥着奶奶忙活的身影和老家厨房炊烟袅袅的温馨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