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高行健 第一位中国文学诺奖之“高行健现象”:文学与政治纠缠不清
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全世界的华文媒体引起热烈辩论。辩论的重点在于:把这个荣誉颁给高行健,到底有没有政治意义?
本文从高行健获奖的反应,分析这个问题。作者发现"高行健现象"至少涉及九种虽然相互关联但又各不相同的政治。
对于华文世界来说,千禧年最重大的文化事件,无疑是旅居法国的华文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并且引发广泛的争议甚至恶言相向。在高度政治化的华文世界中,发生这样的"高行健现象"并不令人意外。这一事件凸现出政治的渗透力十分强大,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关于文学与政治分开的主张,无疑是良好的愿望,但可惜在现实世界中却无法落实。需要指出的是,文学政治化的推手,绝非来自特定的一方。
笔者不是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对于高行健及其文学作品以及其获奖是否当之无愧,没有资格评论。但是,作为政治科学家,尝试厘清一下"高行健现象"所凸现的政治意涵,尚属份内。通过对于在网络世界众多文字的解读,笔者发现"高行健现象"至少涉及九种虽然相互关联但又各不相同的政治。
首先当然是诺贝尔文学奖政治性问题。高行健获奖之后,海内外最为普遍的声音,便是质疑诺贝尔文学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政治奖。
媒体的政治化
针对这一质疑,评审委员会当然严辞否认政治因素渗入评奖的考量。但是,其《新闻公报》仅仅提到高行健的三部作品,而在评价《一个人的圣经》和《逃亡》时,通篇表述的是作品的政治内涵。其原文如下:"小说的核心是对中国通常称为文化大革命的令人恐怖的疯狂的清算。
作者以毫不留情的真诚笔触详细介绍了自己在文革中先后作为造反派、受迫害者和旁观者的经验。他的叙述本来可能成为异议人士的道德代表,但他拒绝这个角色,无意当一个救世主。他的文学创作没有任何一种媚俗,甚至对善意也如此。他的剧作《逃亡》不但让当权者恼怒,也曾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引起同样程度的非议。"
第二,媒体的政治化。可以说,几乎所有媒体,在处理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新闻时,都遵循了"政治第一,文学第二"的原则。
绝大多数媒体,在尚未了解高行健的文学成就之前,先对其政治立场了如指掌,并且迅速加以传播。由此,人们很快得知,高行健是一个流亡作家,曾经强烈谴责镇压天安门运动的中共政权,并且发誓只要中国仍在极权统治下,在有生之年绝不回到中国。
美联社记者在采访高行健时,主要关心他是否会利用这一新增的荣誉,来发起一个反对中国政府的论坛。加拿大的《国家邮报》甚至发表社论,号召人们以高行健为榜样,用文学艺术来暴露中共政权暴力的本质。
中国大陆媒体自然了解高行健的政治倾向,于是对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重大文化事件采取冷处理。与此相对照,台湾媒体则趋之若鹜,并且不断重复这样一个"事实":所有华人都对高行健获奖无不感到荣耀与骄傲,唯独中共如何如何。但真正的事实是,在除了中共以外的华人中,并非所有人都为高行健获奖感到荣耀和骄傲。
第三,身分政治学。同样的观点由不同身分的人来表达,便产生不同的政治效应。
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在第二天评论说:"中国有许多举世瞩目的优秀作品和文学家,诺贝尔奖评委会对此并不了解。看来,诺贝尔文学奖此举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
西方媒体也有质疑
中国作家协会的这番表态,激起海内外众多人士的强烈不满。香港有媒体把高行健获奖称为"中国人的光荣",而中国作协的表态则为"中国人的悲哀"。
但是部分海外华文媒体、西方媒体也发出过这一质疑。例如,德国文学评论家马塞尔·赖希—拉尼奇(Marcel Reich-Ranicki)在电视节目《文学四重奏》中批评说:"我不反对中国人得诺贝尔文学奖,但对于评审委员会拿它当政治手段来滥用却无法苟同,这应该不属于文学奖的功能。"看来,说什么不重要,关键在于什么人在什么场合说。
第四,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国作协的态度引发激烈反弹,当然同这一组织的官方性有关。中国官方对于这一文化事件的处理,引发人们高度关注文学与政治在中国的关系。
持温和立场的人们呼吁中国官方持开放的立场,并且调整文化政策,让文学艺术有更大的自由表达的空间。对于一向视中国为极权主义炼狱的人们来说,中共官方组织的这番作为,又为他们的批判提供了千载难逢的火药。海外中外文媒体常常援引高行健本人的形容,宣称在中共极权统治下,"恐怖无所不在,从劳改营到日常生活,人的天良都被扼杀了。"
然而,在争议高峰过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去年11月5至10日在广东肇庆召开第十一届年会,与会者普遍高度评价了高行健的《灵山》和《一个人的圣经》,赞扬了他坚持不做政治工具的姿态,批评中国作协的政治化表态,并且有人强烈批判了政治权力对于文学批评的压制。
生活在海外自由世界的人们或许会担心,这些胆大妄为的批评者可能会面临无所不在的恐怖。
第五,不同政府反应的政治性。无论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何人,都同外交没有关系。但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却对高行健获奖发表与中国作协类似的负面评论。除此之外,中国政府机构(例如文化部)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华人社会的骄傲"
台湾总统陈水扁代表台湾政府和人民,向高行健获奖表示恭喜,并称这是华人社会的骄傲。台湾立法院的一些立委建议将瑞典皇家科学院对高行健的颂辞列入立法院的记录。有趣的是,当中国大陆的运动员获得奥运金牌时,台湾政府官员,还有众多媒体,并不视之为"华人社会的骄傲",也鲜有恭喜之辞。
法国总统和总理都向高行健表示祝贺。总理若斯潘在贺信中提到:"这不仅是对您辽阔的艺术天分的认可,也是对您的政治立场的承认。"
第六,华人与中国人的政治性。华人与中国人的关系,现在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政治论题。有关高行健获奖的争议,为这一争议添上了新的作料。
陈水扁认为高行健获奖是华人社会的骄傲。在他的词典里,华人与中国人绝对分属两个辞条。有趣的是,不少人认为高行健以法国人的身分获奖,并不是中国人的光荣。也有不少人认为,高行健获奖是他个人的光荣,与中国人无关,似乎也与华人无关。持这种看法的人中,最著名者是苏晓康和哈金。
著名文学史家夏志清表示,第一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由海外的中国作家获奖,与两岸无关,既不是大陆本土作家,也不是台湾作家,这是很公平的交易。看来,无论大陆还是台湾,似乎都有一些问题,不配同诺贝尔文学奖有缘。
高行健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得而知。在一个是否是中国人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的时代,人们最好不要向宣称讨厌一切政治的高行健提出这样的问题。
第七,迫害与流亡的政治性。海外华文媒体和西方媒体在介绍高行健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强调,高行健在中国受到迫害,因而被迫选择流亡。《纽约时报》在去年11月20日发表了一篇题为《追求自由而一夜成名》的文章,在解释高行健被迫选择流亡的原因时,该报援引高行健本人的回忆:在中国,任何文字都要为共产党歌功颂德,即使为儿童、少年写的读物也概莫例外;在那里,一切都被政治化。
有关高行健受迫害的说法
熟悉中国改革以来历史(特别是文学艺术史)的人都知道,高行健在历时不到百日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波及,被列入戏剧界精神污染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一经历,高行健自己在获奖后大而化之地说:"我的作品在大陆都被认为是有政治问题,全部被禁,我最后无法呆下去,才出来。逃,这是唯一的办法。"他的获奖致辞被一些人解读为对于他遭受中国官方迫害的控诉状。
有关高行健受到迫害的说法也受到人们的质疑。不少关于高行健生平的报道中说:高行健在中共最专制的文革时期入了党,还上了五年党校。著名的网上自由作家马悲鸣讥讽说,高行健在入党热时入党,出国热的87年出国,退党热时退党,避难热时宣布再不回到那个专制的祖国。
第八,出版检查制度的政治学。强调高行健受到中共的迫害因而流亡的所有文字,都会强调他的作品在中国大陆被禁止出版。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多数媒体对于这一重要的政治现象大多语焉不详,只是强调高行健的《灵山》,仅能在台湾、法国、澳州和瑞典出版。只有《纽约时报》的文章大胆地告诉西方的读者,高行健的全部作品自1985年以来在中国被禁。
然而,新加坡的一位高行健研究者和一些网上的文章澄清说,《高行健戏剧集》在1985年由大陆的群众出版社出版,印行3000册;《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1988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印行1000册。《灵山》的版权代理人、法国的Aube出版社曾经同大陆的出版社商谈该书的出版,但因权益问题未达成协议。
在高行健获奖前,他的书在中国大陆究竟是被禁止出版,还是出版社由于经济因素不愿意出版他的作品,还是一个谜。当然,在高行健获奖之后的政治化浪潮中,他的书在一定时期内肯定在中国大陆被禁止出版。
第九,文学水准、读者与权威的关系。高行健获奖造成"高行健现象",归根结底在于人们对于高行健文学水准的高低评价不一。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高行健得奖消息传播出来时,不少人所问的问题居然是:高行健是谁?甚至许多华文文学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尤其不了解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
高行健的作品是否"曲高",因为笔者不是文学行内人,不敢妄断,但是"和寡"却是一个事实。他的最重要作品《灵山》在台湾出版多年,销量仅为3400册。《灵山》译成英文,其译者陈顺妍博士费时两年,才使之在澳洲出版,而在全球最大英文文学市场美国和英国,居然没有出版社识货;其《一个人的圣经》华文版也销量有限。
我敢大胆假设,在台湾、香港、美国的众多大学,《灵山》都没有被列入文学(甚至当代华文文学)的必读书。许多作家、文学评论家在接受采访时尴尬地宣称没有读过《灵山》。网上有人尖刻地质问:为什么众多华文作为母语的人有眼无珠,要有待瑞典的专家来指点迷津。
很多人争辩说,《灵山》不畅销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因为文学水准不能用畅销书排行榜来衡量。但是,这一争辩依然没有解释如下的事实,即相当数量的专家和读者,在其作者获奖前,对这一被诺贝尔评审委员会誉为"无与伦比的罕见的文学杰作",居然视而不见,然后在其获奖后又争当这部"文学杰作"再发现的弄潮儿。
看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确对于文学品位和判断力具有某种宰制性。那么,它缘何拥有这种宰制性,的确有待我们加以政治经济文化学的全面分析。这种宰制性的意涵,究竟代表专家对大众的宰制,还是少数专家对多数专家的宰制,西方文化品味对中国民族文化品味的宰制,抑或欧洲人对非欧洲人的文化宰制,或许将来会成为文人雅士的谈资,甚至不少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课题。
"九"这个数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最"的含义。把"高行健现象"涉及的政治说到了"最"的层面,肯定会引发厌恶一切政治的高行健及其拥戴者的厌恶,还是到此打住为好。
·作者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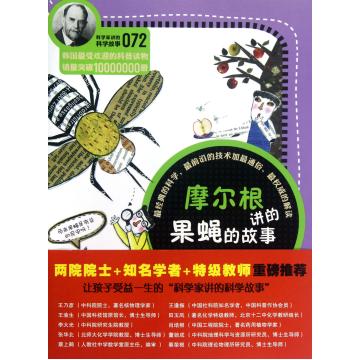

![>单霁翔故宫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故宫将坚持公益性第一位(图)[单霁翔]](https://pic.bilezu.com/upload/b/4a/b4a0795f233e88972a2c830b76ff4fb0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