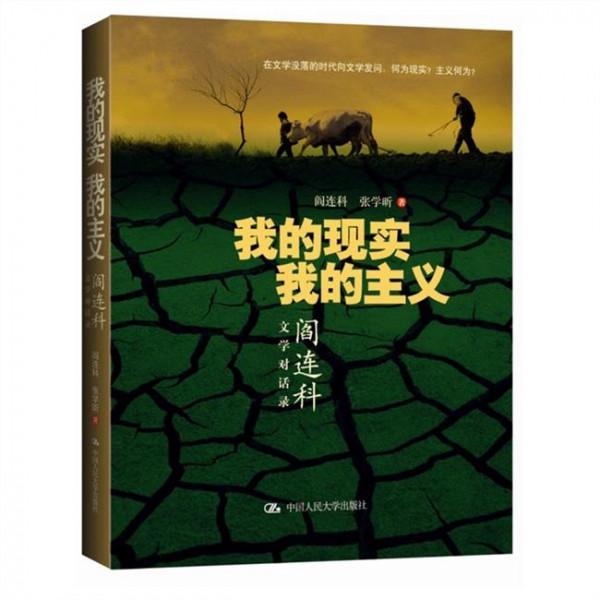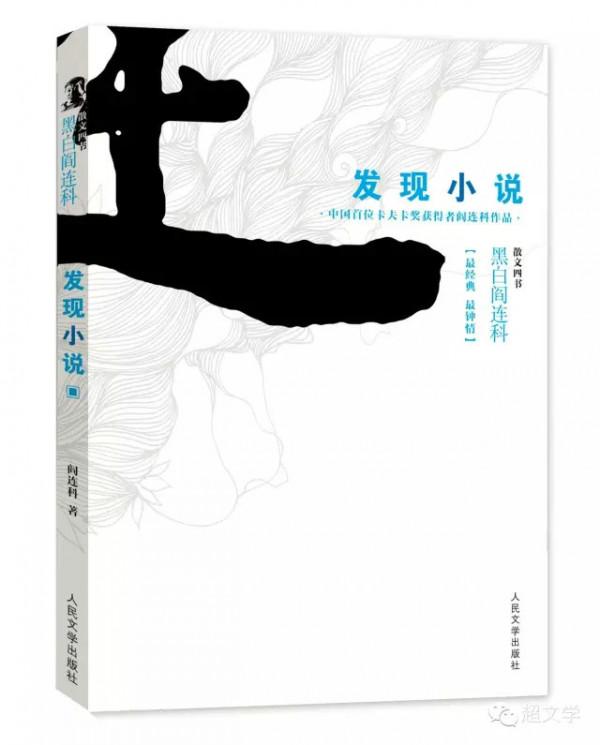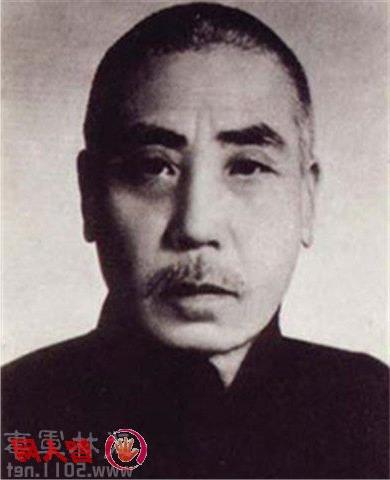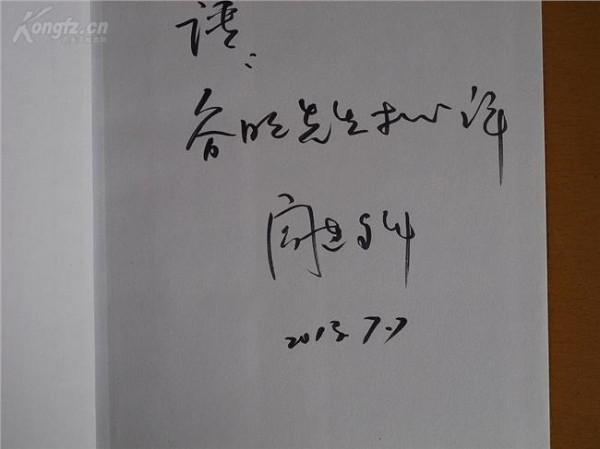阎连科简介 阎连科:不能踏步在简单的现实主义上
继2014年10月从捷克捧回第14届卡夫卡文学奖后,日前,阎连科又凭《受活》获得由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这也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有人说《受活》是魔幻现实主义,有人说是荒诞现实主义,阎连科却说这是“神实主义”作品。
2014年,阎连科在捷克。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小说《受活》的中文版
小说《受活》的日文版
现在,“获奖”这个词算是跟作家阎连科紧密联系上了。继20l4年l0月从捷克捧回第l4届卡夫卡文学奖后,日前,阎连科又凭《受活》获得由日本读者评选的Twitter文学奖,这也是亚洲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此前,阎连科曾先后入围法国费米娜奖、亚洲布克奖、西班牙塞万提斯奖等国际文学奖,但除获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外,大多空手而归。
阎连科因此自嘲,他在文学奖中从来都是“陪榜”的角色。如今,从卡夫卡文学奖再到Twitter文学奖,有人断言,阎连科是继莫言后,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谈及获奖,阎连科说,没想到《受活》在日本卖得如此好。去年底一上市,首印8000册销售一空,四个月之内再版三次,创造了中国作家作品在日销售的奇迹。他认为这一方面可能和获卡夫卡奖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作品中的想象力,“日本小说更日常化,也更人本化,想象力不太会像《受活》这么飞扬吧。”
《受活》是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背叛
发表于2003年的《受活》,讲述的是在混乱的历史和社会中,一个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把自己融入现代人类进程的社会边缘的乡村,在一个匪夷所思的县长带领下,经历了一段匪夷所思的“经典创业”的极致体验———用“受活庄”里上百个聋、哑、盲、瘸的残疾人组成“绝术团”巡回演出赚来的钱,在附近的魂魄山上建起了一座“列宁纪念堂”,并要去遥远的俄罗斯把列宁的遗体买回来安放在中国大地上,从而期冀以此实现中国乡民的天堂之梦。
著名评论家孟繁华评价《受活》时说,如果从故事本身来说,它仿佛是虚拟的、想象的,但那些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叙述,对表现那段历史来说,却达到了“神似”的效果,它比真实的历史还要“真实”,比纪实性的写作更给人以震撼。
在《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尤其在《受活》之后,外界冠以阎连科的作品许多标签,黑色幽默,魔幻现实主义者,是荒诞的,是现代的,是后现代的……阎连科发现,几乎所有的批评家乃至于媒体,在讨论自己的小说时,都给戴上另外一顶帽子,“比如有人说《受活》是中国的《百年孤独》,这是哪跟哪的事情?每一部小说出现时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不是你满意不满意这些帽子,而是这些东西确实和你的小说都没有联系。同时你会发现给你戴各种帽子的人,确实对你小说在简单化处理,对文学没有清晰理解。”
阎连科认为,他的作品从《日光流年》开始,就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摆脱,或者说是背叛了。“尤其是《受活》,有人说是魔幻现实主义,有人说是荒诞现实主义,我想都有道理,可都不太够。我自己的写作发生了变化,我把它理论化并提出了一个‘神实主义’概念。”
阎连科解释说,“神实主义”,就是摒弃固有的生活的表面逻辑,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而恰恰,它是精神上的真实。
基于今天中国的现实和文学,阎连科觉得,只有神实主义更可能达到现实主义的本质。“我提出‘神实主义’,有很多人赞成,很多人反对,我想反对的人大概就只看了‘神实主义’四个字。没有看过《发现小说》那本书,我想他看了《发现小说》,他反对的声音会弱一点。看完《发现小说》,他可能还不赞成‘神实主义’,但是他会理解一个作家为什么提出这个东西来。”
为什么要用神实主义写作
在“神实主义”之前,阎连科有一个和现实主义决裂的过程。如果说,《受活》篇首题词“现实主义———我的兄弟姐妹哦,请你离我再近些。现实主义———我的墓地哦,请你离我再远些”还隐约可见阎连科对现实主义的一种纠结感情,那么到了《四书》,他已经彻底背叛现实主义,说“我真想一刀杀了它们”!
“今天中国现实的荒诞和复杂,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我们的逻辑思维。基于这种情况,只有神实主义能够抵达。还有,传统的现实主义束缚了我们文学的发展,无法抵达现实的最深处。现实主义永远是伟大的,但在今天不是唯一的表达方式。”阎连科简单概括着为什么要用神实主义写作。而要探究其从现实主义到“神实主义”的深层转变,恐怕还要追溯到阎连科20ll年创作完成的随笔文论集《发现小说》。
在《发现小说》中,阎连科谈到了现实主义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控构现实主义”,即有控制的虚构;第二个层面是“世相现实主义”,像张爱玲、沈从文的一些写作,世相小说会分很多类,包括乡村世相、政治世相等;第三个层面是“生命现实主义”,比如鲁迅、托尔斯泰的小说;第四个层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灵魂现实主义”。
“当你把中国现实主义用你自己的认识很清楚地分出这四个层面时,你会发现,我们谈论的现实主义更多的是停留在第一、第二个层面。乃至鲁迅给我们开辟的第三个层面,我们就没有达到,更不要说我们有能力走到第四个层面,写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灵魂深层的东西。
”基于这样的认识,阎连科认为,今天中国的复杂性已经不单纯靠现实主义能够表达。“文学一定是要向前的,我们不能永远踏步在l9世纪简单的现实主义文学上。现实主义恰恰在束缚着我们的写作,所以我说要和现实主义一刀两断。而‘神实主义’,可以关注到我们看不见的真实,被真实掩盖的真实,这些真实不仅包括社会现实,也包括人的内心和灵魂。”
带着“紧张关系”一路走来
一直以来,伴随阎连科的,有三个关键词:成功,争议和误读。但他都淡然处之,专注于内心,“按照自己对文学的认识去写,完全不管别人说什么,别的和我都没关系,我写出什么才有关系”。人性的出路与困难在哪里?阎连科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在写。“你的内心有多么深刻复杂,你就朝那个方向走。人心最复杂的地方,没有美丑之分。在人心最黑暗的地方,发现了一丝光明存在,你把它表达出来,我想这就是文字最深刻、最伟大的地方。”
少年时候,阎连科说自己崇拜三样东西:城市、权力、健康。“对城市和权力的崇拜几乎是每个来自农村的孩子的必然,不管他承认不承认。说我们崇拜现代和文明,说到底是崇拜城市和权力。”
对阎连科自己而言,这种崇拜感觉第一次来得这么真切,是十三四岁的时候第一次去洛阳。“城里路上都没有灰,街上满是高楼,现在想想估计也就三四层———走过去的男孩子女孩子都是一路雪花膏的香味。各家灯光都那么亮,而农村还在用煤油灯。那时我对城市生活有了热切的向往,幻想这一生如果到洛阳找个对象,住在那里,晚上看万家灯火该多好。”
高中的时候,阎连科要到村子以外七八公里的地方上学,每天早起步行,“我家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地瓜粉地瓜叶地瓜面,可每天我都能在村口看到村长家的姑娘拿着白馒头,一小口一小口嚼。那时觉得要想改变命运,要么逃离土地,要么有权力———这一辈子最差当个村长也好。”
现在,曾经崇拜的城市、权力、健康,这三样都成了他的恐惧。随着对城市和权力的向往慢慢变化,阎连科看到太多的矛盾。有一年,阎连科的颈椎病犯了,有人介绍他去北京西山看一个大气功师,“从家里出发,拿一个手机,有司机开车。
他不告诉你路怎么走,就说往前走多少米,看到什么标志物往哪儿拐,不停有电话通知,现在我也说不清是在哪儿。进到山里,院门口有人站岗,里面山坡上有五套别墅、两栋楼,都五星级宾馆一样,地毯有砖块厚,都绣着莲花。里面有花匠、电工、水工。吃饭的时候,饭菜都没法形容,又看到男男女女,女的戴着胸罩坐在那里打麻将。你不亲历就不知道这样的情形。”
等回到农村一看,阎连科眼前又是另外一个样子。这种完全分裂的两个世界,让阎连科内心失去平和而充满焦虑。他对这两个世界都熟悉,又夹在它们中间,左眼看到这么一个景象,右眼看到相反的;左脚可以踏进城市里去,但右脚还留在农村里。
两个世界越离越远,阎连科坦陈是对内心不断撕扯,这种撕扯体现在他所有小说中,“比如写《受活》,是因为我自己对这个社会的感觉就是这么矛盾和焦虑。我会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写作最初,是因为在苏联解体时看到一条消息,讨论列宁遗体如何处理。
不管怎么处理你都会想一个问题: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我觉得这一声炮响是列宁最先扣动扳机的。列宁遗体处理的问题,不是苏联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那时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阎连科认为,他的小说老是与现实发生巨大冲突,老是和现实有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一拉就断。
“我一直觉得自己做人还是比较温和的,但作品很尖锐,经常会想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比如对权力的认识,在少年时期你会做和毛主席下象棋这样的梦,你还把他下输了,这是非常清晰的梦,因为它有太惊人的细节。可想而知你对权力的崇拜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读书时,有一次凌晨从天安门广场步行回学校,走在长安街上,你会发现自己内心的复杂,对权力的恐惧,完全莫名其妙。这么宽阔的马路,没有一个人,只有自己这么渺小。”一方面梦到下棋赢了毛主席,一方面觉得自己渺小得无法形容,阎连科带着“紧张关系”一路走来。写作,正是他对自己内心焦虑和矛盾的充分表达。
回到“世界中心”重新出发
l958年出生的阎连科,相较于他同代的作家属于大器晚成型,他直到l997年才发表了引起文坛关注的中篇小说《年月日》。l998年发表的《日光流年》是他创作生涯的第一个高峰。2003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受活》轰动文坛,成为他的代表作。2006年发表的《丁庄梦》则令他扬名海外。而20l4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让他跻身世界文学名家的行列。
阎连科去年赴捷克领奖,曾在当地举办的文学活动中有一次题为《有一个村庄是世界的中心》的精彩演讲。演讲中他提到,“中国之所以叫中国,是在古代中国人以为中国是世界之中心。中国的河南省原来叫中原,那是因为中原是中国的中心。我们县恰好在河南的中心。我们村,又恰在我们县的中心。如此这个村就是世界中心。”
纵使身子离开,阎连科的心一直认为身处“世界中心”,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其作品表达着独一无二的思想深度、广阔度以及写作风格的荒诞程度。
“我今天50多岁,用了30多年的时间来证明自己。离开村庄走得太远了,现在要带着对世界的认识,再回到村庄。”阎连科说,“回到这个村庄,你可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回不到村庄,可能你的作品就到此为止了。村庄唯一要求的是,你要用文学的方法、文学的名誉,一而再地向读者证明,这个村庄是世界的中心,是中国的中心。”
阎连科还说:“中国作家缺乏那种巨大的爱和包容,在青年时期完不成,但中晚年之后,一定要有巨大的爱。当然爱的方式不一样,那是对人的理解和爱,要让读者慢慢读到。”
或许,让身心回到村庄,带着包容和爱继续写作,是阎连科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