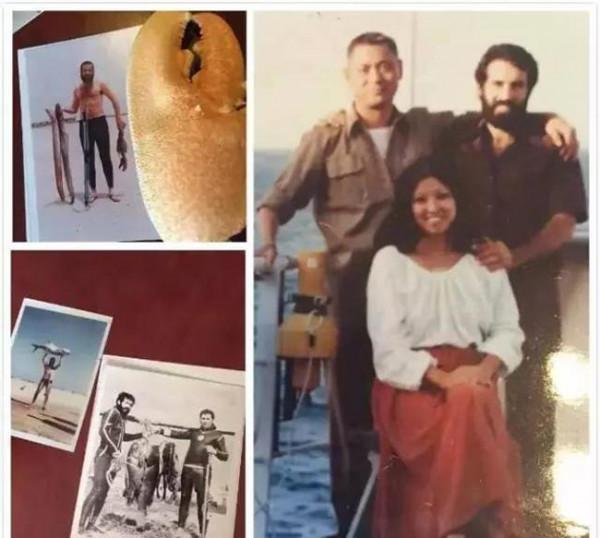三毛和王洛宾的关系 珊蔻说:“我希望能唱唱王洛宾和三毛的爱情故事”
凌晨1点30分,Sainkho Namtchylak降落北京。自2003年以来,她已经不记得这是多少次来到中国了。
十几个小时前她错过了航班,显得有些疲劳。人群中,这位穿着亮黄色短袖,带着平舌帽的老太太,和其他路人并无区别,很难有人会把她和舞台上那位具有超凡能量的歌手形象联系在一起。

在过往61年的生命中,她获得了许多身份:呼麦歌手,实验音乐艺术家,诗人,画家,母亲,祖母,图瓦人,俄罗斯人,奥地利人。然而作为当今世界乐坛最为活跃的艺术家,Sainkho Namtchylak成名已久。她的故事并不复杂。出生在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父亲是当地电视台的记者,母亲是一位中学老师,在音乐学校学习音乐和作曲,在莫斯科组建自己的乐队,后来又到奥地利,开始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合作。

Sainkho的故乡被世人所“发现”,是一个极为偶然的事件。20世纪60年代,一个狂热的集邮爱好者在一枚小小的邮票上看到了和这片土地有关的意象——飞鸟,骏马,湖泊,草原。它深深隐藏早欧亚大陆腹地,那里的人们过着游牧生活,骑马驰骋在草原和群山之间,他们的胸腔中长久流传着一种声音,变化多端,气象万千,那是一种极其独特的喉音唱法(Overtone Singing),当地人称之为“呼麦”(Khoomei)。

这位集邮爱好者深深为之着迷,致力于去向生活在西方的人们介绍这种文化景观,由于种种原因,他毕生都没有机会踏上这片他所痴迷的土地。这位邮票爱好者的另一个身份是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曼哈顿计划”的参与者——理查德·费曼。在他去世后,他的遗愿被他的好友,人类音乐学家泰德·列文(Ted Levin)所继承,后者在90年代后得以进入这一地区,与当地的艺人合作,将图瓦音乐推向更为广阔的世界。

Sainkho Namtchylak初登乐坛也正是这一时代,这也是音乐工业走向全球化、资本化的年代,是世界音乐(World Music)作为一种类型音乐被人们所识别,聆听,并持久地形塑人们的空间意识,重新绘制世界地图的年代。
在她的音乐中,我们不难体验到这种丰富的“世界性”。她一次次将图瓦的传统与现代音乐的诸多进路进行融合,从人声到电子,从即兴到爵士,她自由地穿行其中,留下了诗意的踪迹。在我们的采访中,她并不满足于将自己的身份仅仅局限于呼麦歌手——这一被中国乐迷最为熟知的身份,而是将看成构成自身及其音作品的众多元素之一。这并不意外。
30年来,她发行了76张专辑,她看待他们就像孩子,以至于无法从中选择一张自己最为钟爱的作品。她每天都泡在工作室里,写诗,画画,创作新的音乐。她的下一张专辑《Urban Tribal BPM》将会在2019年发布,风格是电子,爵士和现场人声。
在谈到她的首张专辑《Lost River》时,Sainkho试图去解释创作时的苦闷:1993年,在世界的一极轰然倒下,人们面对着如干枯的河床般的城市和国家,失去了自己的语言,那些愤懑,饥饿和无法言说的情绪,变成了抽泣,呜咽,呢喃和嚎叫,这些是旋律和节奏不足以负载的。
采访中,她挥舞着手臂,或是将拳头紧紧地攥在胸前,那些言语不能抵达的,她哼哼唱唱,用声音再次进行了说明。那张专辑的13首音乐中,只有两首有明显的旋律,其余则是各种各样的声音实验。
十分奇特的是,如果有人尝试在网易云音乐输入Sainkho的名字,排名第一的也是这张《Lost River》。在同名歌曲下,足有足19万条评论,写满了人们被这张专辑的实验性所震慑后,试图以各种修辞来把握的的震惊体验。
在中国的社交网络上,这首歌曲也成为了“神曲”,被人们所调侃,娱乐。这种猎奇的目光,似乎反衬出一个普通听众和实验音乐实践尴尬的相遇时刻,但也足以折射听众和创作者之间的代际落差——这一目光所遮蔽掉的不仅仅是音乐本身的激进性和实验性,还有它背后的广阔而沉重的政治面向。
她似乎并不介意这种落差,甚至有几分自豪地说,这张专辑还被选进了德国的中学音乐课堂。当问起她接下来的打算时,她说受人之邀约,会创作一首向王洛宾致敬的音乐,在她眼中王洛宾是一个传奇,他将“自然的声音,民间音乐和学院派的作曲演奏”融为一体。某种程度上,她和王洛宾做的是同样的工作,而“中国人尚未充分了解王洛宾都做了什么”——也可能并不了解她正在做什么。
对于她,王洛宾似乎是一声遥远的回响。同样的回响,也势必成为在未来两天的音乐会中所期待的事物。受战马音乐节之邀,图瓦音乐的“Big 3”——Huun Huur Tu, Yat-Kha,以及Sainkho,将首次同时来到中国演出。
Sainkho要演两场,分别在14日的北京和15日的上海。密集的行程之外,似乎又是时代的一个缩影,Sainkho心中的那个“世界音乐”的时代,的的确确来临了——尽管要去应付那些困惑的眼光和复杂的逼视,而更多的时候,它代表着诸多可能性的相遇,如同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在那里,世界像图瓦共和国的草原般铺陈,伸展。
X博士:我们先从你的名字说起。中国乐迷都习惯叫你的中文名字“珊蔻”,可能是因为Sainkho Namtchylak有些绕口吧。那么你的姓“Namtchylak”,在图瓦语中是什么意思?
珊蔻:图瓦语中的”Namzhil”或”Namzhilak”,是用来形容那些有读写能力,撰写和保存书籍的人的。在古代,读和写可不是人人都会的事情,你需要花一些小钱来请人帮你去读写,去处理那些写给亲人和爱人的信,不过更多的时候,这些有读写能力的人们的工作是处理官方的信件,以此作为职业收入。
古时那些僧侣和写家们会坐在街边,直接向有需求的人提供服务。因此,他们也是头脑十分活跃,又具备很大信息量的人群,有点像古代版本的信息处理中心。是的,我的父姓正是由此而来。
X博士:你此次的访华计划?
珊蔻:我们会在北京和上海做两场演出。都是很棒的城市!
X博士:对中国有什么印象?
珊蔻: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2003年,去了北京,上海,台湾和澳门。当我在北京街头打出租车去录音棚时,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自行车,成千上万辆的自行车……如今自行车少了很多,汽车越来越多。我也不知道哪种情况更好:无数的自行车还是无数的汽车。
X博士:中国和苏联一样,都经历(过)一个社会主义文化时期,也经历了走向“世界”和全球化的过程。你曾经谈到自己艺术生命中最重要的历史时刻之一,是1989年在阿巴坎(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城市,哈卡斯共和国首府)巨星的音乐节,你将其称之为“世界音乐的开端”。30年过去了,作为一个时常被划分为“世界音乐”分类中的音乐家,“世界”这个词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音乐来说,这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吗?
珊蔻:(世界)像一个开放的实验室,一切元素都可以去尝试融合。事实上世界音乐正在成为全球音乐舞台现场最强劲和最广为人知的音乐类型,并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呈现着:器乐演奏和声乐的融合,电子乐和声乐融合,等等,各种各样的声音系统和声音概念,多多少少都被不同地区的传统民间音乐,古代仪式和古代文化所影响。“世界”之中包含着所有的可能性。
X博士:的确,但当下年轻人喜欢的音乐形式和你的世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甚至不需要吉他,只要有一台MacBook就可以做音乐了。Liam Gallagher说,把电脑烧了,开始弹吉他吧。你认为这些变化对世界音乐是一种挑战吗?
珊蔻:其实我从1993年开始——我所说的“世界音乐的开端时刻”,便参与到内部进程中了,它从那时就开始就成为一种独立的街头音乐。我总是在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
X博士:你也是成长在冷战中的一代,当你现在回看,前苏联的生活和回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珊蔻:幸运的是那个(冷战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的回忆谈不上美好,它总是和挨饿相关。但那段记忆也代表着一段有趣的生活,那时我酷爱收听电台,从早上6点直到深夜,电台里会播放各种古典音乐,介绍文学作品。那些东西我都是在苏联时期学到的。唯一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去演奏那些我们真正喜爱的音乐,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和乐队会在新思维改革实施之后搬到莫斯科并开始在那里安顿下来。
X博士:你如何看待自己音乐和身份中的“图瓦性”(Tuvaness)?比如传统文化,萨满教的传统,蒙古的哲学等等,他们又是怎样塑造了你的音乐?
珊蔻: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萨满教的传统。它听起来其实是非常先锋的。任何萨满的意识都像是一场先锋艺术的表演。在我看来最早的艺术家就是萨满们。传统(图瓦)的哲学同样很重要,他们是佛教寺院的主要工具,同样给我的音乐带来了深刻性和思想性。
X博士:再过去三十年中你发布了将近30张专辑,哪张是你最喜欢的?你在不断试验打破音乐风格的边界,从实验人声到传统双声呼麦,从电音游牧到和Tinariwen等等不同地方的音乐人合作,你的下一个计划是什么?
珊蔻:我其实发布了76张专辑,他们都像我的孩子,很难挑选一个最喜欢的。如果非要说几个的话,似乎《Stepmother City》和《Time Out》是最受欢迎的。
X博士:一些中国的音乐网站或App上,我们发现一个有些讽刺的状况:你最受欢迎的歌曲是《Lost River》,也就是那张最实验,最先锋,同时又是旋律性最弱的同名专辑歌曲。一些并不了解你的听众们被你实验性的喉音所震惊,甚至会有人觉得“恐怖”,“怪异”。你对这种实验音乐和观众之间的认知落差怎么看?
珊蔻:人们不知道Diamanda Gallas,Prodigi,The Kiss乐队或者其他先锋艺术的表演吗?Lost River可是1993年的专辑。这首歌还进了德国的高中音乐课堂。
X博士:对Diamanda Gallas和大野洋子的评价?
珊蔻:他们都是我希望合作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有魔法的明星,和他们共事肯定很愉快。
X博士:作为了解你和图瓦音乐的中国歌迷,可能也很难想象有朝一日可以看到Sainkho, Huun Huur Tu还有Yat-Kha同时来到中国为观众们演出。或许是呼麦和图瓦音乐更流行了,你觉得呢?
珊蔻:是这样的。喉音艺术成为了21世纪新的文化现象,不仅仅是歌唱,倾听也很重要,正因如此,古老的传统才得以在今日得到重生。
X博士:你和世界上的许多艺术家合作过,这中间也有来自中国的音乐人,比如李劲松等等。能讲讲你和中国音乐人之间的故事吗?有没有喜爱或想合作的中国艺术家?
珊蔻:我和唐朝乐队的吉他手老五相识。我非常感激他和他的夫人牧牧,他们在我多次拜访北京期间无私地帮助我。我们还一起合作,去录一些音乐,那是在2008年。关于中国艺术家,我收到了一份邀请,希望我能写歌致敬王洛宾和三毛之间的故事 ,我正在进行与此相关的创作。
X博士:你曾经是图瓦唯一的女性呼麦艺人。打破传统的禁忌需要勇气,天赋,也需要一点点运气。你的成功是否激励了在Kyzyl当地和你有同样梦想的女孩们?
珊蔻:在这个时代,呼麦已经不是女性的禁忌。的确有很多女性歌手去走这条路,也有很多年轻的女孩去音乐学院学习,去参加比赛。她们做得不错。
X博士:有没有担心呼麦有一天会失落,被人们所遗忘?
珊蔻:不会。她始终向历史敞开,向人们已经遗忘了的声音的历史敞开。所以他会长久地生存下去。
X博士:未来三到五年的计划?
珊蔻:我的梦想是能学会中文。希望有机会我能呆久一些,去学习中国的语言和艺术。
我们的采访在持续了一个小时。Sainkho一边吃早饭一边聊天,精神很好,人也十分健谈。为了在北京今日并不洁净的空气中保护她的嗓子,我们颇有些不舍地结束了这次愉快的谈话。
随后,她的乐队成员陆续抵达。她的演出即将开始。
本次珊寇老师在中国的演出有两场,一场在北京,9月14号星期五晚7点30分,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一场在上海,9月15号晚星期六晚7点30,在上海1862时尚艺术中心举行。相信你们,一定不会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