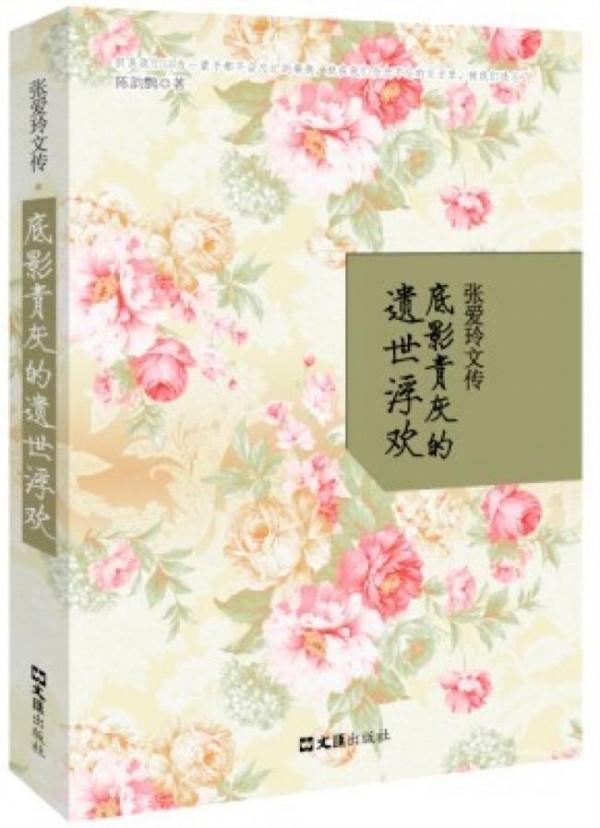陈香梅的母亲 张爱玲、陈香梅记忆中的香港沦陷
节选自《香港文学史》 第二次到香港的张爱玲 她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还是个并不更事的女学生,还拿着奖学金读着香港大学。仿佛记忆中每个穿着素装校服,配着校徽的女学生一样。 这是个一辈子都在逃避的女人。她说,“我爱听市声”。
因为她实践着大隐隐于市。于是她是很坦然的享受着上海那层暧昧氤氲的浮华灯光,还有眼前华丽旗袍的包裹。她躲避着世事纷繁变化,一门心思的用墨水去描绘一群又一群痴男怨女。带着她上海人的性格和背景,她写了八个给上海人看的香港故事,其中就有她最成功之一的《倾城之恋》,里面有个叫白流苏的女人。
就象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大学里面几乎定型一样,短短的第一次停留在香港时间,终于让她成熟起来,无论年龄,生理,还是阅历。
她是一个骨子里是上海的人,长大后却戴着一副名字叫做香港的遮阳镜。 也许因为躲避的性格,所以她无法接受,那大上海居然转眼间被一群腿上拖着泥土的人解放了。也许是因为生怕被泥土弄脏了她的华贵旗袍,1952年,她迁移到了香港。
这是她第二次到香港。也许滋养了近百年的西风,骨子里面也满是算计小聪明的这个殖民地,永远都象她心目中的上海。原来的上海一夜之间,已经面目全非。 她在躲避中用自己的行动来抗议身边的变迁。
那时候全国正陷入抗美援朝中,几乎全面反美。她偏偏要为美国人工作,拿着美元。才到香港,她便接受了美国驻港新闻处的工作,为他们写着小说,就是后来在她写作生命里部头最重的两部小说[秧歌]、[赤地之恋]。
先后两次到香港的她,截然不同。一向只关心旗袍的花色、市井的风味的她,居然最强烈的用起文字来对现实表明了自己最大的抗议,此时的她就象一个怨妇那般。 《秧歌》第一次涉足了农村题材,主题是“饥饿”。
在一个村庄,来了两个外来人。一个从上海归来的女佣人——月香,一个是下乡来体验生活的电影编剧兼文联干部顾冈。晃眼一看还以为是[红旗谱]、[小二黑结婚]之类的山药蛋小说。内容却近似于文革后的“伤痕文学”那般,页一页都是控诉,但显然比起后者,[秧歌]要淡然了许多。
里面的人没有如同时期内地的同行小说那般,一股脑的歌颂与赞扬。她其实只是用自己的笔去反映一段真实的面貌。 张爱玲的文笔与其说是小资,不若是自由。
自在的享受物质生活,享受哪怕是一段失败的畸恋,享受眼前暗掠而过的一副色彩。而当这一切却要受到一种专制时哪怕丁点的羁绊,她默默的,愤怒了,直到灰心死意。在她的笔下,即使最惊心动魄的爱情,也表现得淡然而娟秀,而在字里行间,满是透漏着一股冷凄。
第二次到香港的张爱玲,也在淡然的写着(在当时更准确的说该是揭示吧)一段依然凄凉的真实。 她描写了那个原本饥饿的村庄,因为要支持抗美援朝,村里号召每个人给军属们捐猪肉。
那些省吃俭用依然不够填饱肚皮的人们,不得不想出抢粮的主意。在抢斗中,女主人公就那样给活活踩死了。她用一注冷清的墨水,在白纸上记录着人们的无奈。 紧跟着,《赤地之恋》又出笼了。这部小说反映的现实与结构、人物愈加复杂。
其背景先后跨越了“土改”、“三反”、“抗美援朝”。男主人公刘荃在农村因看不惯在土改中的种种弊端,只身来到了上海。在农村他是原本结识了女大学生黄绢,并和她陷入一个爱情。谁知道来到上海,禁不住女干部戈珊的诱惑,与她又发生了关系。
谁知道,城市里也同样是充满了陷阱。刘荃因为三反而进了监狱。黄绢来到上海寻找恋人,得知此事后,又用自己的身体讨好了当时掌权的干部,把他从牢里面救了出来。刘荃自以为自己是个负罪之人,于是依然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途。
也许这依然是张爱玲一贯的笔调,让一个男人内心里既充满了对昔日爱人的负疚,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去维持与新情人的关系。双重的煎熬,如永远的轮回一般,千年不变的拷问着这世界的所有人。
也许因为这两部小说,至少是直接的原因,张爱玲从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给人为的抹去了,就象抹去了沾在墙上的蚊子血。直到数年后,才重新有人去追忆那残留着的一丝淤痕。 其实,她的写作内容在今天看起来,也并无多大的过错,而一代才女的名声竟然遗失在尘封里。
只是因为不甘接受与屈服,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是一种女人的骨气。也许她只是一个旧时生活的遗老遗少,生活的地方变了,自然便迁移到一个气味类似的地方而已,继续做着她可心甘情愿付与的事。
她一个人在那里,永远也不愿意和周围相妥协,用文字把自己包裹着,甚至最后连冷冷的看看这个世界都懒得。所以她只是因为写出了在那两部不合时宜的小说,便让自己给人遗忘了40年,也不做任何辩白。
只是多年以后,时代如风,吹散了蒙尘,人们“发现”了她,还有那两部在今天看来却颇值得研读的小说。 她也不愿意象胡兰成一样,最后终老台湾,那个保留着她的民国招牌的地方。短暂的香港之居,也许那里气味还是不够地道,最后还是孤身一个人去了纽约。
其间又曾短暂的回过香港,这一次停留的时间更短,一次比一次更短。最后一次,甚至几乎没有留下可以流传的作品。人们开始嘲讽,一代才女也终于江郎才尽了。 1995年,她死在了纽约寓所里,冷清得一连几天都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