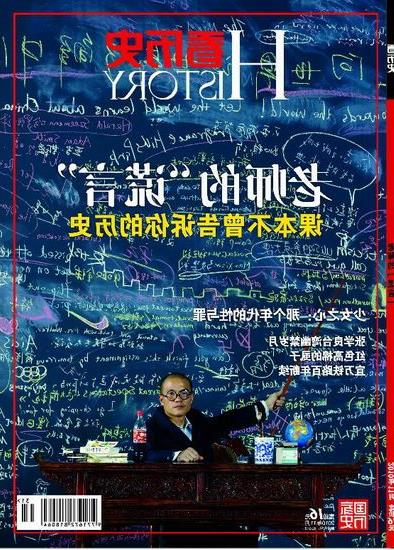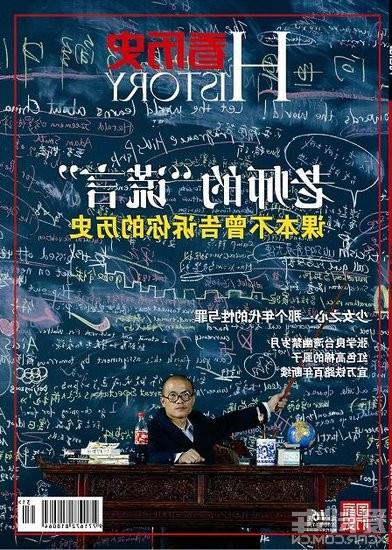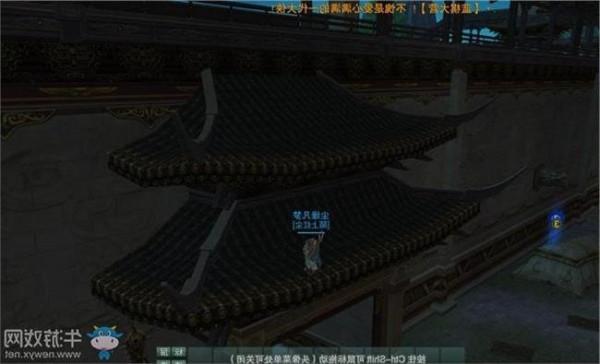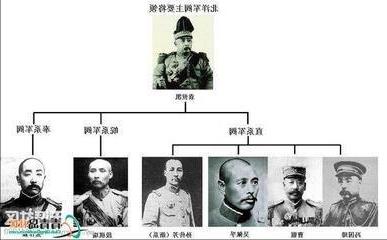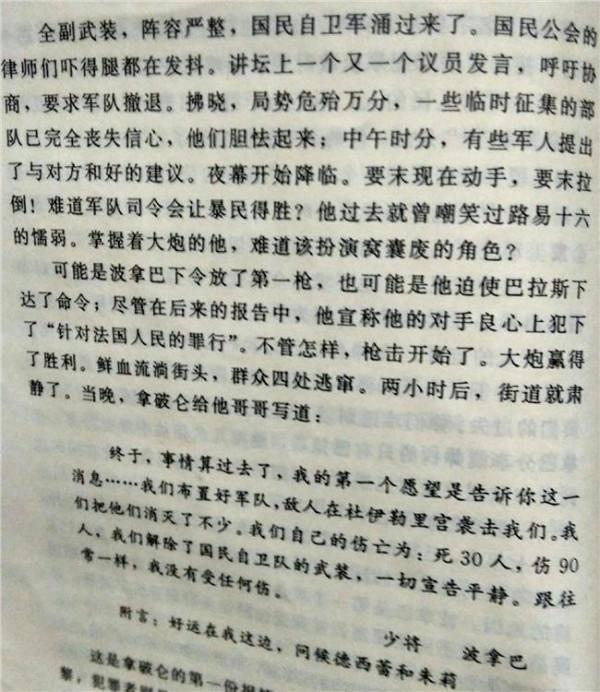吴佩孚的历史评价 课本不曾告诉你的历史:吴佩孚拒与日本人合作
1950年代初期,一篇颂扬朱德艰苦朴素精神的文章——《朱德的扁担》被编入了小学教材。然而,在十多年之后的1967年2月,学生们过完寒假回到学校后发现,同样一篇课文,已经换成了《林彪的扁担》。无数的“红小兵”们又开始在这篇课文中学习林彪的艰苦朴素的精神。
仅仅数年之后,林彪事件发生,教材又悄然换回了《朱德的扁担》。一根扁担,就这样随着政治风云变幻而不断发生换位。这是对常识的亵渎,还是对现实的嘲讽?
虽然这个故事是出现在语文课本,但从来以课本和老师的话为金科玉律的孩子们,如何去辨别虚构与真实呢?
教材之于一个人的意义,远不止于普通的书籍。教科书中的内容成为一种先验的常识和固有的知识框架,而被不假思索接受下来。由此出发,这些常识成为我们认知这个世界的起点和原点。
然而,一旦常识出现问题,则后续延展的知识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结果上,都会出现偏差。
因此,学者谢咏指出,教科书的编纂,一般来说有国家强制特征,这是教科书编纂的通则,因为它可以保证知识传播的国家意志。
而另一方面,教材本身由此面临着诸多悖反。其一,它试图提供一种“标准答案”,而这种答案,却时常随着人们的认识的深化,或者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其二,作为一种“标准答案”,它无法展现出我们对历史认知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作为一种高度“浓缩”的规范化知识,它远不足以展示我们经历的过去的丰富与多彩。
因此,1995年,美国学者詹姆斯·洛温写了一本书,名为《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错误》。他在序言中出语惊人:“实际上,历史是唯一一门让学生学得越多就愚蠢的学科。”
他发现,“美国人既对自己国家的过去感兴趣,却又饱受着他们中学美国历史课程的折磨。”那些充斥于课本中的谎言与偏见,有人总结为虚构之说、片面之词和掩饰之计。而这些,大多来自于沿习已久的认知误区和基于某些冠冕堂皇理由——最常见的是爱国主义——而有意的修饰。
在《老师的谎言》中,洛温告诉人们,不必担心真相会引起混乱;最危险的,是对真理与良知的麻木,以及对思考惰性的习惯。“我们需要培养所有阶级、所有种族背景以及不同性别的美国人都能掌握历史的力量——即用自己关于过去的理解去激励和证明自己当前的行动。这样,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人都将从历史中获得严肃的教益。历史不再只是令人厌倦的‘僵尸’”。
那么,逐渐长大的我们,究竟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审视那些我们从小到大,认为理所当然的“常识”?
我们能做的,只有回顾常识,回到起点,重新见识历史丰富多彩的另一面。
历史老师应该教什么
文│袁腾飞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记载历史、研究历史的学问却往往随着人类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因此,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对此历史学者袁伟时曾提到,对历史教科书而言,比掩盖真相更可怕的是让学生放弃独立思考,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的最大弱点。
作为教科书,价值取向应该趋向客观,使学生了解自己民族的发展过程和经历,使学生产生国家和民族认同感和荣誉感,从而培养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学生群体。教科书不能出于一时的政治需要,而把源源不断的历史长河剪断,否则教育必将出问题。实际上,将“革命史”教育极端化在我们这里并不是没有过,“文革”时期,那些殴打过老师的学生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快感;那些被自己的学生批斗殴打的教师都体味过“造反有理”的“革命史”教育所带来的苦味。
现在的教科书仍大量受旧框架的限制。按历史教科书的观点,中国的历史其实很简单,主要有四条:
1.凡是推动统一的,就是进步的。反对统一的就是反动的。
2.凡是抵抗外侮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反动卖国的。
3.凡是造反的都是革命的。
4.凡是扩张了领土的,就是进步爱国的,反之,就是丧权辱国的。
比如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历史哲学虽然得以淡化,但某些狭隘民族主义情绪却依然根深蒂固,将义和团在“扶清灭洋”口号下对洋人和西方文明采取的一系列野蛮行径,简单视为反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就是一个例子。
外国学者说中国人对历史是“有选择地记忆”或者叫“有选择地遗忘”。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对义和团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现在世上是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我国民若是希望义和拳不再发生,讨厌像克林德碑这样可耻纪念物不再竖立,到底是向哪条道路而行才好呢?
再比如关于太平天国,
1862年夏,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梁启超先生言:“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然而在过去极左思潮一度泛滥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
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
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
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这种作风,在今天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有很大的影响。
学者徐友渔先生1986年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大使馆发给留学人员一本书时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你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这件事让他很受震动,印象极深。徐先生接受采访时说:“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以前对中国学生灌输的历史知识是多么的片面、多么的有问题、多么的苍白无力!这么可笑的做法难道还应该继续吗?这种做法跟中国融入世界是格格不入的,通过教科书的形式来灌输一些教条,这种做法太过时了。”
现在,新历史课程强调人文主义精神、强调人性和生命的价值,确认多元化的历史认知的合理性,要求学生学会同他人,特别是有不同见解的人合作。这意味着,新历史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会使今后中国社会、政治的变革走向更加宽容、更加人性的方向。文明还在路上,中国人都在期待。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高中《语文》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