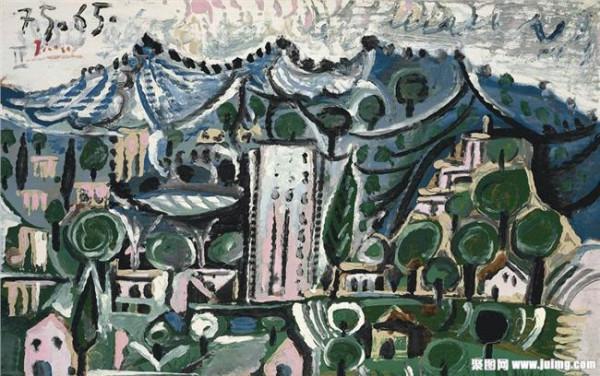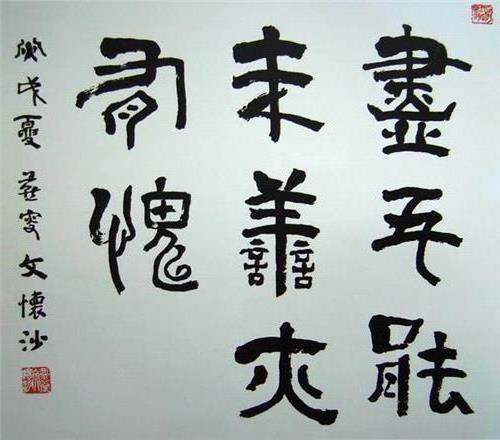任晓雯作品欣赏:《我的妈妈叫林青霞》
任晓雯,小说家,出版有长篇《她们》《岛上》,短篇集《阳台上》《飞毯》。1-4届新概念大赛连获一、二等奖。《她们》获2009年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提名奖。小说见于《人民文学》、《花城》、《钟山》、《上海文学》、《大家》、《天涯》等。
随笔、评论等见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世纪周刊》、《新京报》、《书城》、《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纽约时报中文网等。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语、意大利语、瑞典语等。
任晓雯作品欣赏:《我的妈妈叫林青霞》
我的妈妈叫林青霞。她报出这个姓名时,仿佛自己也不能确定。停顿一下,若有所待。直至对方说:“长这么漂亮,怪不得叫林青霞。”她才“哪里,哪里”笑起来。她笑的样子,仿佛笑到一半,戛然而止--为了掩饰四环素牙,嘴唇抿得太紧了。
傍晚时分,麻将搭子们在楼下中药铺门口,一声声喊:“林青霞在吗?”知道她在,偏要搞出动静,惹得邻近窗口纷纷探头。“快上来。”林青霞滤掉残汤剩油,将碗筷堆进搪瓷面盆。铺好绒毯,倒出麻将牌。
木梯咯吱作响。搭子们上来了,拎着瓜子水果。有时三个人,有时五六个。交替打牌、围观、“飞苍蝇”。林青霞不停嗑瓜子,嘴边一圈红红火气。
婆婆张荣梅提起嗓门:“伟明,你老婆不洗碗。”
曾伟明抖动报纸,扔出一句:“快洗碗。”
“烦死了,会洗的。”
我放下铅笔,默默出去。他们以为我到过道小便--痰盂放在过道上,遮一挂麻布帘子。我穿过过道,上晒台把碗洗了。
麻将打到后半夜。我被日光灯刺醒。换下场的牌友钻入被窝,双脚搭在我身上取暖。窗外,有人骑轮胎漏气的自行车,咔嚓咔嚓,仿佛行进在空阔无边之中。梧桐枝叶受了惊惶,喧哗翻滚。张荣梅也醒了,连声咒骂。一口令人费解的苏北话,犹如沸水在煤球炉上持续作声。
林青霞说,苏北话是低等话,不需要懂。不打牌的日子,她倚在邻居门口,织着毛线,模仿张荣梅的“低等话”。“苏北老太凶什么凶。我娘家也是体面人,10岁的时候,就用上四环素了。嫁到曾家没享过福。我的同事严丽妹,你见过吧,满嘴耙牙那个,老公做生意发了,光是金戒指,就送她五六个。我命这么苦……”
林青霞不像命苦的样子。圆润的脸蛋,用可蒙雪花膏擦得喷香;头发烫成方便面,骑自行车时,飘扬如旗帜;为了保持身材,她将肉丝挑给我,还按住腹部,拍啊拍的:“我从前体形好得很,生完你以后,这块肉再也去不掉,”还说,“姑娘时是金奶子,过了门是银奶子,生过小孩是铜奶子。”在公共浴室,我观察那对奶子,垂垂如泪滴,乳晕大而脏。我羞愧起来,仿佛亏欠林青霞太多。
林青霞穿针织开衫和氨纶踏脚裤。有双奶白中跟喜喜底牛皮船鞋,周日蹲在门口,刷得闪亮。张荣梅的灰眼珠子,跟着转来转去。林青霞故意穿上牛皮鞋,踩得柚木地板喳喳响。她逛服装店,试穿很多衣服,一件不买地出来。她议论严丽妹,“瞧那屁股,挂到膝盖窝了。再好的衣服,都给严胖子糟蹋了。”
严丽妹脖颈粗短,四肢墩实,仿佛一堵墙。她移动过来,包围我,沦陷我,用棉花堆似的胸脯托举我。她身上有黄酒、樟脑丸和海鸥洗发膏的味道。她每周六来打牌。在家喝过泡了黑枣枸杞的黄酒,脸膛红红发光。她说:“我在吃海参。范国强认识一个大连老板娘,做海鲜生意的,每天吃海参,四十多了没一根皱纹。”牌友夸她大衣好看。她说:“范国强在香港买的,纯羊绒,国际名牌。”
是夜,林青霞连连输牌。她再也无法忍受。翌日大早,到香港路爱建公司,买下一块最贵的羊绒料。她将它摊在床上,欣赏抚摸。“我这一辈子,从没穿过这么好的料,得找个最好的裁缝,”在大橱镜前比划,“可以做成长摆的,安娜·卡列尼娜那种式样。腰部收紧一点,穿的时候,头发披下来。”
为搭配想象中的大衣,林青霞买来宝蓝塑料发箍、桔色绒线手套、玫红尼龙围巾。“黑大衣太素了,里头要穿鲜艳颜色。”她挑选七彩夹花马海毛,动手织一件蝙蝠衫。
冬天犹如刮风似的过去,脚趾缝里的冻疮开始作痒。大衣没有做成,林青霞还在编织蝙蝠衫。织着织着,毛衣针搔搔头皮,扯两句闲话。她说年轻时很多人追她。当年的追求者,有的当官了,有的发财了。“萍萍,各人各命。如果换个爹,你早就吃香喝辣了。”
这话或许是真的。顺着她的目光,我看到窗外梧桐叶。新鲜出芽,金闪闪颤动,仿佛一枚一枚婴儿的手。我心里也冻疮一般痒起来。
曾伟明双肩微耸。看得久了,想伸手将它们按平。即使在夏天,他也系紧每粒衣纽,穿齐长裤和玻璃丝袜。他一身机油味儿,走路悄无声息。说话口气总像亏欠了别人。
一天下班,他碰到前同事“王老板”,邀至家中吃饭。王老板吊儿啷当,还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后来下海做个体户。在我六岁时,他来做过客,帮忙组装电视机。那时不叫“王老板”,叫“小王”。小王买了劣质显像管,电视画面常常倾斜,不时翻出一屏雪花。他捏起我的腮帮,挤成各种形状,还喷我一脸烟臭。
三年后,几乎认不出“小王叔叔”。肥肉在他皮带上,水袋似的滚动。右手中指一枚大方戒,戒面刻着“王强之印”。他逮住我,将戒面戳在我胳膊上。刹时变白,旋即转红,仿佛盖了一方图章。“萍萍长大啦。”算是见面礼。
他又招呼林青霞:“小林,你一点没变,还这么好看。”
林青霞绷着脸,双腿夹住裙摆,翻身靠到床头。
他扭头四顾:“你们家还这么破,”掏出一张票子,“小林,买几瓶啤酒,‘光明’牌的。”
林青霞白了一眼,发现是张十元钞票,起身接下,磨蹭地问:“几瓶啊?”
“六七瓶吧。”
林青霞下楼去。
王老板对曾伟明说:“你没把老婆调教好。”
曾伟明讪笑。
那个夜晚,我难以入睡,不停翻身。综绷床的嘎吱声,被王老板嘶哑了的嗓门盖过。他描述自己生意如何了得。曾伟明耸肩,佝背,一副受冻的样子。啤酒沫在嘴角闪光。听至妙处,小眼睛陡然有神:“小王,你太厉害了。”林青霞也倒了一浅底啤酒,慢慢啜着,盯住王老板的手。那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将大方戒拨弄得团团转。
几天以后,王老板出现在牌桌上。林青霞介绍:“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老板,做服装生意,以后你们买丝袜找他。”
同事纷纷握手。
一个说:“大老板跟我们平民百姓搓小麻将呀。”














![钢笔书法作品欣赏|硬笔书法作品欣赏楷书|[转载]硬笔魏碑楷书作品欣赏](https://pic.bilezu.com/upload/0/8c/08c9dbf5396faa997c7a47a532326073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