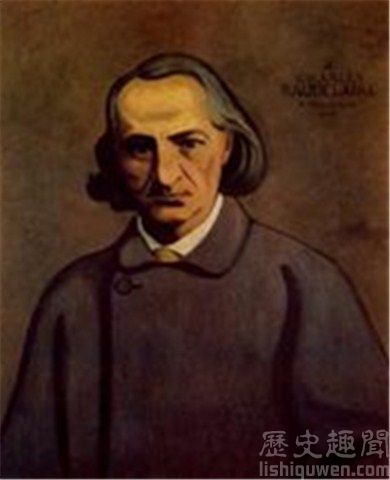叶芝与茅德冈 如何评价叶芝对茅德冈的追求与感情?
1889年的某一天,露珠湿润睡意的英国,伦敦贝德福德公园街。 一位24岁的年轻诗人,邂逅了他一生的梦。叶慈后来一遍一遍地回忆初见茉德•冈昂时的场景,这样写道:“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
” 从那一天,那一刻起,英语史上最美丽的诗歌之一就诞生了——《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我不离不弃 如今,这首诗歌在中国已是家喻户晓,即便许多人没有真正读过这首诗,却仍然对那一段话朗朗上口,感动不已,“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和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那痛苦的皱纹……” 为何这首诗能够打动这么多人,且走出爱尔兰,在其他许多国家至今传唱不衰? 首先,人们在对爱情的追求和拥有过程中,往往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如影随形。
而无论古今,横跨中外,最大的爱情诉求莫过于四个字——不离不弃。我们总想在有生之年,有机会来验证一下身边的这个人,能否实现我们对不离不弃的向往。
那么如何才能最好地证明不离不弃呢?只有时间。而时间一般会以两种形式来临,一是死亡,一是老去。 以死亡验证伟大爱情的,我们已经在中外无数的文学、艺术作品中表达多次,比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比如《牡丹亭》,比如《红楼梦》……;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一方面总感觉死亡似乎离我们很远;另一方面只能在死亡来临、生命终结时才能知晓这个答案,虽趋于生命完满,但我相信很多人是不甘心的。
于是,老去便成为最好的验证方式。 当我老了,朱颜辞镜,红颜不再;昨日青丝已成白发,皱纹爬满脸庞;你是否依然爱我如初?是否对我不离不弃?叶慈给出了答案, 也给出了誓言,“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那痛苦的皱纹……” 饶有意味的是,叶慈是在年轻时为茉德•冈昂写下这首诗,而后来的漫长岁月似乎都在一一检验着他当初的誓言,直到他老去,并且实现了这个诺言。
仿佛是终其一生,一直在朝着自己年轻时虚设的时空走去,走向年老,走向爱情,就像走向一种信仰。
这是巧合?还是个体生命在感情激烈时的预感?抑或是属于诗人特有的冥冥之中的“神启”?所有这些,都为这首诗蒙上了一层宗教般虔诚的色彩。
更具悲剧的是,《当你老了》——感动天,感动地,感动了世间所有的人,却唯独没有感动那个“你”。 “求不得”——失意引发诗意 从1889年遇到她的第一次起,茉德•冈昂就如影随形,不断出现在叶慈的梦里,心里,诗里;即便如今她已去世多年,却在叶慈的诗歌中永生。
此后,叶慈又陆续向她求婚四次,一次一次地被惨拒。 1917年,叶芝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向茉德•冈昂求婚,失败。 好友格雷戈里夫人鼓励他继续努力,而他只回答了一句话,“不,我已经累了,不想再折腾了。
”这时,离他在苹果花下对茉德•冈昂一见钟情,已经过去28年了。 这一年,叶慈已经52岁了。 “事实上,这次求婚更像是负气行为。”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都柏林大学英语、戏剧和电影学院教授Alan Fletcher一边走在Lissadell 庄园的石板路上一边略带神秘地说。
Alan教授面容清癯,一幅长者风范,却也不失风趣,说起叶慈的绯闻轶事,亦是绘声绘色,引人遐想。
我猜想他的求婚用词亦是意气用事,大概类似“这是我给你,也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你仍然拒绝,那我也就认命了。“ 有趣的是,大约五年之后,在遥远的东方中国,同样有一位年轻多情的诗人徐志摩,向他的挚爱林徽因求爱遭拒。
而他在给梁启超的信里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一样的苦恋多年,一样的屡次被拒。“求爱不得”,跨越东方与西方, 似乎成了诗人们的共同命运。
佛家说,人生有八苦, 分别是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 如此看来,求不得——便是叶慈的诗歌主题,也是他的人生命题。英国诗人W. H. Auden在悼念叶慈时曾写到,“疯狂的爱尔兰将你刺伤成诗”。
我觉得更确切地说是,“疯狂的爱将叶慈刺伤成诗”——爱的深沉,爱的坚持,爱的痛楚,爱的无望。 因为求不得,于是别地生花。比如他那首《漫步莎莉园》(Down by the sally gardens),读来颇有诗经中《蒹葭》之感。
一样的辗转反侧,深沉静谧;一样的佳人难求,寤寐思服。 在摄影家约翰•菲利普斯的书中,是这样描述茉德•冈昂的,“她尽管已71岁,仍然不顾警察的监视,在都柏林街头向人群演讲。
她谈到叶慈,笑了笑,说‘他是女子气十足的男人。’” 我曾不只一次凝视着茉德•冈昂小姐的照片。说实话,她实在算不得漂亮,只是眉眼略显清秀,眼睛大而有神,显得眼神颇为坚毅,这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女子,是一个生命底色很难被撼动的人。
我也曾不只一次追问: 爱情怎么会发生在这样两个人生志趣如此大相径庭,个人气质完全迥异的人身上呢: 一个是阳刚的革命家,她的父亲是英国陆军上校,而她则天性热衷政治、暴力和革命,终生司职于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一个是阴柔的诗人,他的父亲是画家,他则敏感多情、温和有礼,一生沉溺于文学之中,永远对故乡Sligo有一种泪眼朦胧的眷恋。
造化弄人,就是这样的两个人碰撞在了一起。 也许是灵魂深处的某种激情相通——她对革命的激情,多多少少类似于他对她的爱情——一样的如火燃烧,长年不熄。 如果说他真的终其一生爱上这个女人,不若说他终其一生爱上的是这种爱情,他甚至这么写,“爱的愉悦令爱远去(love's pleasure drives his love away)”。
失意引发诗意。对于个体叶慈来说,爱情求而不得,国家深陷动乱,可谓爱情和国家的双重失意。
可是对于诗人叶慈来说,也许是一种幸运。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国家尚未独立,民族动乱,才能更大程度激发诗人的家国情怀和民族情绪,启发创作。 同时,正如茉德•冈昂自己对叶慈所说的,世人应为她对他的拒绝而感谢她。
正因为在爱情的道路上,叶慈一直求不得,才一直在痛苦和失意中笔耕不辍。一方面在漫长诗歌生涯里为茉德•冈昂写下无数诗,并不断尝试各种文体和风格,从所有角度想象和沉淀爱情;另一方面在她的影响下,叶慈投身于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参与到国家民族精神的构建中,并成为其中最重要的支柱。
在第五次求婚失败几个月后,叶慈做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极具挣扎性的动作——向茉德•冈昂的养女伊索德•岗昂求婚,同样被拒绝。
就在同一年年底,他娶了早年认识的、一直仰慕他的英国女人乔治•海德里斯。这位年轻的妻子后来为叶芝生养了一儿一女。 叶慈一直是向往家庭生活的,也非常喜爱孩子。后来,虽然有妻有子,可是我相信他多少是心有不甘的,和宝玉一样“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而他一生爱慕的那个人,到死也未求得。
虽然叶慈自己曾在诗中说,“浪漫的爱尔兰已死”,但是这句明显是出于诗人的写作技巧或者意气而为,而他则终其一生都在诗篇中构建了一个无比浪漫的爱尔兰。
我相信,任何说英语的浪漫主义者,只要喜爱诗歌,就能脱口而出如《爱的悲伤》中的诗句:“一个红唇凄然的少女站起身, 仿佛世界的伟大充盈了泪水。
”或者“我一定是走了,一座坟墓边,有水仙和百合摇曳。”《快乐牧羊人之歌》 叶慈以其华丽的诗风、自由的想象不断丰富着爱尔兰,而他笔下描绘的爱尔兰,亦是格调优美,意蕴深邃,完全符合人们对爱尔兰的想象。(文/凌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