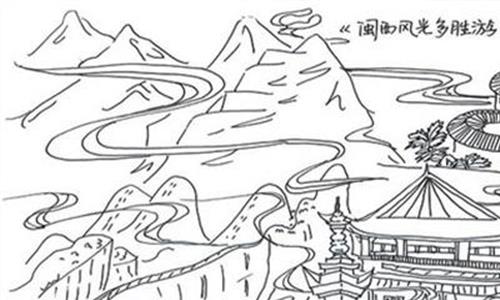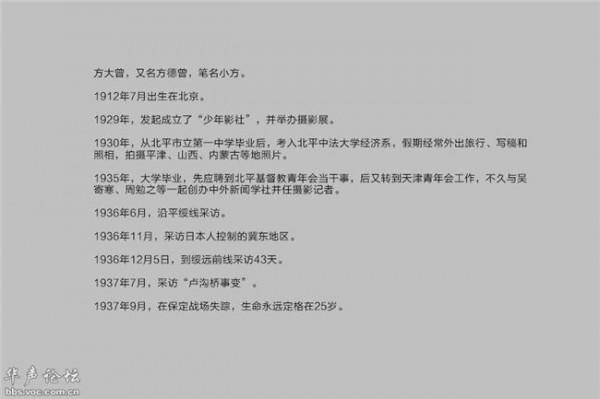川岛芳子是方姥谎言 张钰方姥 逻辑论证:张钰的方姥是川岛芳子是谎言
逻辑论证:"张钰的方姥是川岛芳子"是谎言
尤军丽
一、命题而非判断
判断是对事物的情况有所断定的思维形式。任何一个判断,都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如果一个判断所肯定或否定的内容与客观现实相符合,它就是真的;否则,就是假的。那么,"张钰的方姥是川岛芳子"这一所谓的判断是真还是假呢?从逻辑学的角度,对于"判断"一词有着更为明确的界定。

判断是自身持有的诸规定,是概念的真正的特殊性,是对概念的各环节予以区别,有区别而予以联系。通俗一点说,判断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区别于它物的特殊性。比如,"川岛芳子有一对招风耳"。这是判断,招风耳是川岛芳子本身所具有的特质,具有代表性。

而"命题"的规定性则具有普遍意义,而且不属于主词的唯一性。命题是外在所赋予的。
黑格尔认为判断与命题是有区别的:命题对主词有所规定,而这个规定与主词并无普遍关系,只不过表述一个特殊状态,一种个别行动等等类似的东西。比如,"家里来了一个女人,穿着棉猴儿,围着围巾,衣着普通,但气质很好。" 这仅仅是一个命题,只是对"一个女人"的外在表述,不能称其为判断。

判断是表达个体的特殊本质。而"穿着棉猴儿,围着围巾,衣着普通,但气质很好。"并不具备有特殊性的条件,因为在1955年底到1956年初春间,在中国北方,这是再大众化不过的穿着打扮。确切点说,这并不符合要表达的个体的本性。所以,这只是一个命题。

当然了,张钰画的她的方姥也有一对招风耳。可是画像的依据不清。王庆祥2008年12月29日日记记载,台逯林讲到,"方姥"画像如果属于作者画乃依据川岛芳子在狱中照片所画,而不是依据"皈依证"上的黑白原照片所画,其责任自然应由作画者(张钰)承担。王庆祥2009年2月17日日记记载,关于影像鉴定,后藤华说,那种(台逯林)肉眼观察的方式是不符合科学的。而且"方老太太"的唯一之像既是画像,就不可以依据。

所以,张钰笔下的"方姥"的那对招风耳是够不成判断的依据的。至于张钰对其方姥的其它表述则属于命题范畴。
对于张钰为其所提出的"方姥是川岛芳子"这一命题提供了诸多的证据,包括人证、物证等等。但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一项是直接的或所谓质的东西用来判断其命题为真,相反,却呈现出诸多的主观思维。这些客观地看来似是而非的抽象观念,使命题表达了张钰所提供的东西的感性存在。
一方面对证物的来源模棱两可,另一方面对证物的主观表达则充满一切。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说不清来龙去脉的证据,被认为描述得太像了,像得让人深信无疑!但张钰等人并不明白,无论他们描摹得多么的像,这些证据与方姥,与川岛芳子都是异在的,即彼此完全不相干。
事实上,这种主观思维的所制造的偶然形式,不但没有征服读者,却引导读者作出直接的判断结果,张钰等人的这种命题的不真性也就明白地显露出来了。
比如,段连祥的档案记载一定是准确无误的。"1948年6月4日-1948年11月2日,国民党正编207师服役。"这一命题表达了特殊而确定的思想,就可以从这一规定着的思维中推演出来,段连祥在1948年6月4日-1948年11月2日这个时间正在部队服役。
而张钰交代,在这个时间段内,即1948年年末的10月19日之前,段连祥等三人护送川岛芳子。张钰只顾着制造与川岛芳子执行死刑的时间巧合,却因顾此失彼而弄巧成拙了。如此推演可以证明"张钰的方姥是川岛芳子"的命题是假命题。
很显然,准确的外在因素(档案记载)是可以作为判断命题真或者假的前提的,并且我们还可以以如此被确立了并证明的东西("张钰的方姥是川岛芳子" 为假)作为证明其它相关命题的前提。
(二)循环逻辑
张钰等人是用何种方式证明"方姥是川岛芳子"的呢?
他们采取了所谓"原形先蕴"的循环逻辑。这种逻辑的错误就在于,将最初只是在理想方式内假设的"方姥是川岛芳子"当作已真实存在。对于张钰等人来讲,这种方法的可取之处在于,故事的发展都以川岛芳子为基准,使假设越来越符合川岛芳子,而且故事的内容也无需增加任何其他新的东西,只是形式上需要考虑方姥的故事的完善性而不断修补。
川岛芳子还是川岛芳子自身(至于川岛芳子的历史被写得面目全非,实为出书作者之责任),而方姥需要与川岛芳子有某些共同的东西,使他们同属一类或具有共性。以示张钰的方姥确实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确实活到1978年,并且是善终。
然而作为命题而非判断的那种只是表面的所谓共同的东西,并不是本质的共性;事实上只是,所有的这些证据被人为地归属在一起了,加以主观描述的它们的共同之点。这种人为规定的表象,是无法用来准确判断的。
张钰等人的逻辑是这样的:张钰的方姥是川岛芳子→方姥的东西属于川岛芳子→张钰的方姥是川岛芳子。毋庸置疑,这是何等低劣的逻辑。至于此命题本身是否是真,取决于中项内容"方姥的东西是否属于川岛芳子"。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1.东西是否属于方姥;2.东西是否川岛芳子曾经拥有。这是判断命题是否为真的基本内容,此外,在这两个问题都成立的前提下,还要符合形式逻辑。凭借这些形式,并且通过这些形式,而且存在于这些形式之内,命题才是真的。
于是乎,张钰等人从脑子里搜寻出来各种离奇的而毫无概念的想法,并根据他们的主观活动去强加给这些证据,而试图回避由证据的自身所发挥出来的本质。岂知,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比如,张钰等人主观地认为"浴嬉图"为藏名画,还猜得洋洋自得。不论怎么猜,都是向着川岛芳子靠拢,明显的"原形先蕴"。"原形先蕴"的弊端就是,永远也无法确立主词(方姥)与谓词(川岛芳子)的统一性,这种人为性使论证的形式及内容缺乏必要的特殊性。
然而,"方姥是川岛芳子"中的联系字"是"形成了抽象的表达。依这种同一性看来,方姥也须设定具有川岛芳子的特征,从而川岛芳子也获得了方姥的特征,而联系字"是"也就充分发挥其效能了。这样,这一命题就通过内容充实的联系字"是",进展到推论的过程。
推论是一切真理之本质的根据。正确的推论方法才能够有效地证明命题的正确性。推论方法的正确性是判断命题为真的必要根据。而形式化的推论采用的是不合理的表述方式,这使得推论与理性的内容毫不相干了。事实上推论是以理性的方式实现概念并使其外化。
张钰等人对"方姥是川岛芳子"的推论则是单纯的主观思维的一个形式,形成了经验的杂多体,他们所推论出的诸多结果不过是自我主观活动的实现,无法从证据的自身确立其推论的意义,当然也无法实现推论返回到概念的统一,更无法形成通过思维所规定的全体。
比如,张钰提供的景泰蓝狮子,没有出具年代证明,没有出具质料证明,没有出具底座封漆的证明,不过是几个自封的研究者在那里凭着想象猜测,猜测的方向就是一致向川岛芳子靠拢,靠得越近越觉得沾沾自喜。
那个"秀竹字条"倒是有专家读明白了篆字,至于字条的内涵则还是由这些自封的研究者以川岛芳子为依据,猜得令人啼笑皆非。对于"姥留念"三字的笔迹鉴定,并不能证明川岛芳子与"方姥"为同一人。而某位自封的研究者认为,"念"字,上部"人"字左右之笔划,与川岛芳子的笔迹极为相近、相似,只因纸面空间较小,未能全甩开而稍受限制,还是可以认定为川岛芳子笔迹。
这样主观的推论,对于探求事实真相是空疏无用的。
第一、这种推论中的各项是人为的偶然。
比如,张钰能默写"蒙古姑娘"歌词,三十多年过去了,怎么会记得如此清晰。段续擎都六十多岁了,"方姨"在四五十年前曾教过的长达18行、180余字的蒙古歌《瓮古特》,她还随手就能够把歌词全文默写出来。如果不是后天补课,怎会如此熟练。
还有张钰对于她方姥的一些行为和习惯的描述,几乎都与川岛芳子形成了偶然的相似。略举几例,①"方姥"手拎烧火棍几下子就把狗给打死了。伸手敏捷有狠劲,有川岛芳子年轻时的特征和影子;②"方姥"执意让"小波叨"喝下滴了两滴血的水,是"武士道"精神流露;③"方姥"左胸部位有块褐色疤痕。
川岛芳子受过枪伤,子弹射入部位恰在左胸;④"方姥"的早期脊椎炎与川岛芳子的脊椎炎症吻合。更偶然的是,怎么与"方姥"有关的,大多数都会关联到日本。
日本歌、日本舞蹈、日本画、日本的用具等等。很明显,这些描述只是一些旁观者的经验性的特征,并没有方姥本身具备的特殊性的特性。几十年过去了,方姥怎么没有个性、行为举止、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变化呢?
我们只须随便拾取一个张钰等人的推论中项,即可根据它过渡到(或推论出)他们所欲达到的结论,即"方姥是川岛芳子"。但假如从另一中项出发,比如,张钰通过后天补课,背会"蒙古姑娘"歌词,张钰对于方姥的描述也是参考了川岛芳子,那么也可据此来证明另一个东西,就是张钰别有目的;甚至证明与此前相反的某种东西,就是张钰的方姥不是川岛芳子。
第二、不仅这种推论中的各项是人为的偶然,而且这种形式化的推论也同样是偶然的。它们中间并没有可以作为联系的真正的中项。
(一)全称的推论。已先假定了结论,但条件是,结论本应先假定的大前提是对的。张钰等人的大前提就是"方姥是川岛芳子",但是通过对段连祥的档案进行研究,根本不存在段连祥护送川岛芳子的事件,所以张钰等人的大前提被否掉了。
(二)全称的推论建立在归纳上面。中项就是张钰提供的一堆证据,但由于无人能够说清楚这些证据的来龙去脉,凭着直接的经验猜测总要与客观有差距,因此如此种种的列举证据并不能满足真实性的探求需要。
(三)类推。中项是模棱两可的,大前提是不成立的,类推也就毫无意义了,更何况张钰等人的类推也是主观类推。结论自然是太过空乏了。
如此的类推形式要明确最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大前提先假定了结论所应有的内容,甚至因而先假定了结论作为一个直接的命题。为了能够说明这些大前提起见,首先必须确认关于各种证据的命题是正确的。
1.偷换概念,违反同一律的一种逻辑错误,即在同一议论中用不同的概念来代替已被使用的概念。
如:望远镜有HK,HK是川岛芳子曾用缩写→望远镜是川岛芳子的。
第一个HK具有很普遍的意义,众所周知,香港的缩写是HK,还有人名Helen Keller,也可以缩写为HK。第二个HK则代表个体。
再如:秀竹字条落款"小方",小方八郎是川岛芳子的秘书→字条是送给小方八郎的。
"小方"的用法在中国很普及,即使是人名,也很普遍。而"小方八郎"是个体。
2.偷换论题,也叫转移论点。论证过程中所犯的一种逻辑错误。即在同一论证过程中不加说明地随意改变了原来所要说明的问题(包括对于论题的范围随意扩大或缩小)。
张钰等人声称要证明的论题是"方姥是川岛芳子",而事实上是在证明①川岛芳子逃脱死刑;②对川岛芳子的探讨。
方姥变得有其名而无其实,甚至证物是不是方姥的东西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即使是研究证物,也是建立在探讨川岛芳子的基础之上。
正确的做法是,他们应该先探讨方姥以及证物,对方姥及其证物都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然后再研究方姥是否与川岛芳子有关。
3.自相矛盾,即逻辑矛盾。思维过程中违反矛盾律的逻辑错误。即在同一议论中同时承认两个相互矛盾的判断都是真实的。
比如,①关于方姥的名字,张钰提供方姥没名。然而张钰又说她看过方姥的皈依证,在姓名一格里写着"方氏"。方姥又有名字了。
张钰再次提供,方姥在国清寺,都叫她"方居士",寺里的塔院存放的骨灰盒上写着"方觉香"的名字,我们通过三年的考证才知道方姥叫这个名。而王庆祥日记2008年11月25日记载,何景方接受采访时,从浙江国清寺回来,应该说是无功而返。都无功而返了,何来的方姥的名字是"方觉香"?
②张钰说:"姥爷指着墙上一幅画,让我拿下来包好,回长春交给我母亲保管,他说这幅画是方姥画给我的,留作纪念。"这幅画正是记者看到的《日本风情女子浴嬉图》。
然后张钰又说,段连祥示意张钰打开身边装东西的箱子,逐一交代,其中就有这幅《日本风情女子浴嬉图》。本来是挂在墙上的,怎么又飞到箱子里去了?
③张钰称,蝙蝠型头簪是银质的,"方姥平时别在头上,经常拿它挑菜中的东西,我怀疑她是在验毒。"而张钰对方姥的画像怎么都是短发似川岛芳子的发型。
④张钰说,于景泰带着段连祥去见一男一女两个人,当时就认出了川岛芳子。而后来又交代,女人半月后才亮出川岛芳子的身份。
4.模棱两可,对问题或事物正反两方面,持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
比如,①本来张钰对于皈依证上的照片,说"在2004年底段连祥去世后,随段的遗体一起火化了。"表示肯定。
但后来觉得不妥,所以又改口,"方姥去世后,姥爷舍不得她走,就把方姥皈依证上的照片拿下来挟在了自己皈依证后页,放在衬衣兜里,时常拿出来看。姥爷去世时,家里谁给穿的衣服我不知道。他的皈依证哪去了,我也不清楚,可能是火化时一起烧了。"表示不清楚了。
②对于秀竹其人,也表达不清晰。除了针对证物称"秀竹"其名,以及张钰交代的于景泰告诉段连祥可以称"秀竹"之外,此人都是以"七叔"、"七哥"、"七爷"身份出场。弄得秀竹来去无踪,很神秘。
对于张钰等人的逻辑错误,凡此种种,在此只举几例说明问题。
四、假命题举证的目的性
张钰等人举证这些假命题的目的体现在他们的需要和意欲之中,这种需要和意欲的满足回复了主观抽象与客观实在之间的和平。但是,他们所宣称的描绘得最完善的方姥或主观地当做真知识的证据只是预先假定的。这就是说,只被认作他们所潜在的主观思维与存在的这种抽象的同一,立刻就可由于两方的不同而变得对立起来。
方姥太像川岛芳子了,以至于她根本就不是川岛芳子。因为完善是创造出来的,或者说只存在于人的主观思维中。张钰确信"方姥就是川岛芳子"就是建立在意欲的基础之上的。
通过意欲复进一步充实这种确信,因为意欲的活动使得张钰根据读者的质疑对证词改来改去以示完善,使得主观的就仅仅是并永远是主观的与客观的就仅仅是并永远是客观的这种对立能成为事实。
意欲使张钰弄巧成拙了。所以那假定在先的命题对于张钰等人要实现的目的也只是一种观念性的自在不实的东西。目的通过这种推论方式能够否定矛盾对立而赢得它与它自己的统一,这就是目的的实现。张钰总是不断地在重复,"方姥是川岛芳子"是我姥爷交代的。然而问题是她姥爷过世了,死无对证。在这个推论的过程里,只是自己保持自己,自己与自己相结合。
由于目的的自我保持性,所以张钰的姥爷才是真正的原初。原初又属于那尚无法揭示出来的盲目必然性。因此原初便会过渡到张钰以及她所提供的证物,从而失掉其原来的原初性而成为设定的存在,且须依赖这些证物。而张钰的目的也仅仅通过推论的效果而实现其自身完整。
必须指出,这种寻求目的的方式,失去原初,不得不将证物作为达到目的的工具的做法,很容易使理性的人对张钰的举动进行反思。很容易看出,这种达到目的的办法既不能增进论证历史的真正兴趣,也不能增进科学论断的兴趣。可见,张钰等人的这种外在的目的性总是很令人失望的。
事实上把有限物证赋予了无限的观念恰恰是和存在的东西对立起来了。因为证物本身具有一种客观性,这客观性与张钰等人的目的并不同时相符合,而是有了差异。换言之,张钰等人赋予物证的那样一种观念或一种主观的东西,其物证本身并不包含存在。这种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即指出物证命题为不真,并指出这些推论乃是片面的,因而也就辨明了这种人为的同一就是张钰等人所需要过渡的,并期望借此可得到和解的一种同一。
张钰等人在实现目的活动所进行的推论里,为了使目的通过实现证物的可信性而与川岛芳子相结合。它一方面否定了表现在目的里的直接的主观思维,另一方面否定了表现证物的直接客观性。而把确信"方姥是川岛芳子"的精神境界提高到了神性的境界,它一方面否定了张钰自造的偶然,一方面也否定了它自身的主观思维。
比如,张钰交代方姥是站着死的。这确实是一个医学奇迹。这既不符合偶然需要(就是川岛芳子也未必需要站着死掉),而人类的主观思维也无法达到如此境界,太过神奇。段续擎,说有一次"方姨"带她去长春新立城水库钓鱼,都70岁人了依然身手矫健,能爬到树上大头朝下倒挂,就像会武术一样。
类似的还有一例,就是证人邹福山交代,七十岁的"方老太太"能"穿房越树,还能把狗提起,还能打鸟,在大水泡中用手抓鱼。也就是说,张钰等人对"方姥是川岛芳子"的信念已经超越了极限,即成为了一种信仰。
在这达到信仰阶段的概念或目的性里,"方姥是川岛芳子"只是一种观念,而信仰式的观念的本身就是不实的东西。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所提供的证物作为推论的中项,也不过是同时推论自己,即因为信仰(方姥是川岛芳子),使信仰存在于外物之中(所谓的"方姥的遗物" ),以形成其信仰的观念(方姥是川岛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