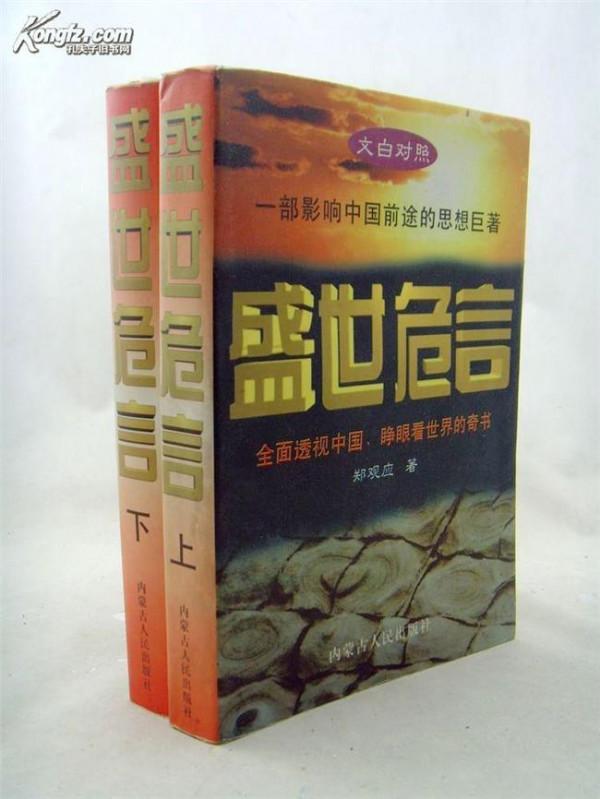孙立平的盛世危言 孙立平:为了理解世界局势的变动 澄清三个问题
美国退群,英国脱欧;盟友间烽烟四起,刚刚威胁互灭的敌手握手言欢;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合流,“建制”成为对立营垒新的界标;原有的规则很多被弃置,新的规则谁也不知是什么。
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这个世界会走向何方?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世界格局的这种变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试图通过对下面三个问题进行澄清,以求把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弄得更清晰一些。
第一个问题:在贸易战的云雾下发生的是一个过程还是两个过程?

要理解当今世界的变局,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当今世界在发生什么?说得具体一点,在贸易战的云雾之下,发生的究竟是一个过程还是两个过程?
弄清楚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我们要么会夸大了某些对立,要么会忽视了某些连结的纽带,从而导致对整个格局和走向的误判。

在6月10日的音频节目《特朗普四面出击意味着什么》中,我说过,从表面看,特朗普四面出击,到处树敌。这真的就是我们一些专家理解的策略上的愚蠢?即便是愚蠢,这个愚蠢是如何发生的?
要弄清楚,这个表象的背后是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两个互相交织但又不同的过程:一个是与逆全球化相联系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或贸易战;一个是准冷战或准冷战生成的过程。

不理解前一个过程,就不会明白美国在向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同时,为什么会对盟友也痛下杀手;不理解后一个过程,就不会明白美国与盟友为什么会不时联合起来对付中国。特别重要的是,不理解这两个过程的交织,会对当前许多重要的问题发生误判。
第二个问题: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狂热者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有没有第三种可能?
特朗普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究竟要干什么?他有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想法?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当今世界的变化,非常重要。很有意思的是,最近,美国《大西洋月刊》主编、曾提出“奥巴马主义”的Jeffrey Goldberg就发表一篇文章,讨论是否存在一种特朗普主义。
在国内,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大行其道的一个说法是:特朗普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专家们告诉我们,外交政策及国内事务处理上的经验,特朗普基本上是空白。他是个商人,他的政策也会受这一因素影响。他清楚中国的重要性,而他现在想做的就是去和中国达成一些协议,让美国在贸易和经济方面获得更多的利益。
他在思考的是在各方面与中国针锋相对的同时,如何和中国做生意能让美获利更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有利于中国,特朗普是那种可以和你坐下喝几杯聊聊天就能改变他的一些看法的人。
在5月22日发表的《特朗普就是个商人?想什么呢?》一文中,我写道:不错,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无论是在对于与中国的关系上,还是在国际事务中,特朗普都很少将其置于意识形态和主义的背景之下,很少使用意识形态语言,很少使用诸如主义这样词汇,而是就事论事,讨价还价,而且讨价还价的时候,像商人一样的认真,漫天要价,坐地还钱。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是,意识形态色彩的淡薄,并不意味着价值观的色彩不强烈。你可以说特朗普不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治家,更不是一个精神领袖,甚至都可以说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同时却不得不承认,风云际会,使得他他成了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甚至是一种文明的拯救者。这个价值观就是基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古典资本主义。
这里所涉及的实际上是一个看问题的框架的问题:要么是唯利是图的商人,要么是意识形态主义者,事情就这么简单?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淡薄的人有没有可能同时拥有强烈的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古典资本主义,甚至一定程度的保守主义,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理解特朗普的一把钥匙?
第三个问题:冷战一定是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发生?
在更早的时候,今年的4月9号,我还写过一篇文章,《班农主义是理解美国战略思想变动脉络的一把钥匙》。这篇文章想澄清的是另一个与之有着密切关联的问题:在有可能出现的冷战中,除了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会不会还有宗教与文明的因素?
讨论这个问题与下面这个观点有关。著名冷战史学家加迪斯表示:现在不是冷战,因为有意识形态才有冷战,而今天意识形态不是重要因素。他说,冷战不会到来,因为意识形态的因素消失了。但加迪斯的观点,在两点上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加迪斯是不是夸大了现实中意识形态的衰落程度,而忽略了近年来的再意识形态化过程?特别是,如果摩擦和对抗加剧,有没有可能导致意识形态新一轮的强化和复兴?第二,只有意识形态才可能构成冷战的基础吗?宗教与文明的会不会成为新的冷战中的重要因素?因为两者都代表着一种价值观。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出现亨廷顿文明冲突的那种情景:文明与文明的对立。但会不会出现这种奇异的冷战情景:在一方是以宗教为基础的文明,一方是意识形态?如果存在这种可能,其中就有很多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意识形态和宗教是两个很相近的因素,但其性质和特点是很不相同的。从历史的眼光看,两者恒久性的数量级就不同,意识形态是百年级的,宗教是千年级的。意识形态就是几代人的事,几百年过去,就是过眼云烟。而宗教所体现的深层价值却往往更加恒远、持久。当然,差异不仅仅是这个。
认识和澄清上面三个问题,对于我们理解当前的世界及其走势,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