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系统和谢志章 何家栋:关于小说《刘志丹》写作的前前后后
邢:何先生,这几年,看了不少您立足于思想文化前沿写的颇有分量的文章。当我听说您还是当年风靡一时的《把一切献给党》、《我的一家》、《方志敏战斗的一生》、《赵一曼》、《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等革命故事的执笔人时,非常惊讶。

按照现在的说法,您应该是家喻户晓的畅销小说家,我是看这些作品长大的。那时,怎么就没有听说过您的名字?当我听说您还参与了小说《刘志丹》的写作时,就一直想听您讲讲关于小说《刘志丹》的写作经过。这部小说从发表、批判、整肃、平反,是当代文学史中的一件重要事件,更是当代政治史上的重要事件。

何:当年写那些东西时,认为是在做着编辑的本职工作,从来没有想到要署名。不出名也少丢人。我干吗写这些东西?说来话长了。我在学校只念过五年书,抗日战争开始,就跑出来当兵了。我的文化知识,都是从文学作品和其他书本学来的,所以我说我是共产党扫盲扫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知学力不足,只能算个文学爱好者。

从来没有想以文字为职业。顾准说能添一粒沙就不错了,我连这点信心都没有。1949年刚解放时,我在工人日报社工作,是搞经营管理的。
比如你父亲(邢野)写的话剧《不上地主当》,就是在我手里印的,由“天下图书公司”出版。报社的工厂本来只印报,我把它改造成也可以印书,就大量承印外活,以增加收入,解决报社的经济困难。《工人日报》接收的是杜聿明的《新生报》。

《新生报》有一批原来的留用人员,本来是实行薪金制,因为,从解放区来的干部实行的是供给制,对原留用人员也实行了供给制。但是这种供给制,不管留用人员的家属。不像解放区来的干部,家属也是由国家供给的,孩子还给保姆费,多一个孩子就多一份供给。
这样一来,留用人员的家属就没了饭吃。当时我这个工务科的科长遇到的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有人因没了饭吃,要上吊。于是我就千方百计地想怎么赚钱,扩大就业,养活这些人。
解放初,财政经济非常困难,没有经费。那时穷到什么程度?明天就要出报了,今天夜里12点还没有纸呢!我骑着车到处借纸,或去买人民日报的下脚料。人民日报社用的是轮转机,他们的纸损耗量很大,印着印着就断了,我们是平版机,就把他们的断纸拿来裁好,印我们第二天的报纸。
有了这些纸的来源,我又找些客户到我们这里来印书,印报、印文件,顺手做点纸张生意,好赚点钱。最大的客户是华北军区,我们把他们全年的任务都包了,一次弄来几百万。
这就是为什么说你父亲的书,是经我手印的。接着就自己编书,干起了出版业务。对内,我那个科叫出版营业科;对外,是工人出版社。开始是印些识字课本,不是搞工人扫盲运动嘛。最初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发行,就是我一个人在搞,一天工作15、6个小时、甚至工作20小时。那两年,我好像没有在床上睡过覚,累了就在地板上、板凳上躺下歇一歇。
邢:解放前,您是做什么工作?
何:抗战胜利前后,我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办报纸,出刊物,搞出版社,归晋察冀军区城工部文委领导。我也就是这个时期学了一点知识。国共和谈时,周扬到了北平军调部,那时我在中外出版社负责出版业务(地点在西长安街,三层楼房已经拆掉,原址就是现在的电报大楼),周扬就把延安出版的《白毛女》、《李有才板话》、《中国通史简编》等,拿来交我翻印。
我自己也从解放区报刊上选了一些材料,编了几本书。那时中外出版社有个中共支部,创办人如孟用潜、孙承佩等,都是在北平美国新闻处任职的共产党员。
这个出版社承担着两大任务,一是推销翻印解放区出版物,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都各印了一万多册;另一个任务,是为解放区的机关、学校提供国统区的报纸、刊物和图书。
国共和谈破裂,军调部解散,叶剑英、周扬撤回延安。中外出版社先是我和其他四位同志被捕,出狱后,出版社又被查封。我回到解放区,到华北联大行政学院学习。后经周扬点名,分配到华北新华书店。
以后又分到《新大众报》做助理编辑。从大公报、文汇报来的名记者,在《新大众报》也只能当个助理编辑。这个报纸是给农民看的,要“大众化”,就是把中央文件改写成农村黑板报那样的豆腐干文章,觉得这些城里来的知识分子只会“化大众”,不懂“大众化”,先得练练基本功。
天津解放时,我被抽调到天津参加接管,就留在天津军管会新闻处工作。《新大众报》原班人马则进入北平,改为《大众日报》;以后又改为《工人日报》,由华北局转归总工会领导。
当时的情况是:从农村来的同志对城市感到非常陌生,从华北联大来的十几个知识分子对经营管理又不熟悉,因为我曾经在北京做过出版工作,熟悉编辑、印刷、发行、全部业务,所以,又把我调到北京的工人日报社。到了工人日报社,我就成了报社工厂的第一任厂长,叫工务科科长兼厂长。
如前面所说,逐步地出版业务有了发展,经济情况也好转了。这时我又成了工人日报的出版营业科科长,招了两三个人,当校对、跑发行,接外活,还不算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出版机构。赵树理是和我们报社一起进的城,在报社住着,供给也在报社领。
我就说,让赵树理当工人出版社的社长吧。出版社的广告就这样写了,也没有人来问,我们也没有到上边什么部门登记。当时组织方面的游击作风可见一斑,赵树理这个第一任社长,竟然是我这个科长任命的。正式打出出版社招牌后,我们出的第一本书是《论人民民主专政》;第二本书是赵树理写的《天下工人是一家》。我那时就是拼命想办法赚钱,好改善报社的经济状况。
邢:赵树理的小说,最早也是在工人出版社出的?
何:是啊。像《登记》、《邪不压正》呀,《石不烂赶车》等,都是工人出版社出的。这里有个小插曲。新大众报社长是王春,也是大众化的主将,他的旗下有赵树理、章容、苗培时等人,入城后住在西总布胡同,工人出版社的创办当然得力于他们的扶持。
工人日报编辑科长苗培时外号叫“苗大鼓”,常把英雄故事写成鼓词,对推动大众文艺不遗余力。他还把老舍、赵树理推到前台,办了个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编了个刊物《说说唱唱》,还办了个出版说唱通俗文艺的“宝文堂”(出版社),通过货郎担子给农村提供演唱材料。
一时名声大噪。作家协会在东总布胡同,虽与西总布胡同这些人比邻而居,双方却是格格不入,西总布胡同认为东总布胡同是“小众化”;东总布胡同认为西总布胡同只会写“一脚落在流平地,一脚落在地流平”,登不了大雅之堂。
赵树理将田间的长诗《赶车传》改写成说唱《石不烂赶车》,苗培时将孔厥、袁静的长篇小说《新儿女英雄传》改成“评书”,就有出他们洋相的意思。
但赵树理的移植确实别开生面,苗培时的改编,若放到现在,恐怕要打版权官司了。当时没有什么版权观念,一切作品都是“公产”,都是图解政治的宣传品,就像马克思说的,每篇文章都只有广告水平。只要能起到宣传鼓动作用就行了。
东总布胡同和西总布胡同的矛盾,在推荐“斯大林文艺奖”作品提名时达到顶点。东总布提丁玲,西总布提赵树理,相持不下,周扬建议双方在作协开会解决分歧,最后将赵树理调到作协,才把问题解决了。赵树理走了,工人日报社长王春正式调任出版社社长,我任办公室主任。
工人出版社从工人日报独立出来,迁往北新桥骆驼胡同。不久王春病故,苗培时离开工人日报,成为专业作家,落户煤炭系统,陆续又创建了煤炭文艺基金会,通俗读物出版社,农村读物出版社,农民日报,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朋友们笑他是文化流寇主义。这样的热心人现在很难找到了。
此时的工人出版社已初具规模,但还是由我支撑门面。我们对东西总布的作家始终一视同仁,既出版说唱、相声、小品、连环画,也出版周立波、草明及其他青年作家的小说和诗歌。
工人出版社就这样发展了起来,出了很多书, 赚了一些钱,买了工厂,盖了大楼。有了点钱,有人就眼热了。 到了1952年“三反”、“五反”,就想借运动把我拿下来了。
他们知道,我曾用大卡车往王府井银行拉票子,几百万,还能不是个大老虎?于是立案审查。他们查了个底朝天,发现我批了个条子,借给一个作家500元钱。这钱当时不是个小数目,恐怕比现在的5000元还多。可是会计发稿费时,本应该把借出的这笔钱扣下来吧?没有扣!
社里派人询问,那个作家说不记得了。可财务上有我的批条。我说,我要贪污,写那个条子干嘛,给人留下把柄?后来上面说,不算你贪污,你把这钱退赔就是了。我就到处借钱,退赔了。
没有查出一文钱的问题,却查出我私人送给客户一支派克笔。那个同志签字时没有笔,我把我的笔给他使,不好往回要。他们就说我是“行贿”,是“资产阶级经营方式”,批得不亦乐乎。
我因此得到一个教训,从那以后,再没有批过一次条子。“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是终生怕井绳,还是很有记性的。
经济上不能整倒我,又有人说我来路(历史 )不清楚。你看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知道,毛主席最担心“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怕坏人混进来。山沟里的人也不理解:你没有分到房子没分到地,不缺吃,不缺喝,跑到解放区干什么?动机不纯!
你1938年参加抗日,是不是个脱党分子?你在北平被捕,是不是个叛徒?送你参加八路军的人在哪里(一时找不到)?是不是你出卖了那个同志?我就成了一个来路不明,历史不清的政治可疑分子,这种人,自整风以来,每次运动都要拿出来斗一斗。于是,不但把我罢了官,还把我的党籍给开除了。我被一抹到底了。经济问题搞不清,就搞你的政治问题。
尔后,全国总工会把文教部端过来,让文教部的部长、副部长,分别做了出版社的社长、总编等。这些人接管了我一个人的工作。算是名正言顺地成立了工人出版社。各处各室也都派了人,就是不给我工作。山沟来的人说,叫这小子起来就没有我们的活路了。他们怕报复。可见我当时多么霸道,因为任务太重,搞强迫命令,得罪不少人。
我被罢了官,让我到校对科。也不是做校对,也不算是当编务。搞的是标字号,设计版式一类的工作,没有什么名义。我心里当然有气。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就是在这个时候写出的。出版社并没有给我任务,我是自己找上门去的。
吴运铎在俄专学俄文,准备出国,我就利用中午间隙,到俄专操场球架下等他,他口述,我记录,回来再整理。这本书一出来,一炮打响,发行了几百万册。出版社赚了一笔钱。这本书,在社会上影响本来很大;但除了韦君宜写了个评介,文艺界不承认它是文艺作品。
我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周扬叫《文艺报》关心一下,冯雪峰就请杜鹏程写了鼓吹的文章。紧接着,送我参加八路军的那个同志,从上海找我来了。我带他找到我们社长,让他讲讲我的情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把我如何参加革命的情况以及如何与我失去联系同我们领导谈了。政治问题算是清楚了,才给我分配了工作。因为写了那本书,因人设事,社里成立了一个文艺组,叫我当副组长(没有组长),就把我挤到文学这条羊肠小路上,以后就搞了一系列的革命回忆录。
《刘志丹》,是我到文艺组后,提出一系列革命回忆录选题中的一部。这个系列选题中还有《赵一曼》、《杨靖宇》、《方志敏》等等,我列了几十个人。但是刘志丹一直没有找到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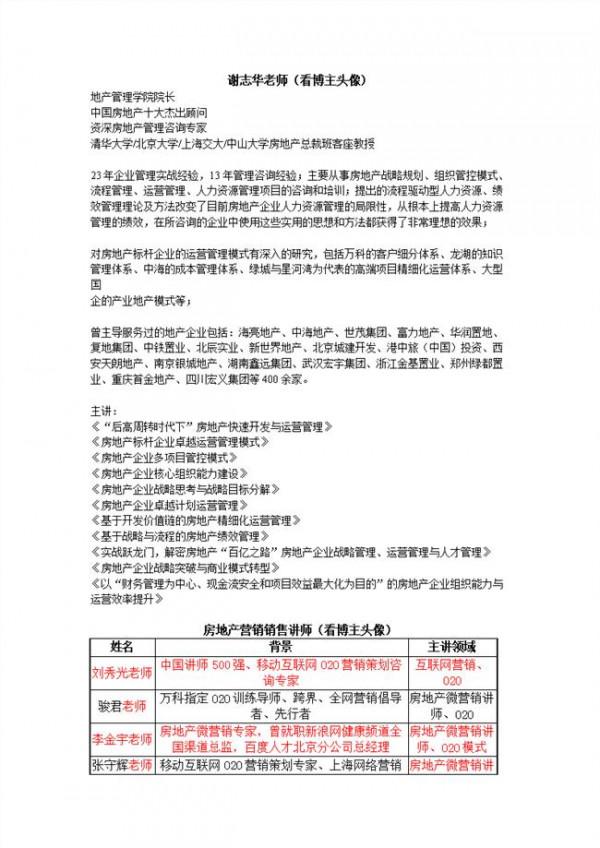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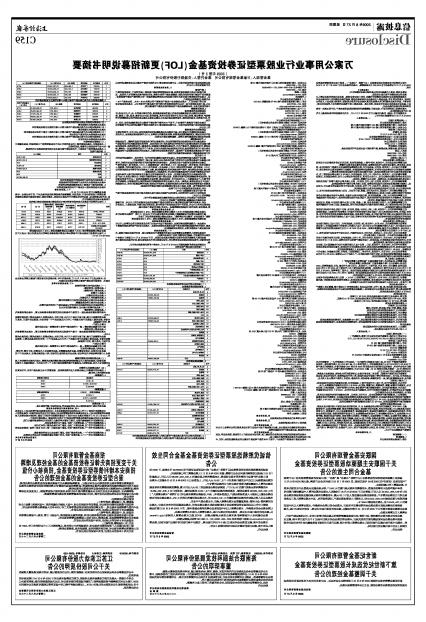

![>谢志强局长 谢志强[江苏溧阳市卫生局局长]](https://pic.bilezu.com/upload/4/62/462e74c9d6568e057afca93c9b29a5e9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