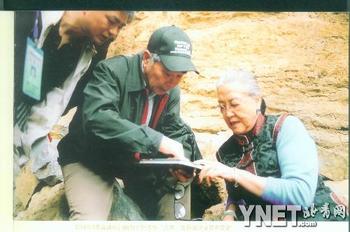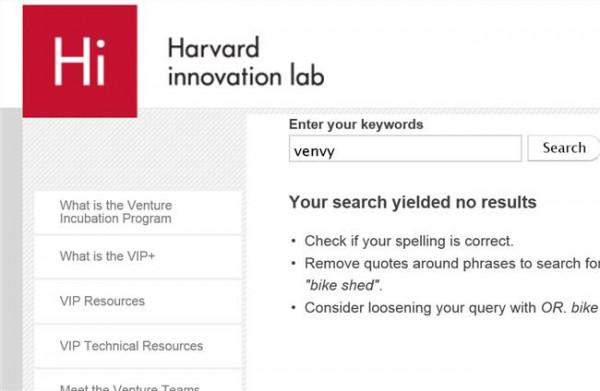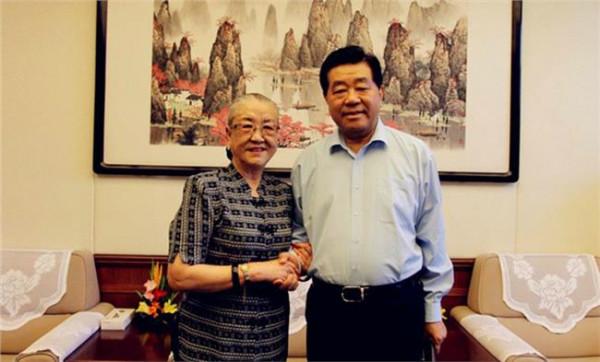耿飚女儿耿莹 女儿揭秘原国防部部长耿飚一生的大遗憾
核心提示:“1932年部队缴获了五六个相机和全套的冲洗设备。他拿着银元到照相馆去,让师傅教他照相,师傅就把全套都教了他,从此他一路照相,长征全程他都记录了。”“斯诺写《西行漫记》的时候,收集资料,问他要,他不给,后来上级只好下命令要。后来这东西就没还回来,成为他一生很大的一个遗憾。”
耿飚长女耿莹,小女耿焱,一位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的理事长,一位曾求学于哈佛大学、在香港城市大学任教。无论现在做的是什么,在均已年过花甲的她们看来,父亲并不遥远,永远都在那里。
“无所畏惧的领导”
在耿焱家中保存着一本珍贵的影集,是一个美国友人送给耿飚的。这本影集的第一页就是一张耿飚与一位美国军人的合影。
这位军人就是耿飚从延安奔赴抗日前线时护送到晋察冀去的美军观察组组长德穆克上尉。1988年5月,已经成为美国政府顾问的德穆克随一个美国商务代表团访问中国,派人将一张名片送给耿飚,要求与他会面。此时的耿飚正忙于其他活动,未能抽空与德穆克见面。德穆克在归国前托人转来一本影集,扉页上方用英文写着:“送给无所畏惧的领导——耿飚。”
时间追溯到1944年9月。耿莹说:“那时有个美军观察组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去考察,父亲率部队护送。美国人习惯了坐车,不会骑马,我们哪有汽车啊?骑不上马就骂人,一路上笑话很多。”
一路上,这些美国人架子大、脾气大,他们把警卫当做他们的勤务兵,埋怨他们照顾不周,甚至提出要吃西餐。
让耿飚头疼的是,这些美国人不仅不会骑马,连从哪边上马都不知道,总有人从马背上摔下来。于是,他们就抽打牲口。
耿飚没办法,只好决定每两个战士保护一个美国人并教他们学骑马。几天后,他们的骑术大进,每当宿营下马后还拍拍马脖子、吻马脸,竖起大拇指夸这些马“顶好”。
美国人对中国的事物充满好奇。路上过一辆牛车,他们也要停下来围观,拍照,嘴里发出“噢、噢”的惊奇声。他们还经常会问“妇女为什么不搽口红”、“老太太脚是怎么变小的”这类问题。
耿莹说:“父亲说,接近黄河时,天空开始出现日军飞机。对我军来说,行军路上遇到空袭,只要指挥员一声令下,几分钟内就会疏散隐蔽完毕。”
然而这些美国人一听见飞机声就乱了套,先是指着飞机大喊“在那边”,然后就策马乱穿,把他们的大衣、行囊扔得遍地都是。战士们解释“那是侦察机”,可他们听不懂。
几分钟的骚乱,常常得花一个小时才能收拢队伍。有的人骑马跑出好远,有的钻到灌木丛里、庄稼地里,找都找不出来。警卫排的战士们不得不到处去找他们丢失的零星物品,大到电台部件,小到项链、十字架。
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德穆克曾问耿飚:“我们该怎样评价这次伟大的冒险?”耿飚想起在延安学习时常用的一句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他回答说:“无所畏惧。”德穆克向他的同伴们转达了这个词,引起一阵低低的“噢!”“OK!”
从此,他们便把这次行军称做“无所畏惧行动”,把耿飚叫做“无所畏惧的领导”。
女儿眼里的耿将军
耿飚的长女耿莹现在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挽救。作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的理事长,她花费了长达4年的时间才拿下批文。“基金会的作用就是唤醒大家:老祖宗的东西不要都破坏完了,要留下来。”
耿莹说,正是父亲让她懂得了什么是“文化”,懂得了什么叫“遗产”。
“和平解放宁夏的前夕,我父亲在前线,我跟在他身边。那是在一个破庙里,我发现父亲手里头有一大张地图,上面用红蓝铅笔作了标记,蓝颜色的圈圈,还有红颜色的箭头。我就问爸爸说蓝颜色的是什么?我爸爸说是我们的炮口啊,我说那为什么不打啊?爸爸也在发愁,指着地图说:你看看这里头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古物。”
耿莹说:“你看他们一边打仗,一边还想着给后代留下什么。现在还有没有哪个干部心里想着要给后代留下什么?拆一片和建一片,天壤之别!”
与姐姐耿莹一样,耿焱认为父亲的爱好特别多,而摄影这一爱好贯穿了父亲的一生。“1932年部队缴获了五六个相机和全套的冲洗设备。他拿着银元到照相馆去,让师傅教他照相,师傅就把全套都教了他,从此他一路照相,长征全程他都记录了。”
“斯诺写《西行漫记》的时候,收集资料,问他要,他不给,后来上级只好下命令要。后来这东西就没还回来,成为他一生很大的一个遗憾。”
耿焱说,“长征沿途的照片,包括过雪山、草地,照片都被斯诺拿走了。父亲从来没间断过找寻,解放后,他通过外交部找了斯诺,斯诺说给了丁玲,让丁玲转交。但是当时丁玲已经在农场劳改了。后来他又找了农业部,农业部就派人到丁玲的地方去问她,丁玲说‘我的东西都不知道哪儿去了,肯定没有了。’”
在耿焱的记忆里,父亲对一样东西保存得特别好,那就是他的党证。“那是他在江西苏维埃政府的时候组织上发的。当时就那么一两年发过党证。他保护的别提多好了,拿个塑料布包着,长征期间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被水洇过,里面交党费的签字都清清楚楚”。
无论是耿莹还是耿焱,对父亲的爱都被埋藏在心底。当被问及“现在想起父亲时,会出现的是什么样的场景?”耿莹说:“我有烦心事的时候会在他坟前和他聊聊天。我觉得我父亲好像没死,在什么地方等我。我一定要去找他。”
“前些日子去参加革命前辈、开国少将陈锐霆伯伯的葬礼,他今年(指2010年——编者)6月13日去世,享年105岁。我看着满墙的照片对他女儿说:父亲陪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我们老了父亲才走,这是我们一辈子最幸福的。我也跟陈伯伯说,如果见着我父亲,给他带个好。”耿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