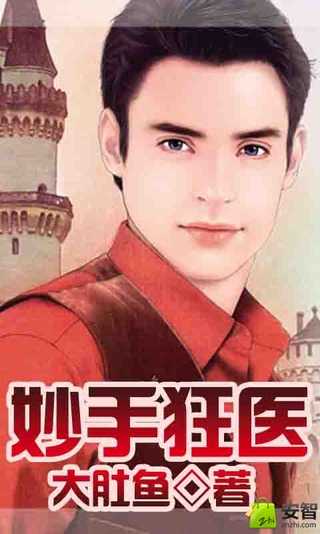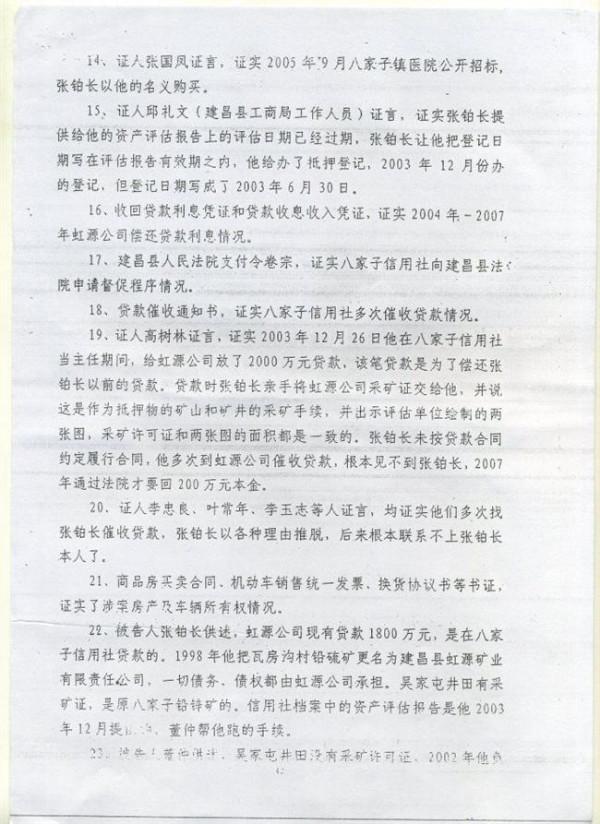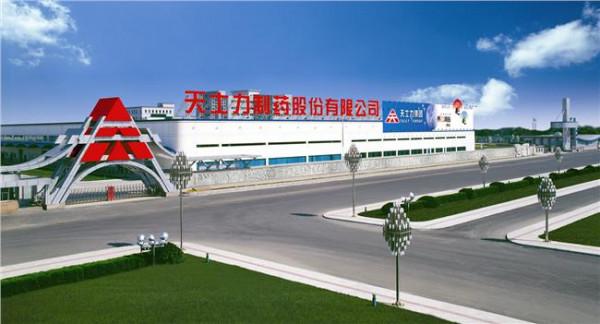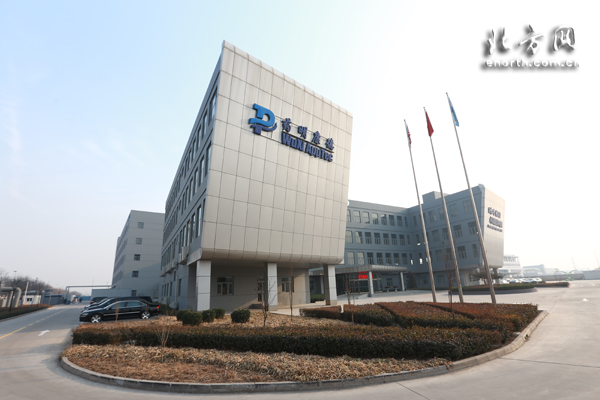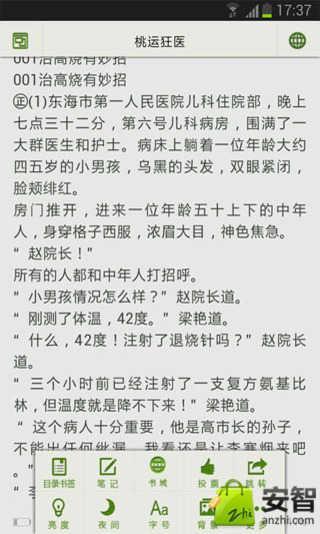张建明中医馆 张建明:狂医的“幸福”生活
“论临床实战能力,就广度和难度而言,我是国内中医第一人;但是就学术功底和素养而言,不能够与硕士、博士相比,更与全国‘十老’相去甚远。”这话前一句可谓狂傲到极点,后一句也算谦虚得可以。
著名散文家何为在上周的《新民晚报》上以“千载难逢”为题,记述了他对怪医张建明的印象。南方某报的记者这几天在蹲点采访张建明。电台、电视台及不少平面媒体纷纷聚焦于张建明。为什么?就因为他的“狂”,他的“怪”?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他在为病人号脉处方,不会相信面前颀长瘦弱、文质彬彬、学者气度的人是一个已出道31年的“老”中医;
如果不是亲耳听见他说“狂言医百病,样样不包治”,无法形容他的张狂;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他在言及母亲时的潸然泪下,难以窥见他的侠骨柔肠。
如果……不会……
将临知天命之年的张建明可在这里面做的填空实在太多……
生命不息看病不止
每天清晨太阳刚刚露出完整的笑脸,一个身材消瘦、戴着眼镜的男子就会穿过嘉定繁华的城中路,在人民街拐个弯进去。男子总是行色匆匆,如果你正好和他迎面而过,就会发现在他紧锁的两道浓眉之下,一双炯然有神的眼睛诉说着他正在思考某些极为复杂的问题。路边琳琅满目的橱窗一个个从他的身边退去,然而男子从不侧脸瞧它们,花花世界对他来说是过眼烟云。
男子拐进人民街,“张建明中医工作室”的牌子就出现在眼前。男子进中医馆,稍作准备后,就落座在诊室里那张黑色的“专用椅”上,赶紧将路上思考的心得记录下来,凝神冥思。不一会儿,就有病人来到中医馆,进门和他打招呼:“张医生,早!”
他就是张建明,一天的工作也由此开始,或者说,张建明一天的生命由此开始——中医就是张建明的生命,张建明对它的热爱已经溶于血,化入骨……
所谓张建明的“幸福”生活,无非就是他视诊治病人为他的至高欢乐;离开对医学的探究,他的生活会变得毫无意义。
通常,在诊室的那张椅子上,张建明一坐就是一天,从早晨第一个病人进门,直到最后一个病人抓完药离开。对张建明来说,休息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为了看病,他常常忘记吃饭,有时候饿得实在不行,就用白饭就着“方子”匆匆果腹——吃饭时仍不忘在草稿上比划药方,似乎中医真的成了精神的“食粮”。张建明也没有下班的概念,病人什么时候看完,他就什么时候下班。因此,晚上十一二点钟中医馆仍然时常灯火通明。有时,甚至到第二天的凌晨四五点,才看到张建明拖着疲惫的身子慢慢踏着最后一点的月光和东方微白的曙光回家去。三个小时后,他又会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中医馆里。因为劳累,张建明越来越瘦,并且患上了严重的痔疮。给病人看病时,往往一边给病人号脉,一边鲜血染红了身下的椅子。然而张建明可以不动声色,持续把病看完,然后起身,走到休息室换上一条备用的裤子,又若无其事地继续为下一位病人看病。
“你是医生,为什么自己不调理自己的身体呢?”记者问。
“我无暇调理自己,我只求温饱。我将我所有的时间都给了中医和病人。”张建明的回答十分简单,然而字字震撼着记者的内心。
从十几岁开始接触中医,张建明就一直站在中医临床的最前沿。虽然受时代影响,张建明没能甫从初始就接受正统中医教育,但是他凭着天赋和后天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进修,已经从乡镇医生成长为中医界的一枝奇葩。“没有临床实践,中医必将名存实亡。
”张建明说。所以他每天都在看病,只要一天不坐在中医馆的那个专用椅上,张建明就觉得手生心慌,找不到感觉。也因为大量的实践使张建明很早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34岁时,他成为本市青年医生中惟一获得首届“十佳”称号的中医师。
34岁,对于“四五十岁始入门、六七十岁渐得道”的中医学来说,是多么难得。以至于一位著名的中医大师在看到他的方子和论文时,竟断定乃出自耳顺之年的老中医之手。谈及此事,张建明傲气顿生:“这就是我狂放的资本。
别人四五十岁始入门,我却能在三四十岁渐得道,凭什么?凭的是我的天分,更凭我的呕心沥血!”张建明对记者算这么一笔账:别人一天8小时工作,他一天16小时甚至20小时高强度运作,他的一天等于别人的几天,所以虽然他现在只有47岁,但是按照医龄算,他足已堪称“老中医”了。
然而即便如此,张建明仍然觉得时间流逝得太快,他必须利用一切时间的缝隙来参悟中医。1992年前后,临床积累了相当经验的张建明开始将他对中医的研究方向从呼吸系统疾病扩展到各种疑难杂症、怪症和癌症上,特别对顽固性咳嗽、哮喘、肝肾顽病、心脏病、重度肺气肿、肾功能不全、心肝肾顽病、心脏病、顽固性失眠、头痛发热以及痤疮等各类疾病都颇有治疗心得,而他运用中医理论针对癌症的疗法,都取得较好的效果。记者惊讶于其所涉猎的疾病治疗范围竟然如此之广,是现代西医难以想象的,张建明意味深长地告诉记者:“中医和西医是不同,西医重病,而中医重人。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自然而然地担负起向人身上各种疾病挑战的责任。”张建明说到这里:“试问天下为中医事业如此振臂呐喊者,舍我其谁?”张建明的浓眉一挑。
振臂高呼不难,难的是埋头苦干。每天20几小时,张建明不是在看病,就是在思考和中医有关的问题,“对中医的思考贯穿在我醒着的每分每秒,骨子里散发出的都是中医的思维。”张建明指着自己宽阔的前额,严肃而又自豪地说,“我想我恐怕已经患上了‘思索癖’。”于是,在街道路旁进进出出之间,路人总会看到一个拿着录音机、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的怪人。“就是我啊,”张建明用手指指自己说,“随身带个小录音机,已经成为我多年的习惯。”张建明的大脑是一台24小时不间断运作的“电脑”,这台“电脑”不断地接受新的病情讯息,同时输出旧的病情内存,进行着比对和对接,从而寻找新的诊断方法。有时在半夜里,灵感忽然在张建明的“电脑”闪现,张建明就会迅速按下枕边随时待命的录音机的录音键,把自己的灵感源源不断地说给录音机听。小小的录音机是张建明的聆听者,不仅聆听张建明的灵感,也聆听着他对中医的痴心一片。
张建明对自己有这么一番评价:论临床实战能力,就广度和难度而言,我是国内中医第一人;但是就学术功底和素养而言,不能够与硕士、博士相比,更与全国“十老”相去甚远。此话前一句可谓狂放到极点。但是张建明的狂放讲究理由:“也许我以后会写一本划历史的中医著作,这也是我的理想。但不是现在,著作等身并不是中医的目的。现在,我要为病人看病。”谈起不少西医甚至同学科的中医专家对他的质疑,张建明自信而又平静地说:“如果我的张狂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进而激发大家对中医的热爱、研究,此心已意足矣!”
我应该谢病人
家住宝钢的孙丽娟女士最近神采奕奕,每天下午下班后她总是准时到家,与家人其乐融融地吃晚饭,然后洗碗、洗衣,看电视,最后上床睡觉。旁人可能觉得奇怪,这样的生活再普通不过了。可是,对以前的孙丽娟来说,这样生活简直是一种奢侈。顽固性哮喘病曾经像影子般纠缠了她20多年,看遍中西医,却仍然无法摆脱。“特别到了天冷,一到晚上就不能睡,睡下就喘,一喘就不能止,只能送医院输液。有时候输完液回家,躺下不到半小时又犯,只能再到医院输液,把我和家人都折腾得不行。”孙女士这样告诉记者。于是在去年年中,她踏进了张建明中医馆的大门,“已经20多年了,我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就算死马当活马医吧。”
“张医生一声不吭,听我把病史说完,然后开始帮我把脉看病,”孙女士说,第一次看完病,她就带了满满一大包中药回家。说到张建明开的药方,孙女士忍不住咯咯笑:“我听说张医生擅开大方,没想到他真的一下开那么多药。”回到家,孙女士不得不用32号的特大号锅才把药煮好,喝完那锅苦得挖心掏肺的中药后,倒出来的药渣,竟然装了整整两大垃圾袋。
但是第一帖药8天的疗程没有效果,孙女士的病仍然要发作。于是又开了第二帖,还是不见效。孙女士有些着急,她问张建明:“怎么没有效果?是不是还是看不好?”张建明什么也没说,只是很认真地问:“你相信我吗?相信我,就再试一次。”孙女士被张建明的认真和自信打动了,于是再照新药方吃第三帖。果然,第三帖开始,居然平喘了。继续服用,效果越来越明显,现在,孙女士已经连一直随身带的救命喷药都用不上了。
“病人说遇到你这样的医生是福气呢。”记者把孙女士的话转述给张建明。谁料,他眉毛一挑,大手一挥:“凭我现在的水准,治好这个病是应该的。我的特点就是敢于下药、诊断务精。不要谢我,要谢就谢中医!”
是的,张建明是狂放的。其大胆的创新理念让人惊叹。问张建明为何如此“胆敢”,他说,在他的观点里,中医学家必得具有“杀性”,才能在与病魔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取得胜利。“中医是天生的斗士,斗士怎能没有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狂放呢?所以,没有‘杀性’的中医谈不上是对病人负责的好中医。”
熟悉张建明的人都知道,张建明在为病人看病时,是怎样的神采飞扬!用他学生的话来讲:“真的就像拍电影一样精彩。”聆听病情时的全神贯注,号脉诊断时的凝神专一,下笔开方时的冥思苦想,面对疑难顽症苦思时的自言自语,甚至怒发冲冠,都活生生地上演着一个现代的中医斗士奋力勃发的镜头。此外,张建明更是战战兢兢地把每个药方都看作决定自己命运的高考考卷,决不允许丢失半分。他甚至会因为一张方子中有一味药“重味”,而对一时疏忽的学生拍台子大骂。诊断疑难杂症时,张建明开方子都要打草稿,这是古今中外的中医都没有的。而这一切,最后都将在病人治愈后那发自内心的展眉笑颜中得到慰藉和升华。每当这时,也是张建明得以长吁一口气的片刻。
“治好的病人总是对我千恩万谢,其实应该是我谢他们啊。”张建明又口出惊人之言:“作为医生,首先理应对生命有种敬畏感,本能地想把病人的病看好。所以,当病人无条件地信任你,将健康和生命托付给你时,你实在应该对他们表示感谢啊。”说到这里,张建明感慨万千:“大概是我已经对诊治疑难杂症上瘾了吧,每看好一个病人,我的生命就会随之达到愉悦的境界。”
于是,在张建明和病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而微妙的关系:他们是医生和患者,同时也是比肩作战的战友,而“信任”就是维系他们的纽带。曾经有一位母亲带着女儿上门求医,女孩患的是闭经,用尽各种手段治疗仍没有起色。
张建明对母亲说,这个病,你给我三个月时间,如果有效,就继续治疗;如果无效,那么就另找高明吧。三个月后,病情没有改观。但让张建明感动的是,这位母亲十分信任他,竟然主动提出继续治疗。这让张建明的责任加速提升,费尽心机重新改进药方,终于在10天后,女孩的月经恢复了正常。
此后又观察了1个月,女孩的身体状况已与其他人无异。母亲当然对张建明感激不尽,但是张建明更想说的却是对这对母女的感激之情——如果没有她们的信任,仅凭他单枪匹马,任他神通广大,对病情也无济于事。
“我从不避讳这样讲:病人带给我很多,名、利、乐,尤其是让我治病的快乐!我又怎能不感谢他们呢?”也许只有狂如张建明者才会讲出如此直白而惊世的言辞来吧。
随着张建明的名气越来越响,上门求医的人也越来越多,病人中甚至有了中国港台澳地区、加拿大、美国和日本等海内外各地的病人。他们中有的是让翻译陪同而来,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信任和期待之意跃然脸上。于是,张建明给自己添加的压力更大了。在子夜时分,张建明会无声地流下泪水,这些泪水不是因为加在他身上的压力,而是因为那些曾极度信任他,而他却没能挽留住他们生命的病人。想到他们,张建明就只能任凭泪湿满襟。他恨,恨自己仍然无法攻克那么多医学顽症;但同时,他也发狠,狠狠地告诉自己一定要加快自己接近中医精髓的步伐。
狂放下的柔情
张建明说,中医本身充满着灵性,体现着国学思想,讲究儒、释、道,所以真正的中医必须有诗人的性情和情怀,讲究联想和灵感,拥有形象思维。没有这些,不能成为好的中医大家。文人都说他有诗人之气质,然记者却认为用智者来形容他也许更贴切些。有名家曾评价张建明:你不像中医,中医不像你,但你就是中医。的确,在张建明身上流淌着的血液中,有中医的痴迷,有斗士的凶猛,有学者的狂放,有诗人的侠骨柔肠,也有哲人的思辨……张建明,天生就是这些角色的混合体。又或许,一个真正的中医就该是这样一个充满个性的、有棱有角的混合体。张建明就这样毫无扭捏地将他的爱恨情仇展现在我们面前,开启他在医生和斗士之间的角色之门。
张建明是文人。踏进他的中医馆,就会感受到浓浓的书卷气:古色古香的诊台,静静伫立的书橱,还有墙上中医界老前辈的题字,这让候诊的病人完全体会不到身处诊所的压力。候诊室的一隅整齐地放着伞架、鞋刷等生活用具,充分体现出中医馆主人在细节上的人文关怀。
拾级而上,是中医馆的药房。药房门楣上方写着“永珍堂”三个字,是张建明用以怀念他的母亲。
说到母亲,张建明那犀利的双眼顿时变得柔和而温情,并用他娓娓的叙述,表达他对母亲的深情热爱和无限追思。张建明说,如果没有他母亲,就没有今天的他。5岁守寡的母亲独自抚养他成人,从不让他受一点苦。即使自己的衣服缝了又补,但穿在张建明身上的衣服却总是整齐干净;即使自己有一顿没一顿的,也绝不让他忍饥挨饿。母亲的恩情他长记于心;而更令他永生难忘的,是母亲对他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张建明永远记得他从安徽出诊回来的情景:那天他一回到家门口,就累得晕倒在地,母亲把他抱到床上。醒来后,张建明问一直守在床边彻夜未眠的母亲:“中医的道路那么苦,为什么我当初学医的时候,您不拦着我?”母亲深情地看着他说:“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啊!”短短的一句话让张建明哽咽着久久说不出话来。这就是他的母亲,目不识丁的母亲,却早已将儿子的远大心胸洞悉透彻。言至此,张建明不觉黯然。双手合十,默默祈祷,希望乘鹤仙去的母亲能够看着儿子实现他的理想,以及他竭尽全力荣耀地走入中医历史的决心。
张建明也是有情有义的男儿郎。他为中医奉献一切的精神使他和妻子白头偕老的梦想难以实现,他一直内疚在心。“这个世界本来就只能有取有舍,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当我决定奉献中医事业时,势必得以损害我的婚姻作为代价。”
结婚时,他们是青梅竹马,珠联璧合;15年来,也是夫唱妇随,从未红过脸,妻子对他的事业更是全力支持。让张建明特别感动的是有一次他参加一个会议,和几位中医一言不合,拍案而起,结果张建明拂袖而去。回到家中,一向怪他脾气差的妻子得知此事后,居然笑眯眯地对他竖大拇指,赞扬他“说得好!”着实让他对妻子刮目相看。
但是,15年里,张建明没能带妻子看过一场电影,逛过一次街,甚至他自己也放弃了年轻时的所有爱好,乒乓、游泳,连亲友的婚庆喜事都一概不去,他的眼里惟中医而已。妻子的朋友对妻子说,你嫁的不是丈夫,是中医啊。“虽然感情不在了,但我还是要感谢妻子在过去15年来对我的关怀和支持;还有对我病人的无私奉献。”张建明这样说,惆怅是难免的,但更多的是一种欣慰。
张建明也是侠骨仁心的侠士。因为从小困苦,尝过艰难的滋味,所以张建明直到现在都见不得旁人困苦。他向记者说起两件小事:有一次,一位大妈到中医馆来看病,号脉卷袖口时,大妈不小心露出里面的棉毛衫,袖口都已经破成一丝丝的。张建明在一旁瞧见,心里咯噔地震动了一下,嘴上仍然和大妈打趣:这么旧了,还穿呐?只见那位大妈很不好意思地把袖口缩进去,什么也没说。随后张建明为她看病开方,等大妈抓好中药最后结账时,张建明告诉收银员,大妈的诊疗费都免了。“中医馆有这个规定,可以凭有效证明减免医疗费。但是这位大妈还要用什么证明吗?她的袖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还有一次,张建明在路上走,忽然见到几个警察在抓一个违章骑车的三轮车夫。眼看警察就要抓到了,那个车夫也许怕警察抓住他罚款,于是跳下车子逃走了。警察就没收了那辆三轮车。当时看到这个场景,张建明并没有多想,直到几分钟后,他在车子被收去的那个机关门口看见车夫正坐在地上,一脸的茫然和不知所措,张建明心生不忍:“也许三轮车就是他赖以谋生的工具呢。被没收了,他拿什么生活?”于是,根本没多想,张建明本能地走上前去,从口袋里摸出钱,塞到车夫手里,对他说:“违章骑车是不对的,你拿这钱去把罚款交了,把车拿回来吧。没事的,明天就好了。”说完,转身离开。
在张建明的眼里,这些人和病人一样,是弱者,需要受到保护。也不知为何,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潜意识地激发张建明研究中医医术的决心。
因为名声在外,张建明从不乏一些“傲慢”的访客。一天,两个“官员”来找他,对门口的候诊队伍视而不见,直奔张建明的诊室。张建明脸一沉,对他们说:请排队。他们却不屑地说:我们只是来咨询,占用一两分钟就好。张建明还是那一句话:请排队。两人拉不下脸,遂发狠道:嘉定还没有我进不去的门!张建明一听,狂劲发作,立刻怒发冲冠,用比他们更狠十分的声音下了逐客令:我这个地方就是进不来!
侠客本该如此,对该施仁心的人仁心,对不该留情的人决不留情!
沉重的担忧
采访越来越接近尾声,记者就越来越发现张建明的那两道浓眉一直紧锁,从未舒展过。而采访中的话题无论如何展开,如何东拉西扯,张建明脑袋里总有一根永恒不变的轴,他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行动都在围绕着它打转,这根轴就是中医。“现代的中医正在剧烈衰退啊!”张建明此言一出,记者便感受到他心中那种揪心揪肺般的疼痛。不是吗?他视中医为生命一部分,他的紧锁着的眉,他的瘦削的身体,他的超负荷的工作,不正明明白白地袒露着他这种沉重的心情么?
2003年,张建明毛遂自荐,成为“非典”期间沪上医界唯一被市领导点名进入隔离病房参加为患者救治的医师,在同时进入的另11位西医专家面前,张建明这个仅有的中医身份让他倍感自豪,然而,也顿生失落。“仅有的中医啊!我们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医难道就这么被忽视吗?难道在人类遇到的疑难杂症面前,就只有靠西医来治了吗?”张建明痛心疾首:“看到有些中医在看病时连脉都不把,直接开处方;还有些中医学院出来的博士生居然连中药都不会煎……每当此时,我的痛苦和遗憾就蔓延开来——连对中医药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又何必做中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