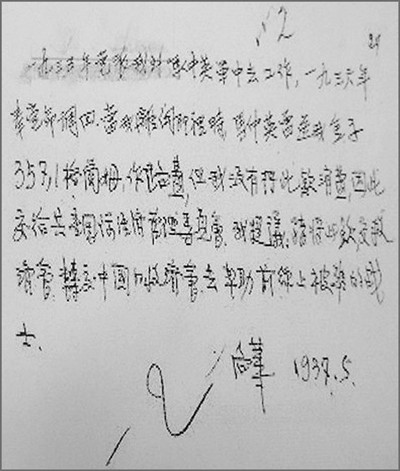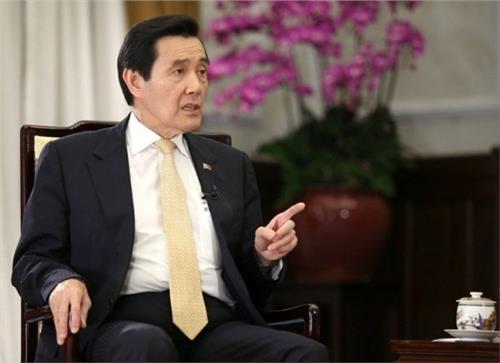马仲英永昌 永远的尕司令:马仲英 | 端庄读书
读红柯《西去的骑手》有感,仅以此文纪念逝去的骑手
一次偶然的机会从同学那里看到了红柯的《西去的骑手》,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书,但是已足够让我震撼或是激动好多次了。一直想写一篇关于书中主人公的文章,可是每每提起笔书中的场景就会一股脑涌向心头,一切都变得杂乱无章,以至于无法继续下去,只好就此搁下笔来。
当心绪平复后,我将搁下的笔重新握在手中,那种混乱的状态再次奔袭而来,只好再次停下。这种痛苦反复折磨着我的神经,我不堪忍受终于打消了继续写的念头。然而,经过一段时间,当书中场景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模糊的时候,尕司令的形象却逐渐变得清晰,我分明看到一个英武、干练而又充满野性的少年骑着一匹雄壮的大灰马缓缓向我走来。
也许是同一民族的缘故,对尕司令总是有种特别亲切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很强烈,我一直自以为是地这么认为。直到后来我看了《千古文人侠客梦》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错了,彻彻底底地错了,自己有那种亲切、甚至是热血沸腾的感觉,不是因为我们都是回族,而是因为我自己太弱小了,我虽然不是文人,但是也和古代的文人一样,面对强大的势力和不可抗拒的暴力的时候,都是那样的软弱、无能为力。
没有力量或者是力量弱小的人都渴望拯救世界的英雄出现,我和那些文人一样,都期待拥有强大力量的救世主去拯救这个世界,仰慕那些逍遥自在的侠客,甚至还幻想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那些侠客一样能够仗剑走天涯去行侠仗义、除暴安良。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幻想或者是一种悲观的奢望吧,至于能不能实现,谁也不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西北人所特有的那种野性在尕司令的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狂放、果敢、睿智、血性,这些优点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聚集在一起,也只有在特殊的环境里上天才会赋予一个生命个体如此多的优秀品质。也就是说,尕司令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他将注定成为那个时代的英雄,即便是生命如流星般短暂,光芒也足以让日月星辰黯然失色。
那片水土不仅仅养育了他,给了他一副剽悍的身躯,还造就了他天生的领袖气质,正因为如此,他的生命之花才会如此地绚烂、夺目。
不可否认在某些方面天赋更加重要,大西北的尚武精神让高傲的德国人都佩服,但是尕司令却能让那些儿子娃娃折服,跟随自己将西北搅了个底朝天,这种特有的气质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更不是通过后天努力锻炼出来的,而是与生俱来的东西。
十二岁时,他已是河洲最厉害的骑手,一直到十七岁打冯玉祥之前,在河洲没有人能够在马背上战胜他。十四岁与堂兄马步芳比武的时候,他的刀法就像海水一样连绵不绝,攻势像凶猛的海浪一样侵袭过去,很快就将马步芳淹没其中。
难怪大阿訇会说“步英是儿子娃娃。而七老太爷也说:河洲能出一匹骏马,我老汉高兴。校场比武之后,他随大阿訇进入了神马谷,至于他在那里具体干了些什么事情、做了什么样的训练或者说受到大阿訇怎样的教诲,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他在那里一定受到了与众不同的洗礼或者也可以说大阿訇为他注入了“魂”——战神之魂。
他接受了洗礼,知道了想要有作为就应该先到沙漠里去,因为先知曾经说过沙子是生命的露珠,越是荒凉干燥的地方,生命的露珠越鲜活。
于是他就将自己的部队带到了沙漠之中,也让他们接受沙子的洗礼,感受生命之露珠,而那些经过沙漠锤炼存活下来的士兵就成为了他日后起兵的骨干分子,他们也练就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躯。
他以他所特有的方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始了自己短暂而又辉煌的传奇生涯。他分明还是一个孩子,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然而他又确实是那支队伍的最高长官,是人人都喜爱的“尕司令”。他凭借着自己的个人魅力迅速拉起了一支极具西北特色的队伍,与其说具有西北特色,倒不如说他把大阿訇为他注入的战魂注进了这支队伍,并逐渐将其锻造成为一支所向披靡的铁军,成为西北地区不可忽视的一股军事力量。
与现代化的枪炮相比,大刀的确有些落伍,但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部分军队里,刀都是必不可少的武器,有的队伍甚至还专门成立了大刀队。一方面是由于武器相对缺乏的缘故,另一方面,中国的尚武精神让他们固执地认为,军人的魂魄胆略都在刀上,如果一个人连刀法都练不好,就没有资格去打仗。
骑兵的特点是机动性强、行动迅速,骑手们利用这个特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入敌阵中,给对手以致命的一击。很显然,当双方短兵相接、狭路相逢时候,刀就有了充分的发挥空间,谁手中的刀更快、更狠、更准,谁就是胜者。
刀过处血肉横飞、哀嚎不断,让对手的血将刀洗涤干净,只有饮到更多的血它才会发出摄人心魄的寒光,这种惨烈的景象让人不寒而栗,但是却能鼓舞己方的士气。
在尕司令看来,只有河洲的“一把手”才是真正的刀,骑手们也以能拥有一把“一把手”为荣,所以他的骑手除了军刀外,还有一把属于自己的河洲短刀。马简直就是骑手的影子,也许应该说是身体的一部分吧。
尕司令在神马谷找到伴随自己一生的神马——大灰马,大阿訇还告诉他,骑手最后的归宿是大海,马血中有海洋的味道,骑手应该喝马血,体味自己最终的归宿。马不是空着身来的,它驮着英雄的魂魄,只要魂魄不散战马就不会倒而且永远保持着奔跑的姿态,当骑手失去生命后,马儿会狂奔追赶骑手的魂魄。
马应该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了。大灰马几乎就是尕司令的代言人,它到哪里人们就认为尕司令在哪里,人们就会尾随大灰马找寻到尕司令的踪迹,就如古人说得那样,只要主人不死,马永远都不会停下奔跑的脚步,大灰马总能在主人与大家失散后将众人重新带到主人的面前。
很显然,那是一匹神马,难道不是吗?当它从青海湖中奔腾而出的时候,就昭示着它和它的主人一样是不可战胜的。
河湟一役,尕司令名声大震,西北升起了一颗年轻的将星,他的光芒注定要盖过其他所有的人。冯玉祥的几员大将都被他打得狼狈不堪,刘郁芬吓得屁滚尿流,像缩头乌龟一样龟缩在兰州不停求援;赵仲华旅在河洲城上被尕司令的骑兵淹没,他本人也永远和那些年轻的河洲娃娃倒在了一起;二十五师遭到袭击全军覆没,师长戴靖宇被砍成重伤几乎一命呜呼;抗日名将佟麟阁率领的十一师被打得溃不成军,自己还差点被生擒,结果连尕司令的人都没见到,就恨恨地离开了大西北。
吉鸿昌在吸取几人的教训后,不与尕司令的骑兵发生正面的冲突,先用炮火将对手的冲锋势头压制下来,等到敌人士气下降的时候,再将大刀队投入到战场上,这样就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西北军的大砍刀,“尕司令”的河洲刀,双方的兵器激烈地碰撞,这碰撞产生光芒盖过了天上的太阳,刀与刀都深深嵌入对方似乎想要成为身体的一部分,很快刀刃被滚烫血液溶化,只剩下刀柄。
尕司令几次败在吉鸿昌的手中,还险些丢了命,但是他失败后都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召集起上万人的队伍,而且每次人们都认为他必死无疑的时候,他总能奇迹般再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这一点,我觉得他的那些兵说得很有道理:尕司令如果那么容易死掉就不是尕司令了。
的确,尕司令是黑虎星转世命硬得很没有人能从正面杀了他。尕司令是天生的战神,那些兵天生就是尕司令的兵,他们都是河洲的儿子娃娃。他们认为,血性男儿就应该活一身辉煌,所以他们选择用手中的刀杀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这也许就是他们心中“儿子娃娃”的标准吧。
大海是骑手最后的归宿,沙漠是骑手的海洋。可是沙漠也是死亡之海,戈壁大漠也早已不再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场景,金黄色的沙子披着丰收的外衣呈现给人们一片肃杀的景象,一切的生命在沙漠之中都显得脆弱不堪。
人们面对沙漠的侵蚀,只是一味退让、逃避而不去采取有效措施与之争夺仅有的生命绿洲,有些人还在肆意破坏沙漠边缘的环境,加快了土地的沙漠化,逐渐形成人人自危,谈沙色变。人们根本就不愿意走进沙漠,更不会有穿越沙漠的念头,这在一般人看来那根本就是送死,穿越沙漠就意味着要穿越死亡地带,那里到处都有隐藏着的死亡陷阱,随时都有被沙漠吞噬地可能,而且说不定死神就脚下沙子中潜伏着。
但是尕司令和他的士兵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穿越沙漠只是一种历练,如果不能在沙漠中生存,那也只好成为沙子的食物。
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克拉玛干沙漠的一头走到另一头,用他们的话就是,跟喝凉水一样容易。他们用侵袭的暴风沙洗澡,洗个沙子澡,跟磨刀石一样,把人磨得闪光。
他们就这样来回穿梭于沙漠之中,沙漠根本就奈何不了他们,从而选择了投降,他们征服了沙漠,不,他们不仅仅征服了沙漠,还征服了死神,死神看到他们都望而却步,他们的脸上没有任何绝望和沮丧的神情,永远都是那么乐观向上。
布琼尼的骑兵也许很厉害,那也是他们没有碰到真正的骑手的缘故。说实话,吉鸿昌能够打败尕司令,与武器先进、火力猛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尕司令有同样的火力,我敢说他吉鸿昌会败得很惨,而且是惨不忍睹。与布琼尼的顿河骑兵师一战就是很好的证明,如果没有飞机的火力掩护,苏联的坦克师也会遭到灭顶之灾。
迪化城外空旷的草原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双方几万人就那样列队对峙着,锋利的战刀发出让日月失色的光芒,两队人马像是两股迎面而来的洪流,哪一方都不肯退让,激撞过后,草地被染成了血色,与残阳的颜色构成了杀戮图的主色调。
血色如果是这幅图的基本色调,那么残肢断臂则是用来勾勒这图画的“画笔”,这活脱脱就是一座人间地狱,人失去了为人的一切条件。
红色骑兵师的师长为自己的轻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当他还在笑话尕司令的是个娃娃的时候,尕司令的河洲刀已插入他的喉咙,他再也发不出任何的声音。尕司令的兵经过训练后,再也不是人见人欺的乌合之众了,而是一支能打硬仗,敢打硬仗,善于打硬仗的钢铁部队。
哥萨克师长倒下的瞬间,尕司令的兵像旋风一样刮了过去,很快俄国人引以为傲的骑兵就被中国的“娃娃骑兵”吞噬了,战场上硝烟弥漫,落日的余辉为这场面镀上了一层更加悲壮的色彩,满地都是被砍翻的哥萨克骑兵,许多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拔出自己的战刀,就那样整排倒了下去,倒下去的人像睡熟了一样安详。
然而尕司令还是战败了,坦克、装甲车也没能奈何尕司令的部队,他们熟练地炸毁了一辆又一辆的坦克和装甲车,但是对天上的飞机他们却无可奈何。
在飞机的“护送”下,尕司令的部队再一次逃进沙漠。当尕司令在沙漠中逃亡的时候,吉鸿昌正在内蒙与日本人喋血;当尕司令再次围困迪化的时候,吉鸿昌已经被何应钦杀害了。当从探险者口中得知吉鸿昌的事迹后,他是那样的不甘心,在战场上,他没有能战胜吉鸿昌,而在打日本鬼子上,他又输给了吉鸿昌。全中国好像只有吉鸿昌一个人能打日本人。
斯大林想让新疆独立,和蒙古一样成为苏俄的附庸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看到了,可是他们忙于“安内”,只有尕司令以一己之力去与苏联抗衡,失败是注定的,他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捍卫中国人的尊严,即使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这才是真正的骑手。
苏联人终于认识到,在新疆那片广袤的草原上,尕司令是不可战胜的。布琼尼的骑兵师全军覆没,斯大林的坦克、装甲部队战败了,飞机虽然将尕司令赶进了沙漠,可是他却接二连三从沙漠中复活。他们意识到,只有通过其他手段才能彻底战胜尕司令。
尕司令要去苏联开飞机了,他带走了二百多人,其中有一半的人都被挑选为飞行员,而且他们以惊人的速度在吸收知识,这让斯大林感到恐惧,尤其是尕司令学习飞机驾驶没多久,就能将飞机开上天,而且在飞机失事后人们都认为他已经必死无疑的时候,又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斯大林这个杂碎终于要向尕司令动手了,他们用卑鄙的手段妄图要毒杀尕司令。可是他们太小看尕司令,他们不知道尕司令是黑虎星,没有人能正面杀死他。尕司令从苏联人的特设监狱中逃了出去,他最后的归宿是大海,他不能死在那些人的手中,他要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大海,他要和自己的大灰马一同走进最后的归宿。
终于要写完了,可是有一种说不出的落寞,在写的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眼睛一直是湿润的。同情,我没有资格,怜悯?可怜?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自己的心情。只不过有一点遗憾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自己没有出生在那样的一个年代,没有碰到尕司令一样的人。
“一个英俊神武的少年,骑着一匹大灰马,手中举着战刀,像闪电一样冲向敌人”这就是永远的尕司令,一个真正的骑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