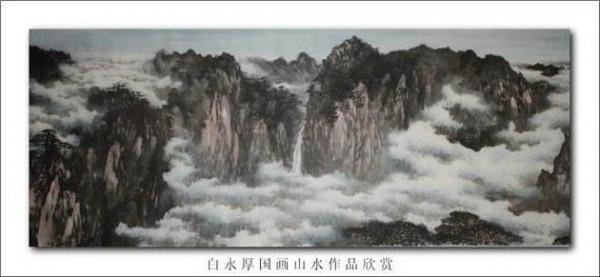王国斌油画作品欣赏三典轩书画网|在
王国斌1962年出生于南京,现为江苏省美术馆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8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业,1998年结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人物高级研讨班。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省市展览并获奖,多家专业报刊杂志发表和介绍。曾代表中国艺术家出访欧洲进行学术考察,并被评为2006年江苏优秀青年国画家,作品被国内外多家美术机构、博物馆收藏。
(根据网络资料编辑收藏)
人得到的同情,与受的苦难应成正比。这一定律,却不怎么适用知青一代。起码在我,知青的遭遇,总难免是“活该”的。所以“活该”,不是他们当年自甘入彀,想“大有作为”;也不是在文革里,他们中有犯下暴行的人。举国如醉,童子独醒,是童话才有的情节,生活是没有的。
我所不解的,是那苦难已成为历史,亲历的人,应反思其由来,留为殷鉴的今天,却有人说“青春无悔”,“磨练了意志”,乃至“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张承志语)。
人之自恋,在于凡自己经过的事,都称是“好的”。比如吃粪是为体味吃肉之香;被抽打,是为享受伤口渐愈时的微痒之快感;“受骗”是“信仰”,遭罪是“殉道”。我说“不是”,岂非连窝端掉了其幸福?故只有说“粪是诚然该吃”了。
但一场改变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命运、因而也改变了中国之命运的浩劫,亲历的人,若只懂得自恋,后来的人,仅报以漠然,则不光罪白受了,下一次浩劫,离我们子孙恐也不远。所幸10余年来,赖得寥寥几个老知青的良知,这浩劫的伤痛与丑恶,才渐被我们认识。
在这个方面,作家是先醒者,如老鬼,徐晓,叶辛等;艺术的反思,似迟钝于文字。但王国斌近年的一组以知青为题材的油画,则于艺术沦为琐屑的逸事、与形式的游戏多年之后,又使人看到了其作为良知之载体的归来。
知青生活,是王国斌近来倾力的主题。目前已完成的作品,似有五、六幅。这些画面,多笼罩于昏黄的基调里。与调子鲜明而冷的其他知青画相比,似一来自反刍过的记忆,一采于知青生活的“现场”;——前者近于“反思”,后者是近于“记录”的。
人心理的机制里,原有“选择性遗忘”的本能;故凡追忆,总难免美化、或浪漫化。王国斌则以清醒的反思,抵制了这本能。故知青真实的处境,如理想的崩溃,受宰割的无力感等,在他的作品中,仍获得了清晰的表达。
这组画中的佳作,当推《青春之歌》与《让我们荡起双桨》。在艺术过于视觉化的今天,这两件作品,可谓重申了“使艺术具有文字之品质(discursive quanlity)”的老雄心。如五、六十年代的人所知的,这两作品的标题,乃套自一同名的小说,一同名的少儿歌曲。
知青一代人,就是在两者所表达的理想与乐观气氛里成长的。它们许诺了其未来的幸福,未来的意义。但王国斌画里的未来,却是另一种样子。如那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长大的女知青,手握的已非双浆,而是挖地的锨、牧羊的铲;“美丽的白塔”,则取代于灰白、驯顺的绵羊;在理该有“绿树红墙”处,却只有灰褐、焦干的土。
那曾“小船儿飘荡”的少女,如今坐于土上,如涸辙中的鲋鱼。
但这个姑娘,似浑然不知其处境。她脸挂着笑容,正以铲为桨,以地为船,仿佛一边默谢着那“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的人,一边体味“大有作为”的快感。则知创作这作品时,画家是假设未来的观众,应熟悉《让我们荡起双桨》一歌的。通过对记忆中歌曲的征引、比较,观众可晓悟作品的反讽之意。
与《让我们荡起双桨》一样,油画《青春之歌》,是对另一篇文字的“挪用”(appropriation),或“反模仿”(parody)。因小说《青春之歌》的主角,也是一位“女知识青年”(林道静)。唯较新知识青年不幸的是,她生于旧社会。
在黑暗势力的压迫下,她初嫁给一地主官僚,成为其玩物。但她不甘于此,故出逃北平,在此遇到了一叫“余永泽”的北大学生。因尚无革命觉悟,她竟爱上了他,与结为夫妻。后在北大革命学生的教育下,她认清了这个余永泽,只是个懦弱、庸俗的小资书生。
于是离开了他,投身火热的抗日,去寻找革命的爱情了。王国斌笔下的知青们,莫不是伴着这小说长大的,莫不以书中的故事,去规划未来的爱情。但讽刺的,在王国斌的画中,知青按革命的逻辑,虽找到了爱情,却发现这个爱情,并不是她真想要、乃至厌恶的。
画的背景,由弧形的窑洞,矩形的门窗、条凳,与圆柱形水缸子等构成,条凳上坐有一男一女。女的是上幅画里我们见过的知青,男的是个一脸憨态的农民。
那女知青已没有上画里的喜悦,她蹙紧眉头,微露愁容;身体则僵硬而局促,并微倾向一侧,似躲避着身旁的新郎。新郎则颟顸地叉开腿,一脸未开化过的兴奋。从新娘那复杂的表情看,我猜她一定在问:这是《青春之歌》里许诺的爱情吗?林道静父母的势利,较之政治的逼迫,是否真那么可怕?因误识人而坠入情网,与迫于“形势”而嫁人,哪个更残酷?政治觉得好的,人性何以厌恶?则知这个从童年起,便以贫下中农为荣的少女,在嫁给一活生生的贫下中农时,才突然感到了阶级的鸿沟,才开始怀疑那些革命的逻辑。
王国斌的这组作品,令人想起吴冠中那句很丧画家气的话:一百个齐白石,也不抵一个鲁迅。我想这个说法,是从怎样使绘画“具有意义”而言的。就油画的范围说,自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艺术结束以来,如何使绘画具有意义,便一直是西方油画的一梦魇。
文艺复兴前的艺术,因有一套通用的象征语言,故颇有“表达意义”的能力。但随着宗教信仰的淡出,这套语言成了滥调,不再能打动人。结果如黑格尔说的:“圣父、耶酥与玛利亚,无论画得多高贵,多完美,都没有用了;它们无法令我们跪下”。
在巴罗克与古典主义艺术以舞台般的布景,演员般的动作,试图给绘画注入意义,然而却失败之后,艺术似逐步放弃了“求意义”的雄心。最后的结果,就是从印象派开始的现代艺术的纯视觉化。吴冠中的灰心,与印象派的信心,其实来自于同一个难题:艺术很难再有共通、共解的意义。
“您在读什么,哈姆莱特殿下?”
“一堆词儿。”
“您在画里见到了什么?”
“一团笔触。”
但在形式的演化自成一连贯历史的西方,即使一团笔触,也能与宗教画、历史画、与叙事画有着同样多的意义,——只要它能纳入形式史的序列内。盖在一原生的、连贯的历史中,形式本身便是文化史的象征,精神史的体现(潘诺夫斯基称“线性透视乃西方文明的象征”,便是由此而言的)。
因此,在传统意义的“艺术主题”失效之后,形式本身便成了西方艺术的主题。但对于移植来的、并不断汇入西方之潮流的中国油画而言,它的形式,并不来自本土的精神之结构,故也无法形成一连贯的历史。
因此“一团笔触”,在中国就只是“一团笔触”了,并不具有任何意义。所以就中国油画而言,形式本身,是只能作工具、不足为主题的。中国油画的主题,应主要是我们的内外之生活。这种主题的提炼,也必与现实、社会有互动。这转而决定了中国的油画家应是有兴趣关心、有能力思考现实的人。
最足表现这种主题的形式之一,是叙事画。所谓“叙事画”,并不是“类型画”(genre painting)——如人们热中的西藏风情等;也不是历史画。前者主要依赖于眼睛的敏锐,后者则为导演的本领。较之类型画,叙事画须多一重对社会的洞察;较之历史画,又要多一套编剧的能力。
不同于前者,叙事画画家,必须假定观画的人,要有与画面叙事相关的知识之背景;从这一点说,叙事画必有很浓的文字性,或文学性。有别后者的是,这预设的知识之背景,并不是规范的,划一的,而是多有个人的色彩。由这点看,叙事画又有须容许解释的弹性。
就这些标准说,王国斌的这两幅知青作品,实可谓中国当代叙事油画的最佳范例。对社会,他有洞察与良知;对抽象的思考,他有编剧的想象;他会善借观众头脑中的知识之细节,来扩充画面,丰富含义。在安排细节时,他有诗人的手段,会巧用隐喻增加阐释的弹性;——如第一幅的绵羊,第二幅的绣花鞋等(想起结婚外,你还会想起“官僚地主”吗?)。
最后、虽非次要的是,他是一名实力雄厚的好画家。他素描准确、精致,色彩浓厚而雅气,注重画中细节描绘;所以观其整个画面,是一体构思的,整体感很强。
他画里的人物很真实,绝无面具感,仿佛加个“王晓”或“李柱”的名字,就能成为我们身边曾认识的人了。这种种特点,使我观看王国斌的画时,似恍然重见了十九世纪“文学化艺术”的伟大实践——那甫有蓓蕾便夭折了的伟大实践。
随着这组知青作品所依赖的知识的消失、或被淡忘,作品所表达的历史内容,或将变得朦胧远去,不能象一朵“好笔触”的郁金香一样,因纯视觉而永恒。但对知青运动尚有记忆、或有知识的人言,王国斌的这一组画,却是对知青遭遇的最诚实、最雄辩的表达。


















![>罗尔纯书法 罗尔纯油画作品欣赏[三典轩书画网]](https://pic.bilezu.com/upload/1/fa/1fa6165813c366b8e92a1a3eb5f7b91c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