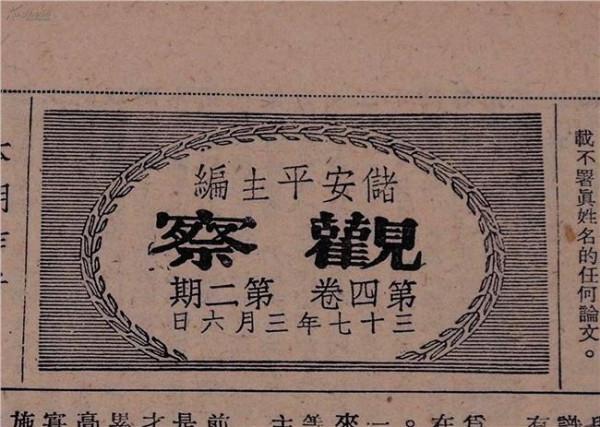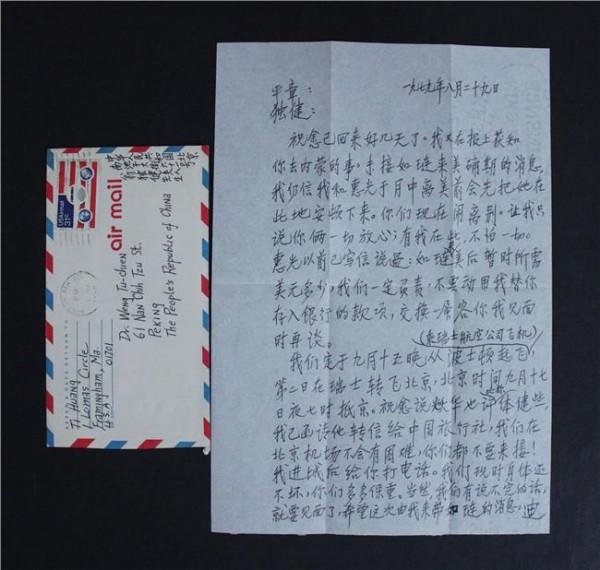潘光旦费孝通 费孝通与潘光旦的学术交往
1947年出版的《生育制度》是费孝通最出色的理论著作,可以作为他前半生学术经历的结束。书写成于1946年夏他与潘光旦在苏州浒墅关避难时期。当时旅途困顿,行止不常,天气极为闷热,费孝通颇有将全稿搁置的意思,后来经潘光旦劝告,才决定姑先付印,以待将来补正。
费孝通请潘光旦写一篇序。潘光旦历来为人做序都非常认真,绝不敷衍了事。跟他的书评一样,他总是希望在评论别人作品时表达一点自己对研究课题的见解。也许是由于对费孝通这颗学术新星的前途期望更殷,他洋洋洒洒,不可收拾,一写就是3万多字。
这就是《派与汇——— —作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的序》一文。他认为,费孝通的书写得很好,但只是一家之言,太局限在功能学派的立场上,器局比较狭窄,并不是全面的分析。他回顾了中西方社会思想分分合合的历史,提出了一个更为综合的新人文思想,期望费孝通能够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费孝通对自己的学术相当自负,对潘光旦的批评,他并没有完全接受。但当时的处境使他们没有条件和心情就这个社会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展开辩论。1947年费孝通从英国回国后,虽然两人同住一院,但也无心就此进一步切磋琢磨,展开辩论。直到1990年代,费孝通年过八十以后,才重新拾起这个似乎已尘灰堆积的思绪,触起了重新思考。
通过反思文革中的经历,费孝通认识到,个体虽然无法摆脱社会结构派定给他的角色要求,但他也有一个顽强的作为实体的“自我”存在。“这个自我的思想和感情可以完全不接受甚至反抗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并做出各种复杂的行动上的反应,从表面顺服,直到坚决拒绝,即自杀了事。
这样我看见了个人背后出现的一个看不见的‘自我"。这个和‘集体表象"所对立的‘自我感觉’看来也是个实体,因为不仅它已不是‘社会的载体’,而且可以是‘社会的对立体’。
”从而将个人与社会作为并列的两个实体。“社会之成为实体是不可否认的。但是社会的目的还是在使个人能得到生活,就是满足他不断增长的物质及精神的需要。而且分工合作体系是依靠个人的行为而发生效用的,能行为的个人是个有主观能动性的动物,他知道需要什么,希望什么,也知道需要是否得到了满足,还有什么希望。
满足了才积极,不满足就是消极。所以他是个活的载体,可以发生主观作用的实体。社会和个人是相互配合的永远不能分离的实体。这种把人和社会结成一个辨证的统一体的看法也许正是潘光旦先生所说的新人文思想。”
潘光旦的新人文思想是一种在社会思想史研究基础上提出来的社会思想,而费孝通则是从社会学学科的基础理论出发,对其做出的新诠释。费孝通学术思想的这一新发展,固然有赖于他善于从社会生活经历中提炼社会学理论的悟性,也是与潘光旦早年在《派与汇》中的批评与期望播下的种子分不开的。
他后来在谈到社会与个人关系时,已经不再像《生育制度》中那样“见社会不见人”,而多少已经接受了潘光旦的批评意见。这时潘光旦已经去世几十年了。
费孝通与潘光旦的私人关系很深,从私人关系而学术交往,而政治上的长期风雨同舟,长达三十多年。作为晚辈,费孝通一直以师生关系来看待他与潘光旦的关系,在人格上、在学术上、在政治上他受潘光旦影响很深。本文所叙述的,只是他们在学术交往上的几个片断,还远不足以揭示全貌。虽然他们在学术上走的路子不同,但是能够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合作共事,对今天学者之间如何相处应有重要的借鉴意义。